▌曹利群
灯放在斗上,就照亮一家人。——西谚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T.S.艾略特


波恩_贝多芬像

维也纳贝多芬棺材的钥匙

贝多芬波恩故居内部
在近300多年来的西方音乐坐标图上,巴赫以巴洛克音乐的终结者和后世音乐的奠基者,毫无疑问地坐在第一把交椅。位居第二的莫扎特,以其古怪精灵的天分和对各个领域的杰出贡献稳居第二。然而更多的时候,巴赫是在尖顶的教堂里俯视我们,莫扎特则始终在城市宫廷内不断穿梭,他们远不如那位坏脾气且勤奋的贝多芬更有烟火气,离我们更近,尽管他始终位居第三。就交响曲的数量来看,虽然他远不如海顿、莫扎特写得多,但九首交响曲各臻特色。其中的第九交响曲虽然在首演时差强人意,甚至令作曲家沮丧,但是在后来的200年中,每每历史的关键时刻都少不了它的救赎与拯救,当然还包括那些公共事件的高光时刻。相比其他的作品,贝九更容易被用于政治目的。它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被演奏;1989年,再次又在柏林演出。贝九的第四乐章《欢乐颂》总是凝聚着精神,象征着希望。在智利,抗议皮诺切特政权导致的失踪和死亡时,人们唱起了这首乐曲。在日本,常被安排在除夕夜演奏的贝九象征着新生,成千上万的业余歌手组成合唱团参与其中。1998年,指挥家小泽征尔召集了六个合唱团,在长野冬奥会开幕式上通过全球接力演唱了《欢乐颂》主题。这也是“第一次将全球影像和声音同时联合在一场实时演出中”。团结奋进,昂扬向上几乎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色调。
创作与猜想
创作第九交响曲时,贝多芬已年满53岁,几乎完全失聪。自第八交响曲完成以来,也已过去了近十年的时间。然而在此期间,他依然完成了包括《庄严弥撒曲》在内的多部杰作,直至1827年去世,还创作了晚期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等作品。
那个年代的维也纳人越发追求享乐主义,娱乐让他们暂时忽略黑暗的政治现实,而赶时髦当然是大众所趋之若鹜的,罗西尼作品的流行依然统治着城市,不消说也减少了其他音乐的听众。这些对于贝多芬的重新出山显然是不利的。然而伏枥的老骥没有昏睡,壮心不已的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芒的消逝”。迪伦·托马斯这句话用在贝多芬上再合适不过。
巴伦勃依姆在今年夏天以指挥家的视角告诉我们,人们可以从贝多芬身上学到很多,他是音乐史上最强大的人物,也是将情感与理性结合的高手。与贝多芬的作品相处时,听者必须能够结构化自己的情感,换句话说就是在情感中感受结构。音乐学者西蒙森指出,贝多芬的天赋显示在他驾驭自身才能的至高无上,并不在于他的个性特征。虽然他的个性特征十分鲜明,但在他的人性力量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没有第二个作曲家的人性力量表现得如此突出。
准确地说,第九交响曲的标题应该是:最后带有席勒的《欢乐颂》合唱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不是以陈述开始,而是提出问题。或者说它开始的那几个音符更像一个引子,像音乐的创世纪。开始的若干小节既不可界定为节奏,也不能界定为调性或者旋律。只有当节奏的片段集中起来,成为一个绝好的全奏主题时,才能初步领会到它面貌的端倪。之前的八首交响曲大都开宗明义,即开头几小节就提出辩证逻辑的对立因素。贝九把处于变化的状态与不变的事物对立起来,从而展示出根本的对立因素。就此便打开了一个体量巨大的延展空间。
第一乐章的引子中有一个神秘的空五度在低低的运行,仿佛开天辟地之前的黑暗与混沌,暗示着这将会是一部庞大的作品。主部主题的片段逐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突然像闪电似的在乐队中闪耀。在沉重肃杀的第一乐章之后,作为谐谑曲的第二乐章,以敲击声似的八度开头,据说这来自贝多芬的一次生活体验,是从黑暗中突然转向光亮处联想起来的。作为听者,总感觉这种敲击的音响和下行进行附点的节奏与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是有联系的。这个大型赋格段充满力量且轻巧明快,被生动地形容为“戴上丝绒手套的铁掌”。夹在具有冲击力和戏剧性的前后乐章之间的慢板充满了宁静和深刻。这是一个双主题的变奏(贝多芬所喜爱的一个形式),其中第二个主题无疑具有浪漫主义的渴望。第三乐章表现的是心灵的狂喜之后完全的陶醉,其温暖与情感的深度是空前的,即使在贝多芬其他作品的慢板乐章中也绝无仅有。这种超拔脱尘更接近上苍,面容严肃,步履缓慢,充满喜乐和庄重的赞美。
至于第九交响曲为什么会有一个使用人声的末乐章,讨论之前需要摒弃一个套话,即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的开始已经蕴含了其必然的结尾。大凡作曲家在一个作品下笔之前会有一个大略的构思,但未必就先入为主地把结尾规定好了。况且贝多芬在多种场合下说过,他喜欢在同一时间内全神贯注于几个曲子的创作。
《欢乐颂》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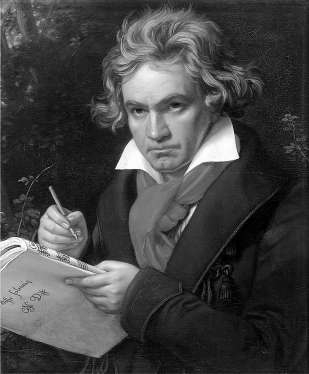
贝多芬在《欢乐颂》之前三个乐章中对管弦乐团的运用,加上他在音乐创作的特征上,造成了类似于凝视天空的那种畏惧。但到此为止,第九交响曲基本上还是幻想层面上的沉思默想。这种幻想压倒了一切,能够唤起欢乐,也能引起绝望。实际上,贝多芬在前三个乐章里把人类缩小成微生物的尺寸,这些景象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从思考一个浩瀚而不可思议的宇宙开始,我们受到柔板乐章中不断增强的自信心的推动,像一个人在漫游一个光辉灿烂的境界,直到闪烁的星星和苍白的月亮在我们眼前暗淡下来。
需要给出答案了。
当贝多芬二十岁出头时,确切地说是在22岁,就已经在考虑将席勒的《欢乐颂》谱成音乐,响应诗人呼吁普世兄弟情谊的主题。(见斯瓦福德著《贝多芬传》)也就是说,他青年时期成长的波恩与之后立足的维也纳(贝多芬于1792年搬至维也纳)之间的联系,为贝多芬日后思想的发展和创作的延伸奠定了基础。在平民视角的贝多芬传中,斯瓦福德巧妙地将《英雄交响曲》末乐章的主题——基于一种名为“英国舞”的流行舞蹈——与席勒书信中的一段话联系起来,将“英国舞”视为一种理想社会的象征,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但从未妨碍他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同时也顾及他人的自由。”
虽然有席勒的诗歌在前,但贝多芬也考虑过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另外一种可能的写法。在a小调四重奏中(作品第132号),他探索了另一种形式。这是一部孤高同时又带有怀旧情绪的作品,第一乐章就充满了悬而未决的紧张。与贝多芬其他悲剧作品的不同在于,它带来了一种压迫感。音乐在这里讲述着所忍受的痛苦,没有缓解的希望也没有愤怒。如果把四重奏和第九交响曲两个结尾对比一下,一个被激愤悲怆撕裂,另一个则充满信心。然而草稿表明,贝多芬曾打算把a小调四重奏的末乐章,至少它的主题素材用在第九交响曲中,而宣叙调在两个作品中都出现了。经历了绝望、恐惧和平静的三个乐章后,也许贝多芬更乐意给到众生以希望而不是沮丧。于是在两种对立的解决方案中选择了以人声的介入来唤起人们的信心,最终想到青年时期的抱负,这才引用并改写了席勒的《欢乐颂》。当然,这些也许只是推论,贝多芬并没有写在第九交响曲的总谱上。
柔板乐章的慢速所体现的人类的温情不断加强,渐渐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宇宙的空间转向眼前,转向人的位置。贝多芬把整个四乐章看成一个循环结构,他要完整地统摄这一作品。经历了前三个乐章的乐思转折,最终由人声与乐队共同传达出仁爱的力量,把变奏曲的静止带入到一个激情澎湃的狂欢状态。
《欢乐颂》的主要文字如下:
(男中音独唱,四重唱与合唱)
嗯,朋友们,莫悲伤,让我们用欢乐的声音齐声高唱。
欢乐,你是上帝的灵光,天堂的女郎。
女神啊,我走进你的神殿,欣喜若狂。
你的话把被无情的习俗分开的人们又重新连上,
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
(男高音独唱与合唱)
欢乐,上帝的昼夜在宇宙间的光荣轨道上运转。
兄弟们,快把善行的航程引到胜利的方向。
(合唱)
拥抱吧,千百万人民!
吻这个世界。
兄弟们,星际的尽头是我们慈爱的万能之父,
啊,千百万人民,
你可跪在他的面前,你可感到他与你同在。
去寻找吧,他一定住在那星际的尽头。
(茅于润译)
贝多芬从席勒的诗歌原作中挑选了少数几节,并以任意重复的方式用在音乐里。
至此,作品的抒情性与戏剧性达到了完美统一,管弦乐和人声获得了高度一致,人性和神性融为一体。而苦难深重的众生是否会得到超度依然是一个谜语。
“黑色贝九”

战后,威廉·富特文格勒于1947年得以重返职业生涯,并与他的乐团——柏林爱乐乐团重聚。
200年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的尴尬被历史一一记录在案。为了凑齐更加庞大的乐队,他需要调整演出场所;为了获得批准,他还要向检查机关申请;为了资金和收入有保障,他不得不向贵族们请求资助。而在首演当天,几乎两耳失聪的大师还坚持指挥到乐曲结束。结局让人尴尬:虽然有现场观众的欢呼,但真正理解和懂得他作品的人微乎其微。至于收入更是惨不忍睹。这之后的三年时间,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晚期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也是一条孤独的路。至于第九交响曲在后世两百年的演出和录音所掀起的巨大波澜,即便是贝多芬在世也会错愕不已。
说到贝多芬作品的演绎一定离不开两位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和富特文格勒。(有关托斯卡尼尼以反法西斯艺术家的姿态对富特文格勒的道德指责,参见我的文章《把德意志镶进历史之墙》)单就两位艺术家的指挥风格来说,前者动作清晰,速度偏快,严整有力。后者处理作品的依据是乐句而非小节,使音乐跟随自身的特性而行,在总谱的基础上显示出一种相对自由的速度,构成了一种指挥家对作品的参与关系。
在众多贝九的演奏和录音中,富特文格勒无疑是一个最具重量的人物。他前后演绎的多个版本一直被后来者嘉许和争论。恰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每一个文明的文献同时也是一部野蛮的文献。”如果说我们在其他指挥家的演绎中都不曾见证本雅明的观点,那么,1942年4月19日富特文格勒对“贝九”的绝地演绎,则将此说诠释得淋漓尽致。
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十多部富特文格勒指挥“贝九”的现场录音。最早的是1937年在伦敦,最后一次录音是1954年8月,刚好是他去世前三个月。虽说每次演出的细节和强调之处都有所不同,但整体结构是一致的。在Tarha公司发行的唱片里,萨米·哈布拉有一篇详细的音乐分析,指出了富特文格勒有过三次演绎的独特之处:1942年的绝望黑暗,1951年的释怀抒情,以及1954年的平静与告别。其实在“黑色贝九”之前的3月22日,他在柏林演出过一次,虽然第一乐章激烈的高潮仍给人带来震撼,但比起4月19日的演出,在第一乐章的副题上,以及第二乐章的弦乐更富有抒情性。这种抒情性在展开部的末尾段尤其突出,那种歌唱性的渐慢无法不让人有一种太美了不忍离去的感觉,而作为对比的三连音呈现的是典型的贝多芬式渐强,仿佛由远而近渐次掩杀过来的漫天兵戈。第三乐章也是出奇的平静,波澜不惊。作为对应,有好事者把这个版本称为“旋律贝九”。我们不知道这个演出是不是4月19日的预演,从不断的咳嗽声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现场录音,但指挥家和乐队却没有失控。富特文格勒在战后重启的195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上指挥的那版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虽然表现出非凡的激动,仿佛寄托着人类新生的无限希望,而细品也是对艰难年代的痛定思痛。
1941年冬天有关莫扎特音乐周上演细节的讨论中,富特文格勒也有参加,虽然他未必赞成用《安魂曲》来安顿在前线冻馁毙命的亡灵,也不会用它来号召年轻人走上战场为艺术而战,但显然他无法逃避这种演出。正如他在1942年4月19日不能逃避用“贝九”为希特勒祝寿这样的尴尬时刻。
早在1933年,很多德国的作家艺术家面对纳粹的暴政都选择了流亡。富特文格勒之所以在犹豫之后选择留下,是作曲家勋伯格给了他勇气。创造伟大的音乐,“这是你的职责,也是真正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1937年夏天,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和富特文格勒有一个历史性的会面。老托认为,只要在第三帝国做指挥就是纳粹分子,艺术与音乐成了当权者的工具。富特文格勒则认为,音乐属于另一个世界,与政治无关,伟大的音乐能够与纳粹主义对抗。然而正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领域。毫无疑问,他选择留在德国坚守了德意志文化传统,但也因为政治上的幼稚而为纳粹当局所驱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内心的不甘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和让步,始终让这位伟大指挥家的内心处于挣扎的泥沼之中,也必然会反映到他所指挥的音乐中。这场1942年的现场广播录音(来自一个偶然的私人录音)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演出。富特文格勒与柏林爱乐对第一乐章的诠释让人想到“恐怖”和“愤怒”,这场称得上末日般的演出,可谓充满令人不安的暴力感。听听第一乐章的几段齐奏和末尾的猛烈和狂热的和弦,立刻就会被卷入而不能自拔。“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弦乐奏出的音色刺耳甚至凄厉,第二乐章的定音鼓用“火山爆发”来形容都显得不足,暴怒的鼓槌听上去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像是一种传声筒,无处发泄的怨怼和愤怒的表达,无可阻挡的自然伟力,无不来自指挥家的内心。乐队如影随形地跟着这位屈辱愤懑的指挥家,也把彼时彼刻的心情宣泄得无以复加。在愤怒的贝多芬之后,第三乐章展现了一个冥想与祈祷的贝多芬。富特文格勒从未像在此乐章中那样虔诚地祈祷。为遭受苦难的人们祈祷,为失去生命的士兵祈祷,为未来的和平时代祈祷。乐曲结尾前的四五分钟影像被广为流传,特写镜头里,人们可以看到志得意满的刽子手,面无表情的军人和士兵,一脸严峻的知识分子。合唱声中,他们也许会想到遥远的战争、硝烟、死亡,人们如何拥抱这个世界,如何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千百万人民。当此时刻,才能感受到贝多芬第九在特定的时空的正背两面,既有自身具有的内涵,也有艺术无法弥补的无妄灾难。愤怒,沮丧,下坠,祈念中依然憧憬着不知何时能现的希望之光。也许这正是它被称为“黑色贝九”的由来。这是欧洲的至暗时刻,也是德意志的至暗时刻,更是指挥家内心的至暗时刻。只有此刻,只有此人,才能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那种恶魔似的狂乱悉数演绎出来。而此前和之后的其他演出和录音,都无法背负这样复杂而又无解的历史使命。这也是贝九神秘而无法言说的宿命。
历史录音及其意义

威廉·富特文格勒与柏林爱乐乐团在慕尼黑展览大厅进行排练,时间为1935年圣灵降临节。
只有富特文格勒赋予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形而上学的意义和深刻的心理维度。在这个意义上说,1942年版的贝九也是富特文格勒指挥艺术的巅峰与精髓。自开首的第一个音符起,音乐仿佛从黑暗的深处浮现,将我们带入一系列恢弘而惊心动魄的时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时任柏林爱乐乐团的定音鼓手奥古斯特·洛泽,他的敲击完全与富特文格勒同频,表现出令人震撼的强大力量。并非录音师调高了音量,富特文格勒只用了他最信赖的录音师弗里德里希·施纳普设置的单一麦克风,充分保留了乐团音色的真实还原。这种还原的意义远超出了技术,这是对彼时历史的还原,也是对指挥家内心复杂状态的还原。顺带提一下其他单声道录音,它们可以托斯卡尼尼的众多演出现场为代表。无论是战争中还是战后,这些录音大都集中体现了一种反战或救赎的立场。其精神的指向虽然纯粹却也单一,难以望富特文格勒项背。
1958年,第一张立体声录音由费伦茨·弗里恰伊与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录制。或许受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中对第九交响曲提及的启发,库布里克在1972年的电影版中加入了弗里恰伊的录音片段,同时还采用了温迪·卡洛斯制作的电子版本。不料这段录音却掀起了1960年代的演出浪潮,包括乔治·塞尔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1961年),弗里茨·莱纳与芝加哥交响乐团(1962年)的版本等,指挥家们纷纷加入这场录制盛宴。最有影响的当数卡拉扬,1962年的柏林爱乐乐团的版本被认为是他五次录音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进入数字录音时代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CD的出现,指挥家们迎来了新一轮的录音热潮。据《ClassicFM》《Wired》等出版物报道,第九交响曲对CD格式本身也产生了影响。CD最初的74分钟容量据称是为了容纳整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而设定的。(这一说法一度被人认为是传闻,但至少是说法之一。)
无论如何,CD格式因其便捷性、音质的清晰度和宽广的动态范围而大受欢迎。听众在家中第一次能够以接近音乐厅的效果欣赏第九交响曲,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激烈段落。1986年,由君特·旺德指挥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受人瞩目。另一个录音事件出现在1987年,当时罗杰·诺林顿首次与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使用古乐器录制了第九交响曲,采用了大胆而快速的节奏。随着对这种“历史风格演奏”的兴趣增加,乐手们逐渐掌握了羊肠弦和无活塞号的演奏技术。此后又出现了几部新的古乐版第九交响曲,包括霍格伍德与古乐学院乐团的版本,赫雷维赫与香榭丽舍管弦乐团的版本,以及加德纳与革命浪漫乐团和蒙特威尔第合唱团的版本。然而听来听去,虽然几个古乐版本用接近当年贝多芬创作时所用的乐器和乐队编制,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本真”却难以呈现富特文格勒在德意志和人类面临灾难时所能表现出的那种独特的震撼。
音乐学家马修指出,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曲》是“永远在寻找契机的应景之作”。悖论在于,当我们将这些作品的意象用于理想与激情时,它们也许会被夸大,乃至沦为某种象征符号。但历史的关键时刻从来离不开贝多芬第九的加持与鼓动。如此,我们才有必要隆重纪念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200周年,并记住1824年5月7日首演这个伟大的日子。
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1929年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当时的意大利正被墨索里尼掌控。“我的思想是悲观的,但我的意志是乐观的,”他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为: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希望。观其一生,无论何时,贝多芬面对命运的挑战都无所畏惧。这也是第九交响曲的核心品质。葛兰西的精神可以用来诠释包括第九在内的贝多芬的许多作品,也可以使灾难来临之时,每一个人的心灯不会熄灭:“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克服它的勇气使生命值得一过。”
(谨以此文纪念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2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