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赵茜
2024年12月10日下午,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会同春风悦读榜组委会共同举行的2024年“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冬季榜”上榜作家正式揭晓,方晓位列其中。
方晓是典型理科生,大学专业是数学,当过几年数学老师,硕士才读了法律,毕业后转型做了法官,进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虽然从没学过文学,但他与文学的缘分早已注定,“要说开始写作,真没什么具体的契机,大学的时候待在校园杂志,那会看了很多小说、杂文,看得多了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试着写写,慢慢就养成了写作的习惯。”他这样谈及写作的缘起。
2006年,方晓第一次发表作品,成为一名写作者,至今已经创作近19年,发表小说百余篇。2015年,他入选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第三批成员。2021年,入选杭州市文联第十一批青年文艺人才。2021年,获储吉旺文学奖。
在短篇作品集《花好月圆》中,方晓用九篇作品,聚焦都市男女的感情和婚姻,聚焦两性关系中的那些不圆满与困境。在他的笔下,有随遇而安的淡然,亦有飘逸深邃的幻灭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得知上榜“浙江青年作家季度之星·冬季榜”,方晓想感谢这些年来浙江文学圈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从花落谁家到花落我家’,这个心理过程就是我的感受。帮助我的人们都是聪明人,自然早已知道我内心对他们的敬意,所以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另外一个感受是好好写,这才是对他们的回报。何况写作是这个世界最一本万利的事情之一,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没有理由不继续写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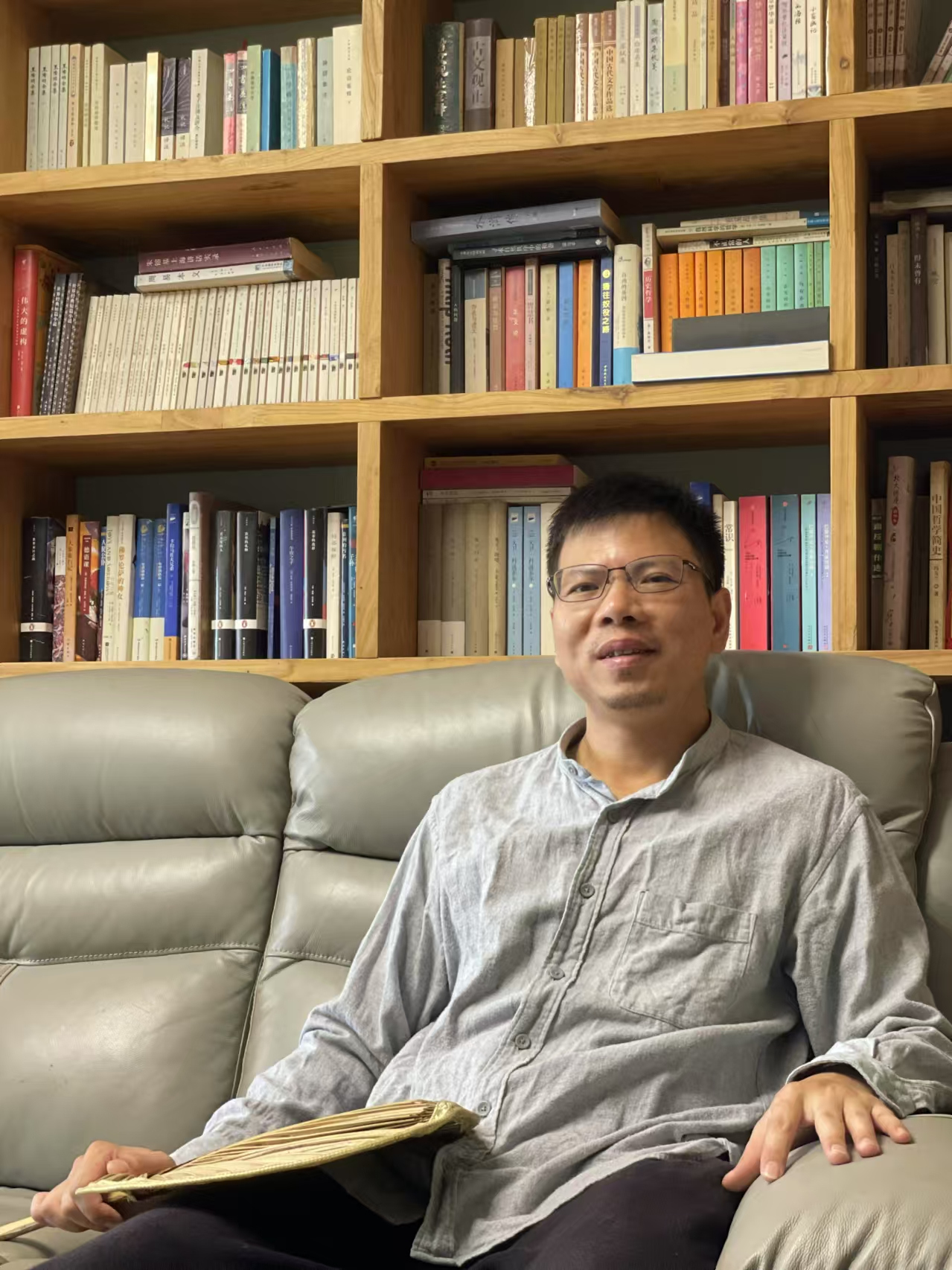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潮新闻:《花好月圆》里的九个短篇是怎样选择出来的?挑选过程中有没有经历很纠结的时刻?
方晓:选择从来不难。只要你手里有牌。这些短篇陪我度过了我的三十八岁到四十三岁。
我的写作风格这些年一直在变化,这很可悲,因为我还很难说自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风格。能自我安慰的只在于,虽然我每年写得很少,但应该自我相信在变化。唯“变”不死,那也就姑且认为变化等同于某种进步吧。
我喜欢的是《无人幸免》。它是《李得先生》系列中的一篇。
有位读者朋友说它有种迷幻感。他用语很精准,我想这也正是我喜欢的原因。
我现在喜欢更抽象、更寓言性的短章,既和我没有太多时间写作有关,更可能是哲学侵蚀了我的文学观,而出于偷懒我并不打算对此进行反抗。
我不再详实地描写生生死死的爱与恨,但我自觉《李得先生》系列里的人物在模糊而荒诞的人生境遇中,更真实、悲悯、无助又不得不自我赐予希望地活着,并且努力活下去。
潮新闻:法律行业的从业经历如何影响您的文学创作?
方晓:没有人愿意很正式地谈论自己的职业,尤其是如果只用它来养家糊口的话。如果加上“被迫”两个字更能说明什么,我觉得加上也无妨。
我经常对律师朋友表示羡慕,他们会参与一份合意的酝酿、磋商、订立、友好履行的过程,充满善意、谦抑、包容、期待和成就。而我见证的只有合同解除、公司解散,破坏与毁灭。
连看够了生老病死的医生都是值得我艳羡的对象,毕竟他还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生。
那些虚假、背约、恶意、因果日复一日在我面前上演,仿佛世间万事不过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你不知道还要坏到哪里去,你必须亲手斩断它,似乎只有判决终止一切权利义务,才能阻止它更坏下去。
你几乎不能改善分毫。
也有娇弱的柔情小花在情感灰烬之上悄然生长起来,一起离婚案件,法官在询问一对儿女跟随谁生活的意见时,姐姐说,“弟弟跟爸爸我就跟妈妈,弟弟跟妈妈我就跟爸爸”,弟弟说了和姐姐一样的话,但又补充说,“其实我是想跟爸爸的,因为妈妈结扎了,妈妈担心爸爸再婚生孩子,就不要我们了。”
话中蕴含的诸多情感,我相信并无一个字解释的必要,所有人都能体悟,而这就是对我而言最可谓温暖的东西了,人的情感是人世间最不可辜负之物。
我面前的法律场,是矛盾最集中之地,情感最爆发之地,人性最凸显之地,本身就已经具足了小说最核心的必备要素,但我直到现在,从文学意义来说都只是一个旁观者,来不及或者更准确地说暂时还不想化到我的小说中去,我宁愿离它们远远的。
如果有人非要说,法律职业塑造了我这个人,从我确实不能反过来塑造我的法律职业这点来说,我也无从反对。毕竟你与别的什么东西总归可能是一种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
但如果有人要进一步声称,法律职业从而也影响了我笔下塑造的人物,我却是要毫不留情地举起双手不赞成。我认为我笔下的人物只会更抽象、更本真、更具有寓言气质。人物在故事背后,而故事永远在案件背后。
至少我无法明确评断法律职业在我写作上的意义,说它毫无影响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从来没有从事过它,我的人物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小说写作给了我一种观察的习惯和角度,在断案中这是有用的,而且几乎可以说,它能赋予我直觉,引领我直击真相和软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潮新闻:您说过,“临界”是您喜欢的一种选择。
方晓:枪响之前,是运动员最有爆发力的时刻。在拒绝爱的话语出口的前一秒,在导弹发射按钮按下的瞬间。
临界,所以有了后续的千万种可能性。
“如果当时我不那么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过太多类似的话语,是不是?
无论选取故事的一个横截面,或者在故事已然终结的地方想象缓慢展开翅膀,还是从故事的中点开始往回走,这些形式无关紧要,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悬而未决不是更有故事性吗?
我想这不是一种风格,更多的是一种自觉选择,如果说成是习惯仍然不能表达选择主动性的话,也可以说成是一个小说家应该具备的本能。对我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至少得用五万字回答,但这里我只提一个名字,格拉斯。他从第二章开始创作了一部真正伟大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这在现代小说中几乎无与伦比。
我曾经用四年时间只读这一本书。后来我也读了格拉斯的其他长篇小说,可惜读不下去。我想我的苛责就是对格拉斯最大的尊重:你无法忍受一个伟大作家的哪怕一丁点平庸之处。
潮新闻:翻看您的作品集,感觉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是围绕“爱而不得”展开的。
方晓:难道爱而不得不是爱情的最好状态吗?这也是临界的一个具体截面。
爱情停留在被毁灭之前。那么也就是说,爱情始终保鲜在它最美丽的状态里,叔本华的那句话太耳熟能详了,我认为它太残酷,以至于哪怕不接近文学作品的真相,也接近现实生活的真相。
如果我们表示不愿意承认,那也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知道再也没有比它更真实的了,所以我不打算重复那句像钟摆的那句话,时间的钟摆永恒,无聊、痛苦与厌烦也总在那里。
请原谅我还是说出了这几个词语,就像也得请你原谅我将爱情作为写作的切口,不然我还能以什么为切口呢。除掉美好,爱情还是人世间最奇妙的情感啊,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人,突然从某一个时刻起愿意彼此生死与共,简单而纯粹。
人的情感尽管复杂又模糊,但一定是真实的,写出真实本身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问题也许是,如何写出真实,且不自我限制。但既然这个问题你没有明确问出,我也就不大费周章地回答了。抵达,是一个过程,任何属性的过程都天然潜带着技巧性的。当你自以为不了解世界时,你就反观自身好了。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写作者自己,这话显然偏激之极,但如果你把真实的自己写到极致,一定不会错过心灵的真实。
潮新闻:现在您正在创作什么小说?未来,您有没有想要尝试的风格和题材?
方晓:我正在写一些不合大众口味的小说。这里的“大众”只祛除了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人。
《李得先生》系列就是我的起点,我认为它能够带领我进入一个和一千零一夜一样的幻象世界,它会继续向爱伦坡、马尔克斯、卡夫卡慢慢靠近,同时与爱丽丝门罗、威廉特雷弗挥手作别。但我仍然会随身携带着所有伟大作家曾经馈赠给我的浅淡的影子,绝不忍心丢弃。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