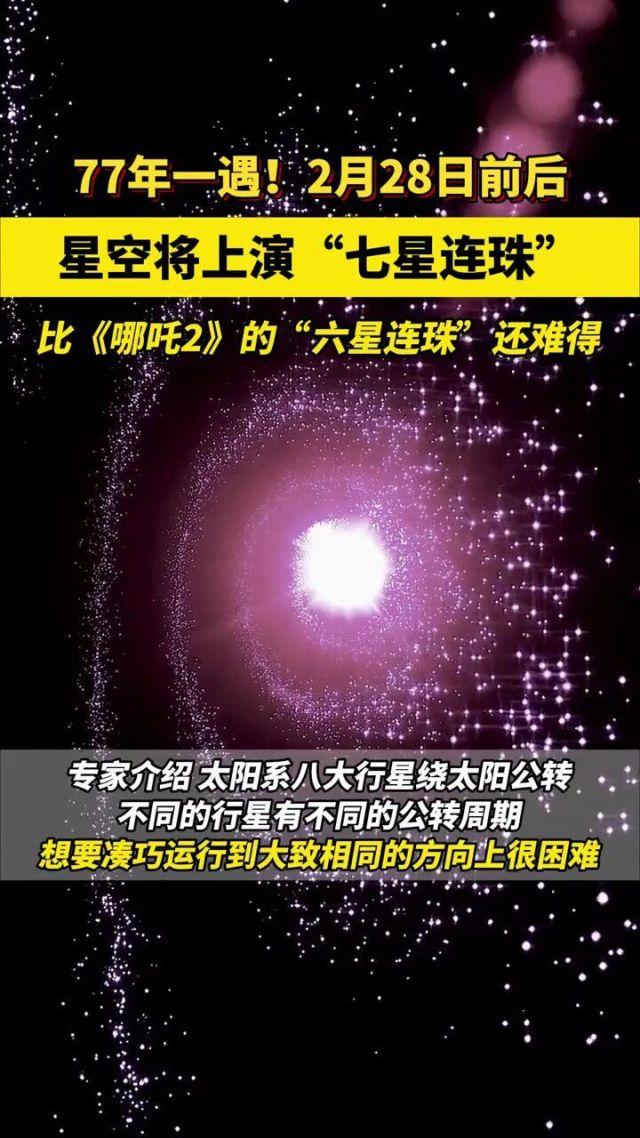医生正在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移植到患者体内。
■本报记者张思玮
如果异种移植在2024年只是“黎明破晓”,那么2025年或将“光耀大地”。
自今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以创新性新药方式批准联合治疗公司的UKidney异种肾移植临床试验申请,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线上公布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治疗终末期肾病病例死因,再到美国第四例猪肾移植患者术后仅一周便出院的消息公布,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异种移植再次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的热点话题。
不可否认,异种移植已经从科学幻想走向临床实践。终末期肾移植患者用上“猪肾”已指日可待。
“这主要得益于基因编辑、免疫抑制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异种移植临床应用的可行性日益增强。尽管如此,异种移植的临床应用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中国科学院院士窦科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要真正实现异种移植的临床应用,仍需解决免疫排斥反应、生理兼容性、病原体跨物种传播,以及伦理和法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有望解决供体短缺问题
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慢性病和终末期器官衰竭病人的数量日益增多。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却受限于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在此背景下,异种移植作为一种潜在的替代方案,展现出弥补器官、组织和细胞供需缺口的巨大潜力。
异种移植是将动物源性的活细胞、组织、器官以移植、接种或注射的方式植入人体的过程。猪因其生理特性与人类相似,被认为是理想的供体动物。同时,基因工程为修饰猪器官提供了契机,大幅度提高了猪器官与人之间的免疫和生理相容性。
早在2021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移植外科教授Montgomery团队宣布,他们成功将基因编辑后的猪肾移植给了一名脑死亡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同济医院器官获取组织首席顾问陈忠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临床异种移植,只能说是一种介于动物实验与临床研究之间的“亚临床试验”。不过,这一特殊模型的建立和试验研究是非人灵长类动物(NHP)实验与临床研究之间必不可少的“桥梁”。
直至去年3月16日,美国麻省总医院实施了世界首例真正意义上的猪肾移植手术。手术治疗团队向FDA提出申请,以“同情医疗”方式为终末期肾病患者里克植入了一枚被基因编辑的猪肾。据悉,该猪肾经过69处基因编辑,包括删除3个异种抗原、灭活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PERV)并插入7个人类转基因。
患者术后52天去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公布其死亡原因。患者有重度冠状动脉疾病和心室瘢痕,但无明显的异种移植物排斥反应,推测死因可能是室性心律失常。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开展异种移植的信心。”陈忠华表示,从现已实施的4例异种肾移植情况来看,近期内免疫抑制方案基本有效,免疫排斥反应的风险基本可控,但因样本量有限,后续仍需开展更为精准的研究。
不过,从现已实施的异种移植手术来看,主要集中在肾脏与心脏,鲜有肝脏。究其原因,窦科峰表示,肝脏具有极其复杂的功能和免疫原性。
此前,窦科峰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主导了国际首例基因编辑猪-脑死亡患者异种原位全肝移植手术。他表示,我国是“肝病大国”,肝移植的需求量远超其他国家,亟待扩充肝移植供体。因此,探究异种肝移植的基础理论、开展相关的亚临床和临床试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直面免疫排斥反应问题
其实,不管是同种移植还是异种移植,都必须直面免疫排斥反应问题,异种移植尤甚。而这也是移植成功的关键。
窦科峰表示,可能出现的免疫排斥反应主要包括抗体介导的超急性排斥反应(HAR)、急性体液异种移植排斥反应(AHXR)和细胞介导的急性细胞异种移植排斥反应(ACXR)。
不过,研究发现,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敲除αGal抗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异种器官移植中的HAR问题。而后续发展形成的GGTAl/CMAH/β4GalNT2三基因敲除(TKO)策略,已经在异种移植相关亚临床、临床试验中被广泛运用。
在世界上首例猪肾移植术后,即便是患者里克生前(术后第34天)的最后一次活检,也没有发现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证据。
“这说明,经过基因改造和免疫抑制治疗,异种肾可以在短期内为患者提供维持生命的基本功能。”陈忠华说。
尽管如此,现今的基因敲除策略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异种移植学者仍需更深入地解析人和NHP基因组的差异,开发出最适用于人类的基因编辑策略。”窦科峰表示。
解决生物适配性与跨物种感染问题
生理学差异是影响异种移植物存活的另一个主要障碍,物种间的生理学差异影响了凝血功能。目前,利用基因修饰技术在供体猪中表达人凝血调节蛋白(hTBM)已成为治疗凝血病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窦科峰表示,未来的研究需要着眼于探索具有更高效力、更小副作用且能精准调控凝血系统的新型抗凝药物,以更好地满足异种移植临床应用的需求。
此外,器官大小不匹配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也引发了广泛关注。比如,在美国纽约大学报道的2例心脏移植病例中,其中1例病人在术后24小时出现乳酸升高、血压降低和心脏功能衰退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受体和供体心脏大小不匹配,进而造成移植物组织灌注不足。
“除了注意移植后的出血、凝血问题外,还应采取综合疗法来限制移植器官的生长和肥厚。”窦科峰说。
猪病原体的跨物种感染是异种移植后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PERV是焦点。几乎所有猪都携带这种病毒,然而其对人类的潜在致病性仍不清楚。
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首例猪肾移植手术主刀医生之一、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莱戈雷塔临床移植耐受中心主任TatsuoKawai团队利用靶向核酸检测和宏基因组测序对患者体内动物源性病原体进行了全面监测。在整个临床病程中,没有检测到猪源性病原体。陈忠华指出,该团队使用的猪由生物技术公司eGenesis研发,已用基因敲除方式使PERV失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异种移植没有人畜共患病传播的风险。特别是由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病毒可能重新被激活。
窦科峰认为,目前在监控跨物种感染方面可以做的主要工作是,对出现感染迹象的受者采取血培养、放射学和侵入性检查,以及系统保存检测样本、实施严格感染控制等措施。今后,随着临床数据不断涌现,感染监管和控制指南将不断更新。
突破生命的界限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期异种移植的曝光度持续增加,公众的接受度逐渐上升。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中,我国公众对异种肾移植的接受度达到了71.3%。而在482例肾移植等待者群体中,异种肾移植的接受度更是上升至87.6%。
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异种移植与同种移植的效果相同时,有42%~80%的病人能够接受异种移植。
窦科峰指出,尽管如此,异种移植大规模应用于临床之前还需要解决一系列伦理问题。首先是PERV等跨物种病毒传播的风险,其不仅涉及接受者个人,还可能影响到更广泛的人群,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疫情。其次,为预防病毒传播,还需长期监测受体及其密切接触者,这与参与者的自主权和隐私权相冲突。
此外,异种移植还涉及对动物的利用和福利问题。具体而言,用于异种移植的动物需在严格管控的环境中生存,这极有可能对它们的自然行为及情感状态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异种移植技术的运用或许会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窦科峰认为,有必要制定清晰明确的伦理指南和完善的法律框架。
“目前,每做一次异种移植都是在为后续异种移植进入临床积累宝贵经验。异种移植的进步是推动现代医学进入全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在陈忠华看来,在这场跨越物种的生命接力中,医护人员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一步步突破了生命的界限。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不仅关乎医学进步,更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