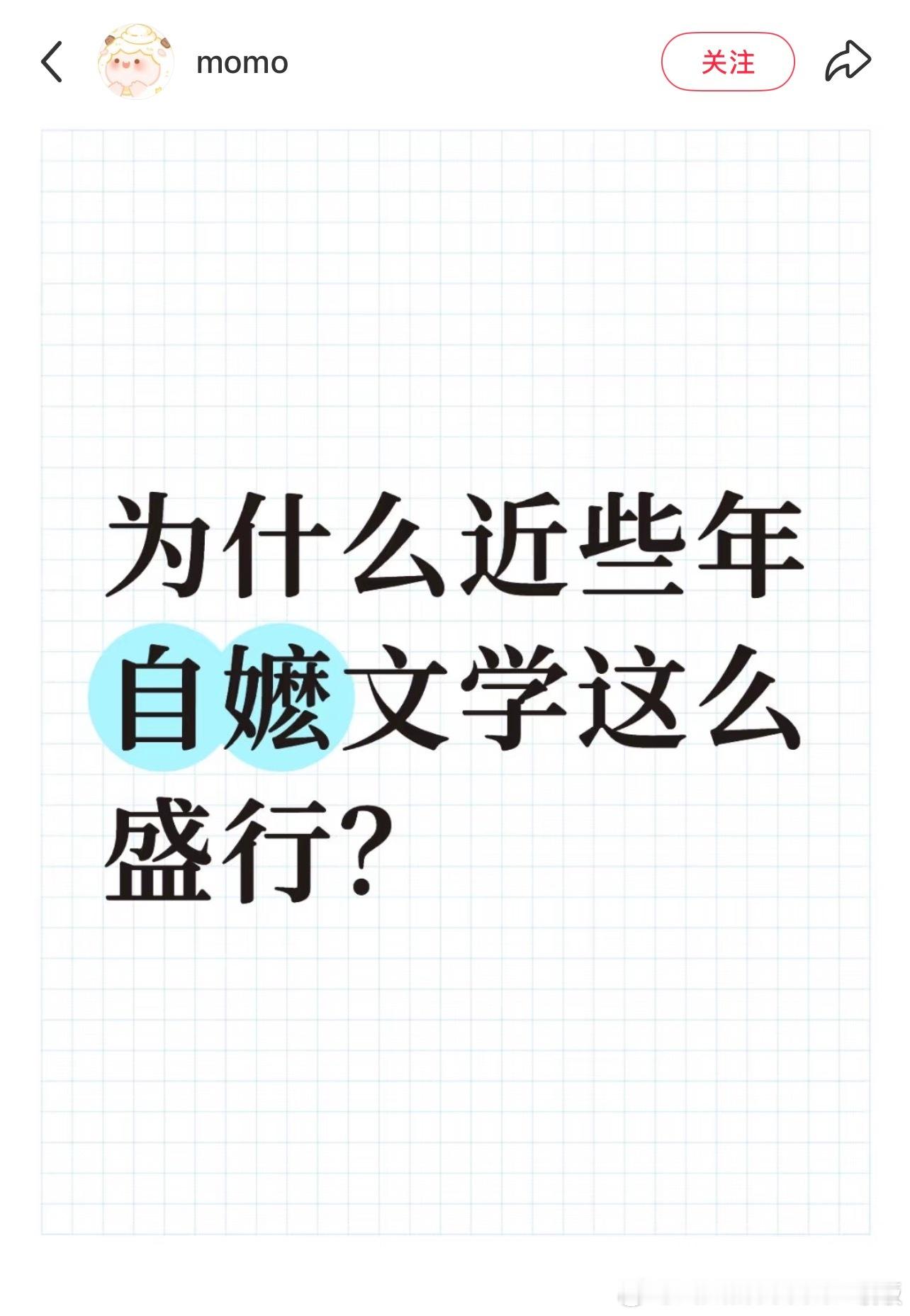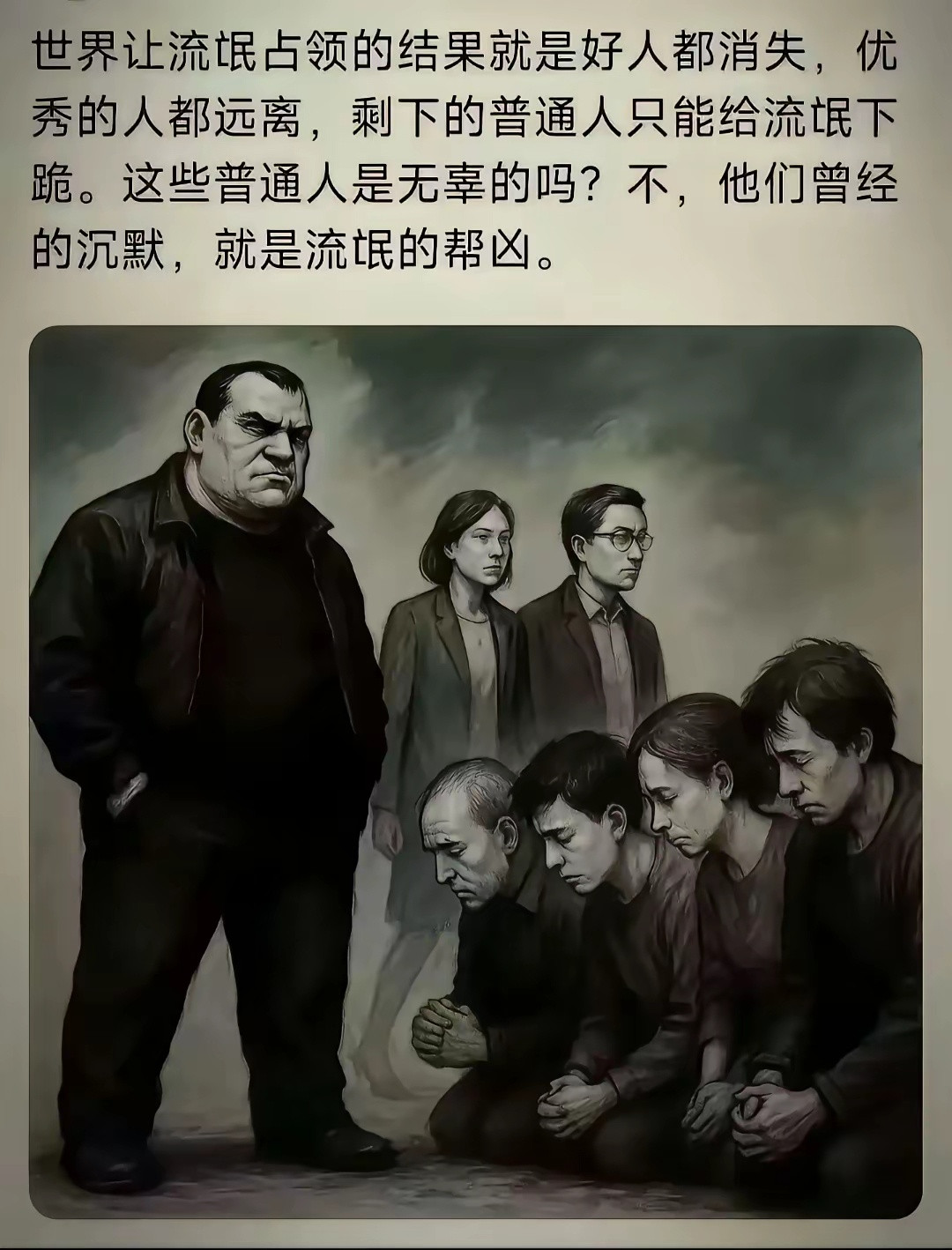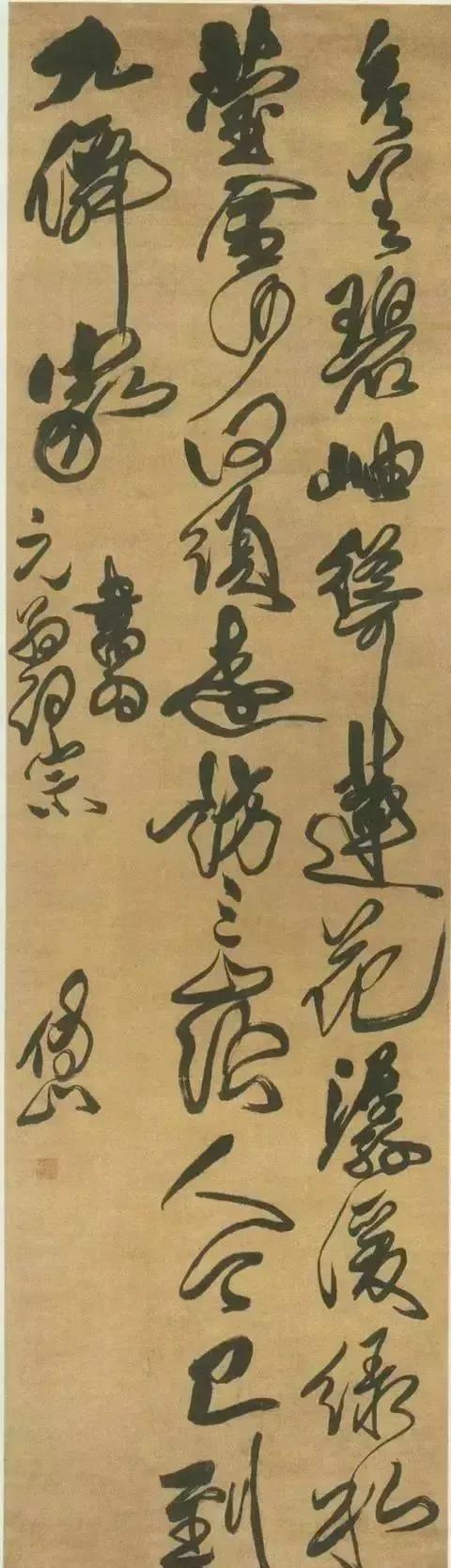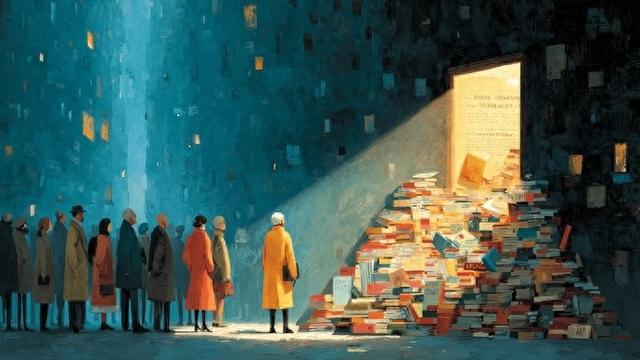

主持人语
夏日的一个周末,我坐在杜厦图书馆,找来那些没被借走的书,《微尘》《我在北京送快递》《在菜场,在人间》《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我曾是一名饲养员:流浪东北的日与夜》等等。我读得很快,也时不时走神,这是我在文学史上没有学到的内容,但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一定有他们的一页。我们现在,称呼他们为“素人写作”。
我好奇的是,大家真的认同“素人写作”这个概念吗?又如何看待“素人写作”的火爆出圈,觉得这其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相关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又让既有的文学环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此之外,我们对于“素人写作”或者说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霍艳老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钟媛老师和《当代文坛》杂志社刘小波老师的支持,他们对“素人写作”的话题有研究、也有思考,更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是大众写作中被看见的“素人”,而“素人写作”所代表的,是没有被我们看到的千千万万的“素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探讨才刚刚开始。
——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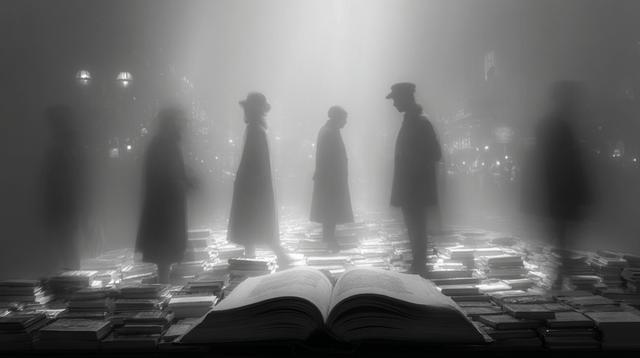
素人写作:消失的审美距离,拉近的受众距离
文/刘小波
素人写作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写作和出版现象,具有较高的自发性和大众参与性。其作者多为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未经过专业写作训练的普通人,以书写自身故事和自我体验为主,内容偏重个人经历和真实故事,且多为基层叙述。2010年,《人民文学》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首次明确征集“普通写作者”作品,为素人写作提供了早期平台。其实这一栏目的开设和当时互联网上涌现出众多的普通作者不无关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绝大部分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写下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在合适的时候就有可能变为他者所共情的文学。素人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的胜利,与其说这些写作是文学,不如说他们是传播事件更为贴切。素人写作存在于文学的每一历史时期,但是只有在当下所处的媒体时代才有如此的轰动效应。秦秀英《胡麻的天空》借助微博广泛传播,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通过微信大火。其实这些所谓的素人,已经坚持了多年的文学梦了,只是在这样一个微传媒时代才有机会被大众所熟知。微信、微博、豆瓣、抖音、知乎、快手、B站这些都是素人写作发表传播的主阵地。素人写作的影响力得益于传播的魅力,自来水效应。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走红的事件本身和文学有多少真正的关联。此外,素人写作除了媒体的推动,也有出版的加持,很多出版策划推动了这一提法的流行,有刊物和出版社直接冠以素人写作的名号,并以此进行营销宣发。
素人写作是对传统写作的一种“冒犯”,是作为“刺点”的写作,但这并非贬义,正是这一个个的“刺点”,让文学不至于彻底被人遗忘。单从文学性角度而言,素人写作并无多大创举。从体裁上看,素人写作基本选择了非虚构、散文和诗歌这些门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讨论文学几乎都落在小说上,小说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学,但另一方面,大众热衷传播和讨论的,却是诗歌、散文和非虚构这些体裁。素人写作几乎都未染指小说,仅有个别作家在经过了长期文学训练之后才偶有小说创作。当然,小说在很多人眼中也不过是“编故事”,但其仍有一定的门槛,而诗歌、散文和非虚构这些体裁门槛较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写下来,成为非虚构,也可以加入一些大众的共通情绪价值,就成为散文,还可以把散文分行,变成诗歌。这些文字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是属于普通大众的共通心理,阅读这些文字和浏览图文并茂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刷视频并无太大的差异。
素人写作的选题也相对单一,比如某杂志最近推出的素人写作栏目,相继刊发了清洁工、外卖骑手等相关的作品,这些都是素人写作的常规选题,也是外卖员、快递员等写作火了以后产生的效应。平台需要抓住流量,作者则需要蹭一下热度。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转变,写作技法被拔高到很高的地位,近些年来创意写作持续升温,专业的作家培训成为主流,而这些素人写作则又回到“写什么”的路子上去,他们的笔下总能发现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这是一种贴地飞行的状态,但是同样也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从日常生活领域来看,许多素人作者常聚焦于平凡琐事,这类题材因其贴近生活易被选用,但也因缺乏独特视角而重复出现。久而久之,难以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和独特的阅读体验,自然也会限制其发展。
素人写作的一大共性就是审美距离消失,作品与受众的距离拉近了,这些自叙传模式的创作大都如此,由于艺术品与受众之间的审美距离消弭掉了,读者不需要经过二度加工、二次叙述,甚至不需要思考,只会一拍即合,所谓“对,这就是我的感受”。有论者指出,最近各种文艺“爆款”的背后必然是广泛的共情,是否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渐渐成为大众文艺能否被接受的新逻辑。不过,还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共情的内容和日常生活没有明显区隔,如果文学不能有超越性的东西,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重复的文学呢?
近年来,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互动让人人写作成为现实。但不管是谁在写作,文学应该有检验自身的标准,也有恒定不变的准则,大众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消费娱乐,但文学的本性仍需保留。快餐性的文字只会随着下一位网红的出现而被取代,而经典的作品是无法被取代的。当前文艺创作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互动性逐渐超越审美性成为主导创作的逻辑,话题性甚至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这种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突出,创作者为了吸引注意力,往往优先设计具有争议性、有话题性的选题,而非专注于艺术形式本身的精雕细琢。互联网的热点只是短暂的,许多爆款作品在传播一段时间后迅速被遗忘。当受众的审美期待被互动性迎合时,整个文艺生态可能陷入“流量内卷”,最终损害的是艺术创作的本真性。
素人写作的价值可能更多的是在读者这一端而非作家一端。从创作端而言,素人写作虽然普遍缺乏文学的高超技艺,文本的文学性较为匮乏,但是凭着对生活的深度领悟,往往能够发现那些被遮蔽的点,形成一般写作有效的补充,为主流写作提供更多的选题参照。虽然这些素人写作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多年以来坚持文学阅读,“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合格的读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状是,文学读者群体的萎缩。无论是作家群体、期刊刊载作品还是文学类的图书出版的量,当下时段几乎都是有史以来的最顶峰,但还是给人一种感觉,文学影响力下降了,其根源在于读者群体的萎缩乃至消失。而素人写作的持续火热,一方面能够吸引部分读者的回归,另一方面这些写作者本身就是忠实的文学读者。素人作家群体获取文学创作技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量的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的养料,正是在大量的阅读基础上才有了创作的冲动和尝试,也让部分作者得以走红。大量的写作者籍籍无名,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梦,永远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而存在。不少素人写作者还参加了各种文学社群,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以传帮带的形式巩固着最基础、最稳定的读者盘,这本身就已经是最美丽的文学风景了。
素人写作的勃兴是媒介技术革新、文化生产机制转型以及公众情感结构变迁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媒介逻辑主导下“传播事件”的胜利,也是个体生命经验寻求表达共鸣体的草根实践。一方面,它以“刺点”的姿态闯入已经相对封闭的文学场域,凭借原生质朴的生命力构成了一种对传统写作的“冒犯性”补充。另一方面,其内在局限亦不容忽视。素人写作要想突破怪圈,需要在生活原真书写的基础上,保持文学性的追求。既不丢生活根基,又不失文学灵魂,实现共情与超越的兼顾平衡。
(作者系《当代文坛》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