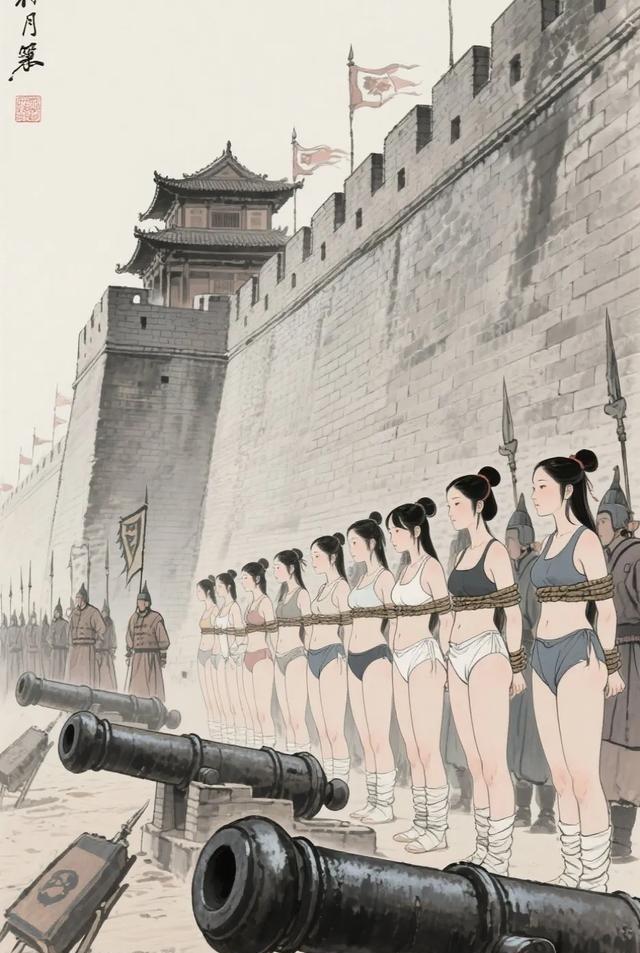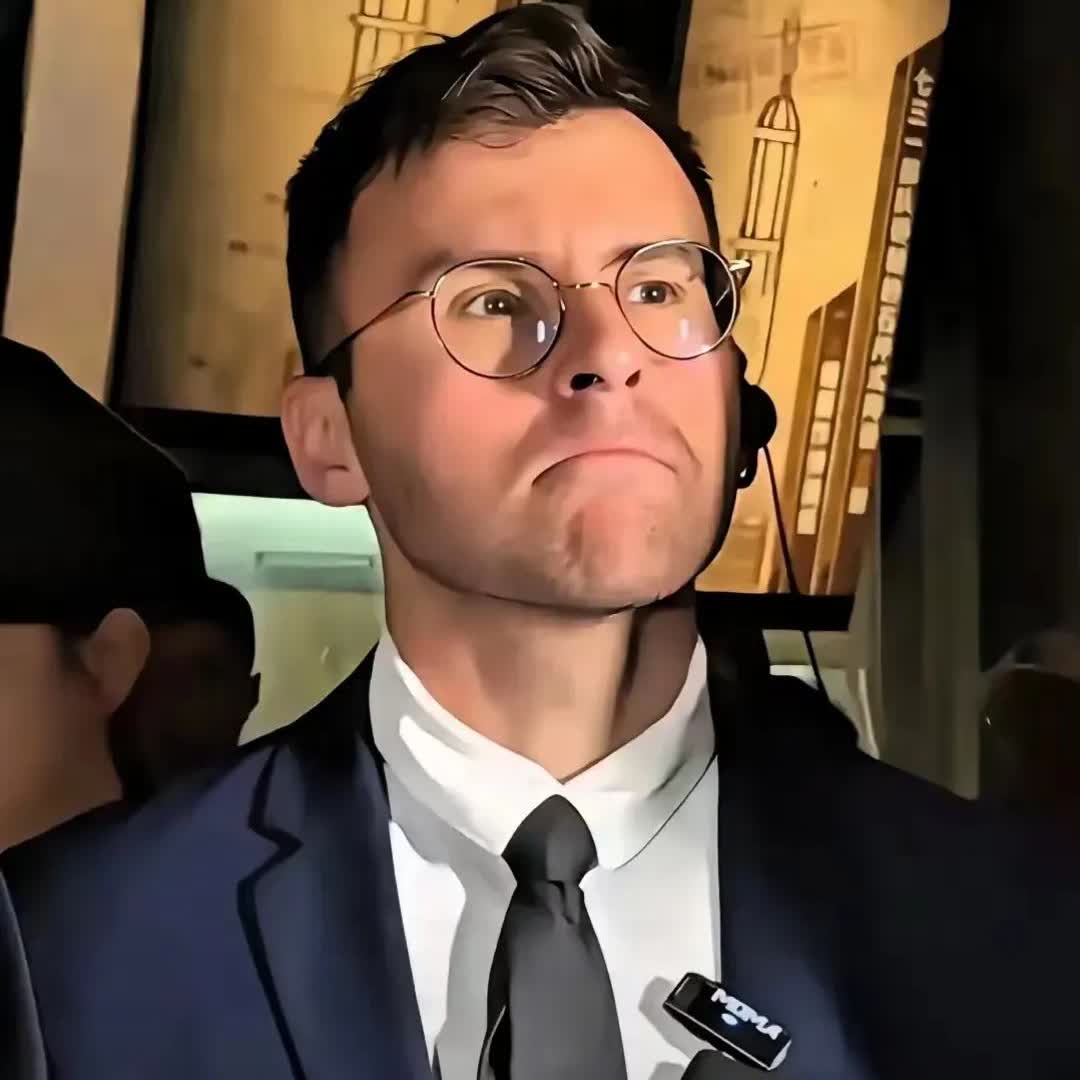1834年,52岁道光皇帝陪着全贵妃吃晚膳,而在一旁侍奉的18岁宫女,让皇帝心中躁动不已。全贵妃便说:“万岁爷,今晚不要走了,就让我的宫女陪你侍寝吧!”道光直夸全贵妃懂事,晚上留宿全贵妃宫中。 银烛的光透过茜色纱帐,在描金拔步床上投下细碎的影。全贵妃亲手给道光剥着荔枝,指甲上的凤仙花汁红得鲜亮——这是她刚得的新方子,说是用岭南的胭脂花调的,比宫里的玫瑰汁更显色。宫女春桃站在案边添酒,袖口磨出的毛边蹭过青花酒壶,发出细不可闻的声响。她垂着头,能看见皇帝明黄色龙袍的下摆,绣着的十二章纹在烛火下忽明忽暗。 “你叫什么名字?”道光突然开口,春桃手一抖,酒洒在紫檀木桌面上,顺着纹路洇开。全贵妃笑着打圆场:“这孩子是去年从苏州选上来的,叫春桃,手脚笨了点,胜在干净。”她说着给春桃使了个眼色,“还不快给万岁爷换盏新的?” 春桃退到外间换酒盏时,听见里屋传来全贵妃的声音:“万岁爷最近为了漕运的事劳心,今晚就让春桃给您按按肩。这孩子手巧,前儿个给我捶腿,倒比太医院的按跷还舒服。”她捏着冰凉的酒盏,指节泛白——来宫里三年,她早就听说过,主子们把宫女送给皇帝,就像把桌上的点心递给客人,从来不用问当事人愿不愿意。 掌灯时分,春桃被太监领到偏殿。这里的被褥都是新换的,绣着并蒂莲,可她摸着却像摸着冰块。一个老嬷嬷进来,往她手里塞了个玉坠:“这是贵妃赏的,记住了,今晚不论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都烂在肚子里。明儿要是能讨得万岁爷欢喜,你这辈子就不用再做粗活了。”老嬷嬷的指甲在她胳膊上掐了一下,“要是惹得万岁爷不高兴,咱们浣衣局的冰水,冬天也是能淹死人的。” 道光进来时,带着酒气和龙涎香。他坐在床边,打量着站在角落的春桃,像打量一匹刚进贡的绸缎:“抬起头来。”春桃慢慢抬头,看见皇帝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饭粒,突然想起老家的爹——去年家书里说,爹在田里插秧时摔断了腿,弟弟还等着她的月钱买药。 “你会唱苏州小调?”道光拉过她的手,那双手常年搓洗衣物,指腹上有层薄茧。春桃“嗯”了一声,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她唱起小时候听来的《茉莉花》,唱到“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时,看见皇帝闭着眼,嘴角带着笑,不知是想起了年轻时的事,还是单纯觉得悦耳。 第二天卯时,春桃被送回全贵妃宫里。全贵妃正对着镜子描眉,看见她进来,从妆匣里挑了支银步摇:“昨儿个万岁爷夸你了,说你性子静。这步摇你戴着,以后就不用去外间伺候了,在我内殿当差吧。”春桃摸着头上的步摇,冰凉的银链贴着脖颈,像昨晚偏殿里的月光。 可她没得意多久。半个月后,道光再没来过全贵妃宫,倒是内务府送来新的宫女名册。全贵妃翻着册子,突然对管事嬷嬷说:“春桃这阵子看着没精神,让她去圆明园的花房当差吧,那里清净。”春桃收拾东西时,发现那支银步摇的链子断了,她没修,就那么揣在怀里去了圆明园。花房的老太监说,前几年也有个宫女被皇帝临幸过,后来被派去守皇陵,再也没回来。 这段故事听着像那么回事,却藏着对宫廷生活的刻板想象。道光在史书记载里是出了名的节俭,龙袍都打补丁,连御膳房的鸡蛋都嫌贵,不太可能在饭桌上对宫女“躁动不已”;全贵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全成皇后,她能从贵人做到皇后,靠的是智谋而非“懂事”——她给道光出的漕运改革主意,至今还记在《清宣宗实录》里,哪会把心思花在送宫女这种小事上。 更有意思的是,人们总爱编这类“宫女被临幸”的故事,好像宫廷里的女性关系,只能用“争宠”“送礼”来解释。全贵妃和道光之间有政治默契,春桃这样的底层宫女有生存智慧,这些都比“皇帝动心、贵妃送礼”的戏码更有嚼头。可大家好像更愿意相信,后宫里只有情爱纠葛,忘了那里的女人,首先要学会在权力的缝隙里活下去。 还有那些像春桃一样的宫女,她们在史书里连名字都留不下,却成了野史里的“艳遇主角”。没人问她们愿不愿意,没人管她们后来怎么样,就像没人在乎花房里的花,开过之后是被晒干还是被扔掉。可她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有老家的爹娘要牵挂,有没说出口的心愿,不该只成为别人故事里的背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