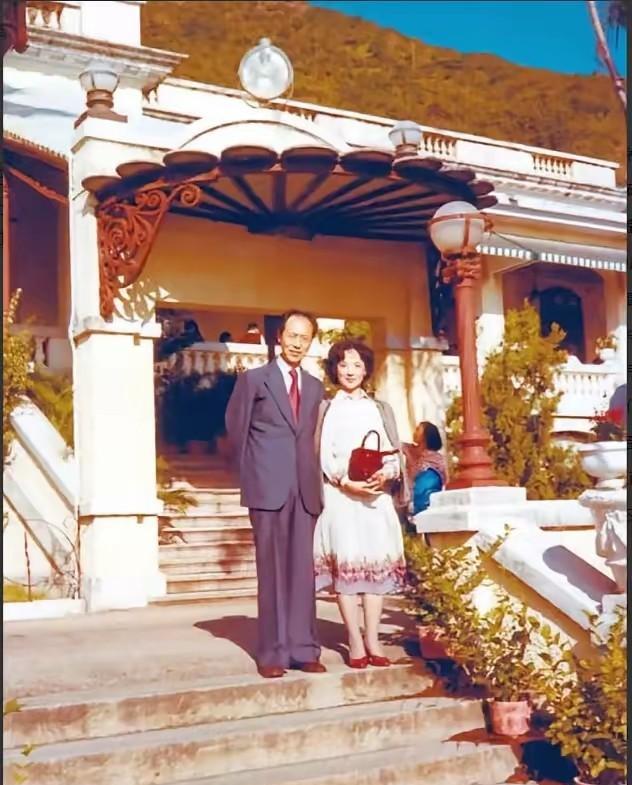1938 年,128 师俘获数名日军。下属请示师长王劲哉如何处置。王劲哉没有任何犹豫,当即下令:“绑树上,让新兵练刺刀,壮胆!” 下属面露难色。 王劲哉正往汉阳造的枪膛里压子弹,听见下属嘀咕 “娃太小”,手指猛地一顿。 作战地图上,日军标注的 “清剿区” 红得扎眼,那是从战死少佐身上搜的,三个被圈住的村落,此刻已在浓烟里化为焦土。 他想起今早从芦苇荡抬回的李太婆,七十岁的人被刺刀挑在门槛上,手里还攥着给孙子留的糖块。 目击者说,动手的鬼子里就有个这么大的娃。“小?” 他把枪往桌上一拍,陕西口音带着火药味,“他捅人时,咋没嫌李太婆老?” 下属蹲在俘虏堆前,看着那个日军娃娃兵。军装罩着瘦骨嶙峋的身子,脖子上挂着褪色的千人结,冻裂的手里攥着半块米饼。 可这双手,三天前刚点燃了沔阳南乡的茅草房,火光照亮了他们狞笑的脸。 远处新兵营传来操练声,二十多个庄稼汉挥着刺刀,动作僵硬得像木偶,他突然懂了:王师长要的不是杀人,是让握惯锄头的手,敢握住保命的刀。 新兵栓柱的刺刀在手里抖得像秋风中的芦苇。他爹被日军铡死在村口,人头挂了三天,可面对绑在树上的日军,他腿肚子转筋。 王劲哉走过来,解开绑腿露出小腿的伤疤:“土匪砍我时,我跟你一样抖,结果眼睁睁看战友被捅死。” 他把绑腿缠在栓柱手上勒紧,“现在抖是怕沾血,将来抖就是怕脖子上架刀!” 话音未落,日军娃娃兵突然挣扎,嘴里喊着 “天皇万岁”,试图扑向地上的枪。 王劲哉一脚将枪踢飞,靴底碾过枪栓:“看见没?他们的胆,是用咱老百姓的血喂大的!” 栓柱的眼泪砸在刺刀上,猛地嘶吼着扑上去,刺刀没入日军胸膛时,他自己也瘫在雪地里,却死死攥着刀柄。 夕阳把芦苇荡染成血色。王劲哉坐在土坡上,看新兵们轮流上前,有人吐了,有人哭了,没人后退。 他摸出烟袋,烟叶是从李太婆烧焦的屋里找到的,纸包里裹着半块咸菜。 “你说,那娃的娘知道他在这儿杀人吗?” 风卷着血腥味掠过,下属没敢接话,只看见他指节捏得发白。 夜里,哨兵见王劲哉在俘虏尸体旁站了很久。他给娃娃兵整理衣襟,把搜出的千人结放在他胸口 —— 樱花图案已被血浸黑。 “都是娘生的,可惜投错了胎。” 第二天,日军钢盔被挂在营门,红漆写着 “练胆专用”,新兵每天对着刺一百下,直到刺刀能精准穿过盔顶弹孔。 三个月后侏儒山战斗,这些新兵成了日军的噩梦。栓柱端掉机枪巢,刺刀捅弯了用枪托砸,浑身是血仍往前冲。 战友在他口袋发现半块焦咸菜,纸包上有李太婆的针脚。王劲哉看着咸菜,想起栓柱哭着说 “俺爹该夸俺了”。 汉口洋记者骂他 “违背伦理”,电报来时,王劲哉正分发日军罐头。 他把电报揉进罐头盒:“让他们看看,这肉是从哪个村子抢的!” 新兵啃着罐头,眼里的光比太阳旗亮。 瞎眼老太摸王劲哉的手:“你杀了人,也护了人。” 她不知道,师长常对着千人结辨认针脚,那结缝得潦草,像母亲匆忙的牵挂。 1939 年潜江战役,日军新兵蹲战壕里哭,王劲哉用枪托砸晕他带回。 “留着练胆,别往死里捅。” 下属不解,他望着远处重建的茅草屋:“总要留点念想。” 日军军官日记写道:“128 师的兵眼里只有仇恨,太可怕。” 王劲哉把日记给新兵看:“他们怕的不是刀,是咱不敢死的胆。” 《湖北抗战史料》记,128 师三年百余战,未丢一寸百姓聚居地。栓柱成英雄,刺刀刻着二十三个缺口,对应着二十三个被救下的村庄。 档案馆里,王劲哉未寄的家书写:“我杀了人,夜里常梦见他们。可护着的人能好好活,值了。” 信纸边角皱着泪痕,日期正是下令练胆那天。 芦苇荡的风,诉说着血与火的过往。王劲哉的狠,是日军逼的,是百姓泪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