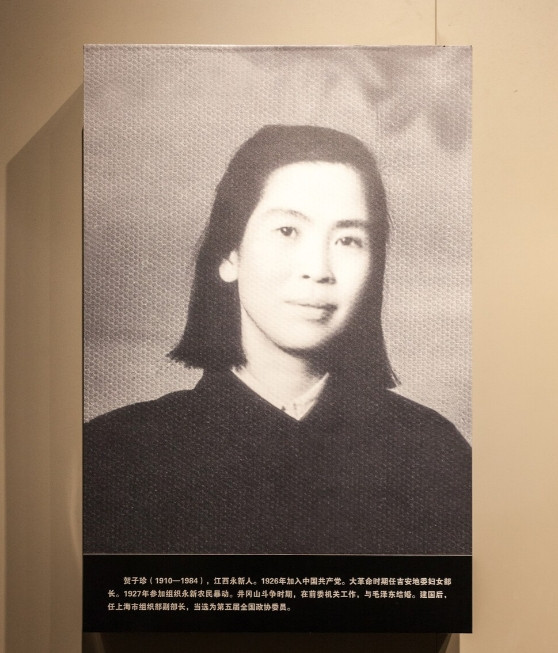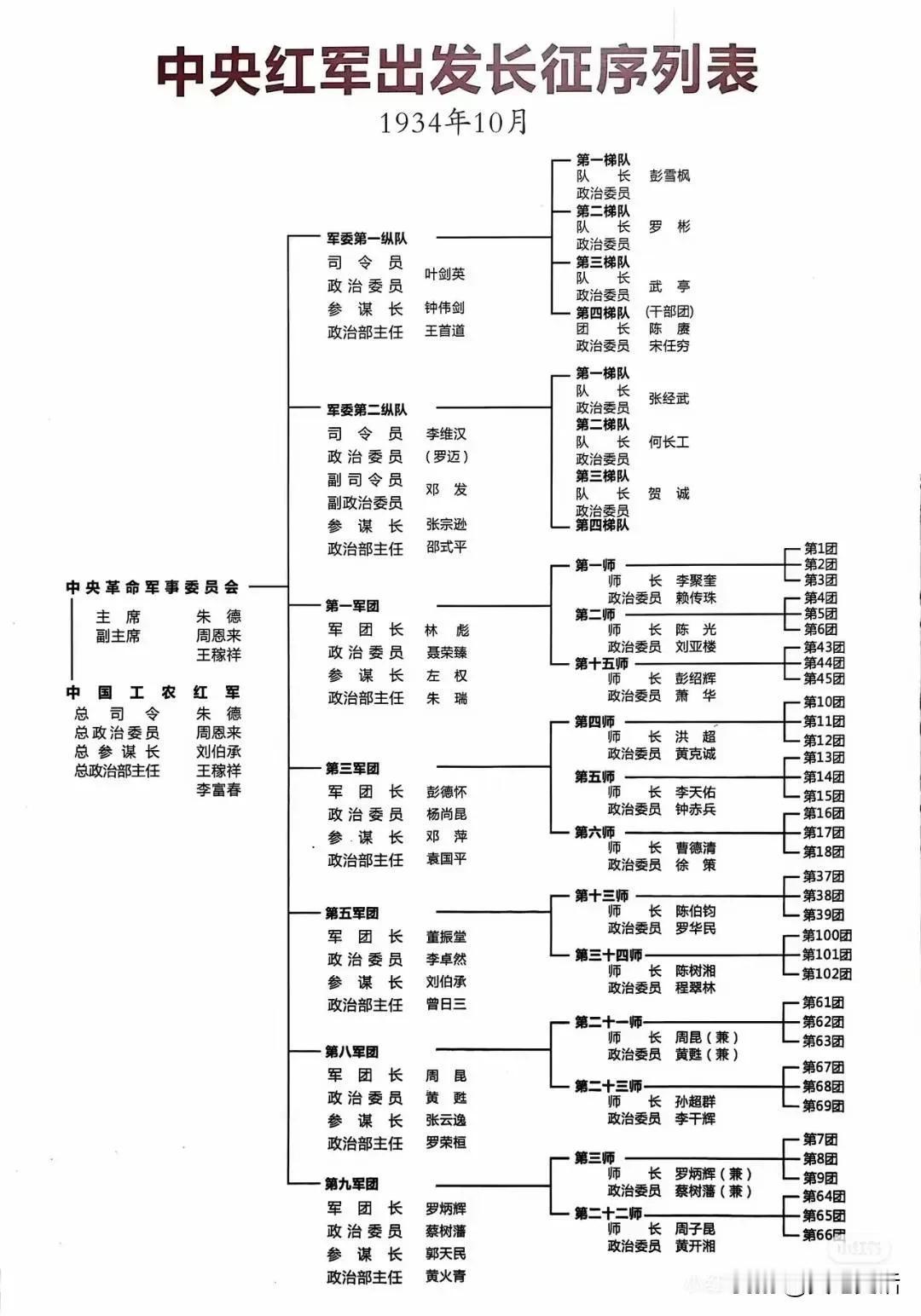1985年,关押方志敏的看守所所长遗孀生活困难,方志纯:予以帮助 1985年,初秋。江西省委大院里,秘书将一封信轻轻放在了方志纯的桌上。“书记,这封信您看一下,写信人……是凌凤梧的家属。” 凌凤梧。这个名字,方志纯当然记得。它像一枚尘封已久的印章,深深烙刻在家族的记忆里,也牵动着一段长达半个世纪、关乎他堂兄方志敏烈士的隐秘往事。信纸很薄,字迹娟秀却带着一丝颤抖,诉说着一个老妇人晚景的凄凉与无助。这位写信的老人,正是凌凤梧的遗孀王玉琴。 时光倒流回五十年前的1935年,南昌绥署军法处的看守所阴森压抑。新上任的所长凌凤梧,每天都能看到一个特殊的身影。那人叫方志敏,是国民党眼中的“要犯”。凌凤梧的办公室与方志敏的“优待室”仅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夜深人静,当他巡察时,总能看到对面那间囚室的灯光亮着。方志敏要么在奋笔疾书,要么在静心阅读,仿佛身处的不是牢笼,而是一间简陋的书房。那份泰然自若,让凌凤梧百思不得其解。 有几次,凌凤梧忍不住隔着天井与方志敏交谈几句。他本是浙江金华的布商子弟,骨子里并非冷酷之辈。他发现,这位共产党的“要犯”言谈举止间毫无暴戾之气,反而充满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方志敏的话语,总能让他这个国民党军官深受触动。渐渐地,一种混杂着同情与钦佩的情感在凌凤梧心中生根发芽。当他看到方志敏脚上那副沉重得几乎无法行走的镣铐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凌凤梧向上级打了报告,以“便于管理”为由,请求为方志敏换上一副轻便些的脚镣。这在当时,无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不仅如此,他还成了方志敏与外界联系的秘密信使。那些后来震撼了无数国人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正是经由凌凤梧的手,冒死传递出去,最终交到了鲁迅先生手中,才得以保存于世。可以说,没有凌凤梧,这些珍贵的文稿或许早已湮没无闻。 遗憾的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方志敏烈士牺牲那天,上级在凌凤梧的房间里搜出了一张方志敏留给他的字条。这下证据确凿,凌凤梧被撤职查办,关了三天三夜的禁闭。对于方志敏烈士最终被秘密掩埋于何处,惊魂未定的他确实毫不知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成立了。寻找方志敏烈士的遗骨,成了党中央和江西省委的一件大事。调查小组成立后,工作却一度陷入僵局。他们找到了当年的照相师,却只知道大概的沙窝区域;他们走访了无数当地百姓,也只得到一口薄棺材的模糊线索。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凌凤梧这个名字进入了调查组的视野。 找到凌凤梧后,他详尽地交代了当年的所有情况,但对于掩埋地点,他确实爱莫能助。调查再次陷入了停滞。直到19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南昌代纤厂在下沙窝地区施工时,工人们竟从地下挖出了一具遗骸,令人惊奇的是,这具遗骸的脚踝上,还锁着一副铁镣。 调查小组立刻请来了凌凤梧进行辨认。当他看到那副锈迹斑斑的脚镣时,情绪有些激动,几乎是脱口而出:“就是这副!错不了,这就是我当年给他换上的那副!”这句肯定的答复,为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凌凤梧,这位当年的看守所所长,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他对这位特殊“囚犯”的最后一次帮助。 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尤其是在辨认烈士遗骨这件事上立了功,凌凤梧在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得到了宽大处理。然而,历史的波诡云谲,远超个人所能预料。在后来的“十年运动”中,他还是因为其国民党旧职员的身份,被错误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受尽折磨,不久便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凌凤梧的去世,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他的妻子王玉琴独自拉扯着孩子,生活举步维艰。一晃又是多年过去,到了1985年,实在走投无路的王玉琴,偶然间打听到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担任了江西省的领导,便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写出了这封求助信。 放下信纸,方志纯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清楚,凌凤梧的身份是复杂的,但他更清楚,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凌凤梧做出了符合人性的正确选择。他同情革命,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堂兄的生命结晶。这份恩情,方家不能忘,共产党人更不应该忘。 他很快提笔作出了批示,大意是:凌凤梧此人,在方志敏烈士的教育影响下,对我党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其遗属生活困难,应当根据党的政策,予以照顾和帮助。 不久之后,一笔专项的生活困难补助费,开始按月发放到王玉琴的手中。这笔钱,或许数目不算巨大,但它足以慰藉一个在时代风雨中飘摇了几十年的家庭。它更像是一份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确认,确认了在那个黑白分明的残酷年代里,依然存在着人性的微光与复杂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