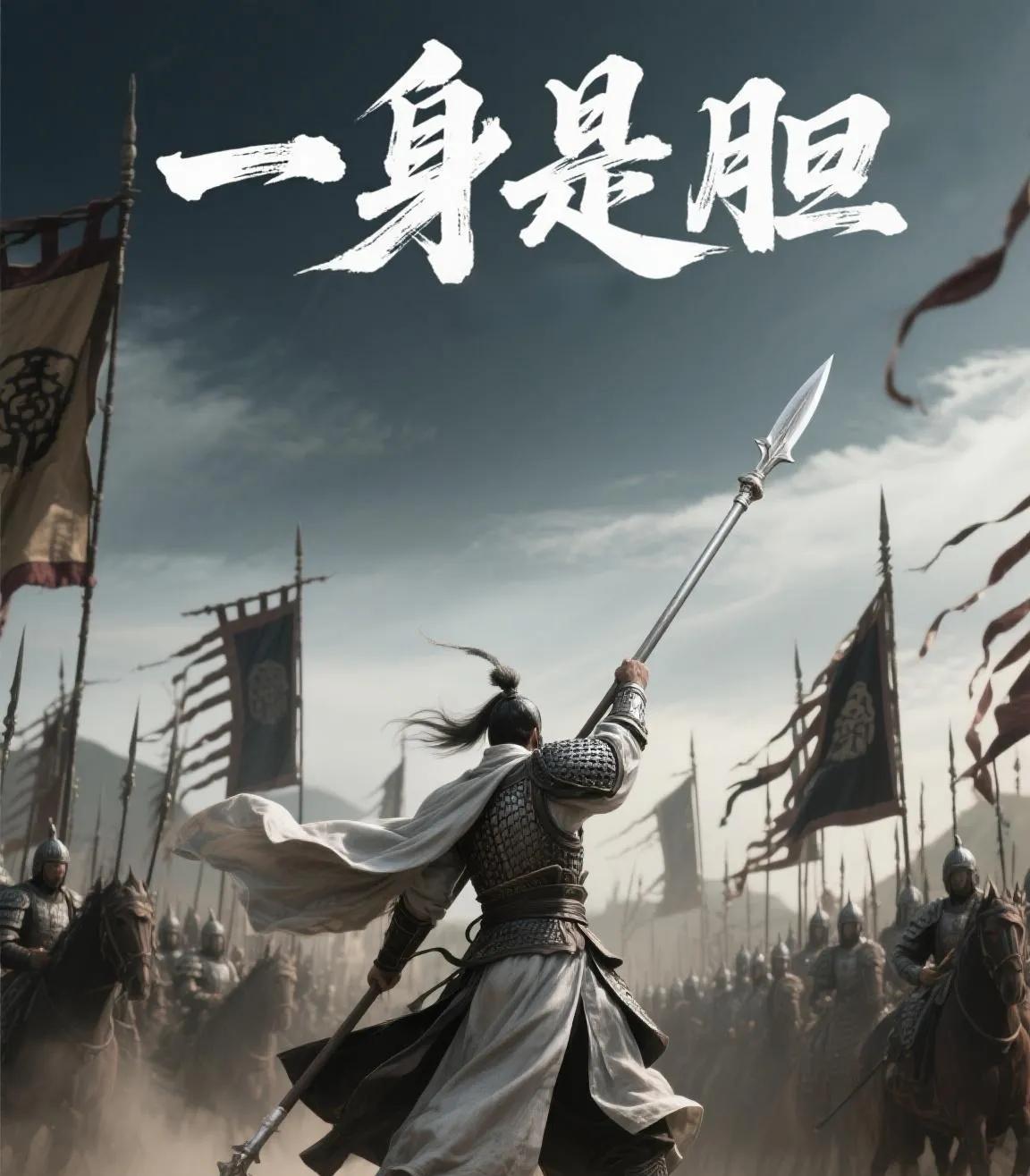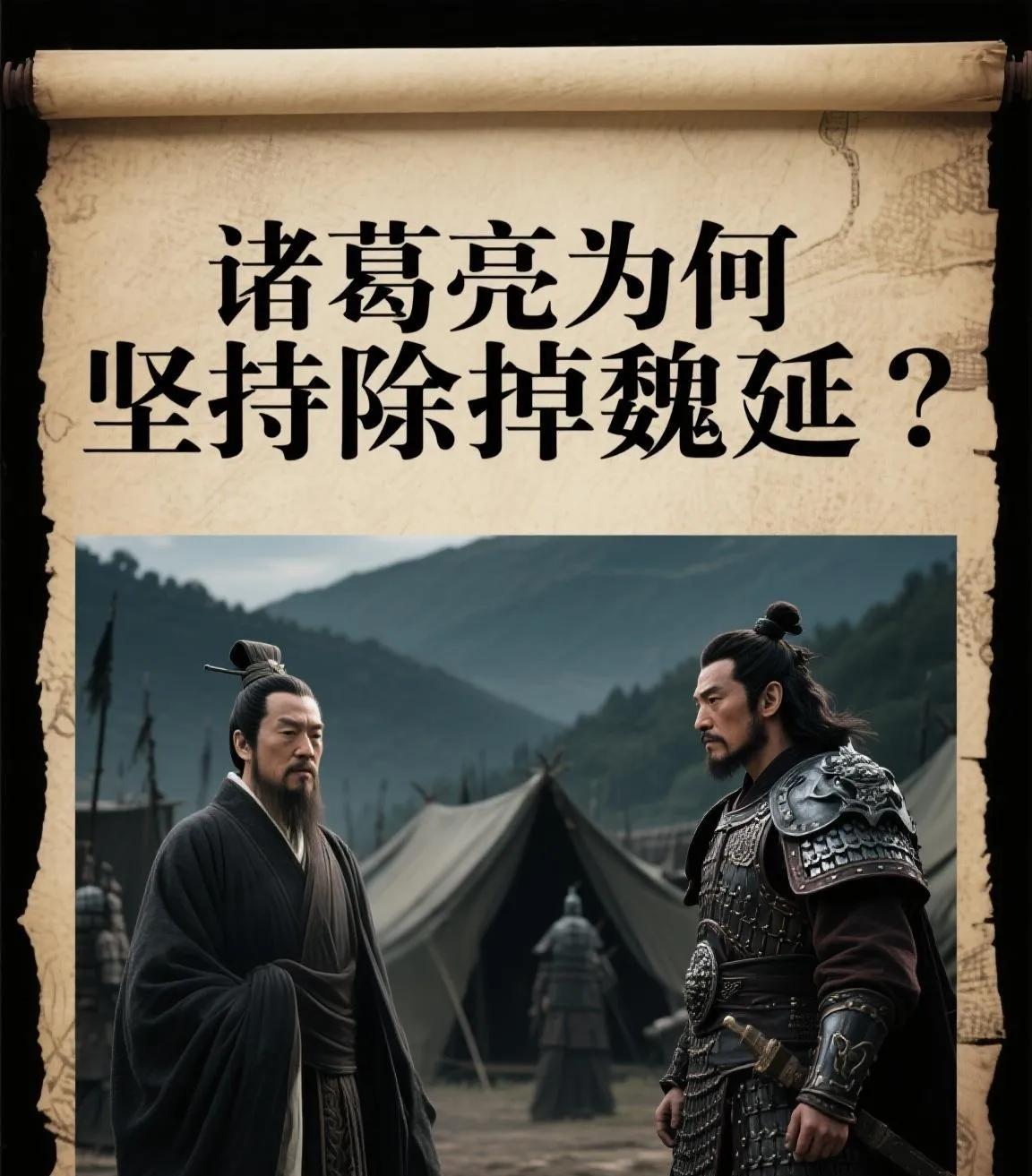❗️ 《一部虚构的间谍小说》 4
四
人生就是用来试错的,错了就删,错多了就把人也删了。
我曾经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一个仍然相信文字能改变现实的深度调查记者。
现在回想,这种信念是一种青春期的自恋:以为自己在和世界对话,其实不过是在对着废墟自说自话。
我像一个在深海打捞遗骸的潜水员,花了三年时间,紧盯着一个随时都会毁掉我的职业生涯的选题。
某IT大厂——直到现在也不能提起它的名字,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公司,而是一头披着企业LOGO的利维坦。它是吞噬数据的怪兽,它对任何数据都感兴趣,个人隐私、公共信息,甚至连你的情绪波动,它都觉得可以量化打包成“资产”。
三年来,我看过他们收集的所谓“用户数据”——其实是对人的“数字肢解”:指纹、声纹、面部微表情,行走的节奏,夜里独处时屏幕停留的时长,带着犹豫的点击,甚至未曾发出的朋友圈、输入又删除的搜索词。你在屏幕前做出的每个微小动作,都是一次无意识的表态,它们被存档、建模,直到你成为一个“可控样本”。这些数据构成人的精神底层的解剖图,被保存在某个数据库中。
它们确实能预测你下一次购物或者就医,但更深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预测你的下一次恐惧。它知道你什么时候孤独,什么时候焦虑;它模拟你的倔强,反复演算一个“驯服的你”。
它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它在最佳时机推送能让你屈服的信息。不知不觉中,把一个普通人塑造成顺从的良民。
我原以为我在调查一家越界的公司,直到有一天,一个类似科学怪人的工程师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你以为我们在做产品?其实我们在驯化人。”
工程师在酒后跟我说:“这是用算法来改造人,一种意识实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灭,而是更深的精神重置,让你自愿爱上铁链,主动维护锁着自己的数字牢笼。”
他继续说:“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终点,也是国家的未来形态。当权力不再需要恐吓你,而是通过算法训练你,把你的愤怒转化为点赞,把你的绝望转化为消费,你就再也无法区分自己是主体,还是样本。”
三年后,我的调查报告摆在总编的桌上。
总编让我撤稿,他看着我的眼神像在估价一个旧物,权衡是修补还是丢弃。他说,“有些东西不是新闻能碰的。你非要触及秩序的中枢,我也没办法。”
“我做错什么了?”
“写这些,有意义吗?”
“意义是你们删掉的。”
“你没做错什么。新闻就是用来试错的,错了就删,错多了就把人也删了。”
无所不知却永远不直接现身的系统给我发来一份“主动离职”的通知。我的署名、新闻奖、履历一并被系统清除,就像它们从未存在。
他们不讨厌我,也不想毁掉我。他们只是把我当作一个走偏的节点,一个可以重新归档的 bug,用温和而高效的方式,把我送回“出厂状态”。
总编的眼神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套规则是荒谬的,但我依然参与其中。”
我终于懂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人生就是用来试错的,错了就删,错多了就把人也删掉。数据可以被删除,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