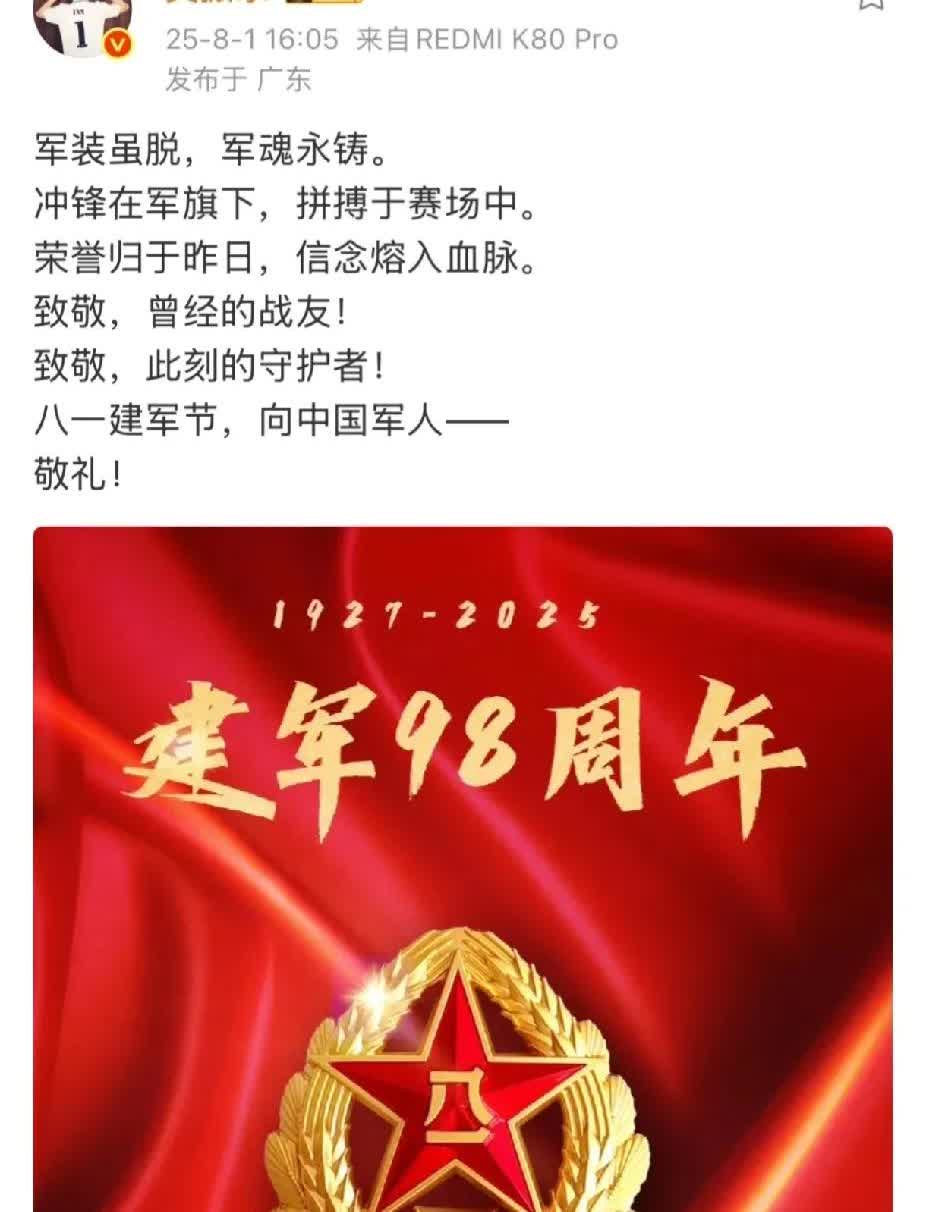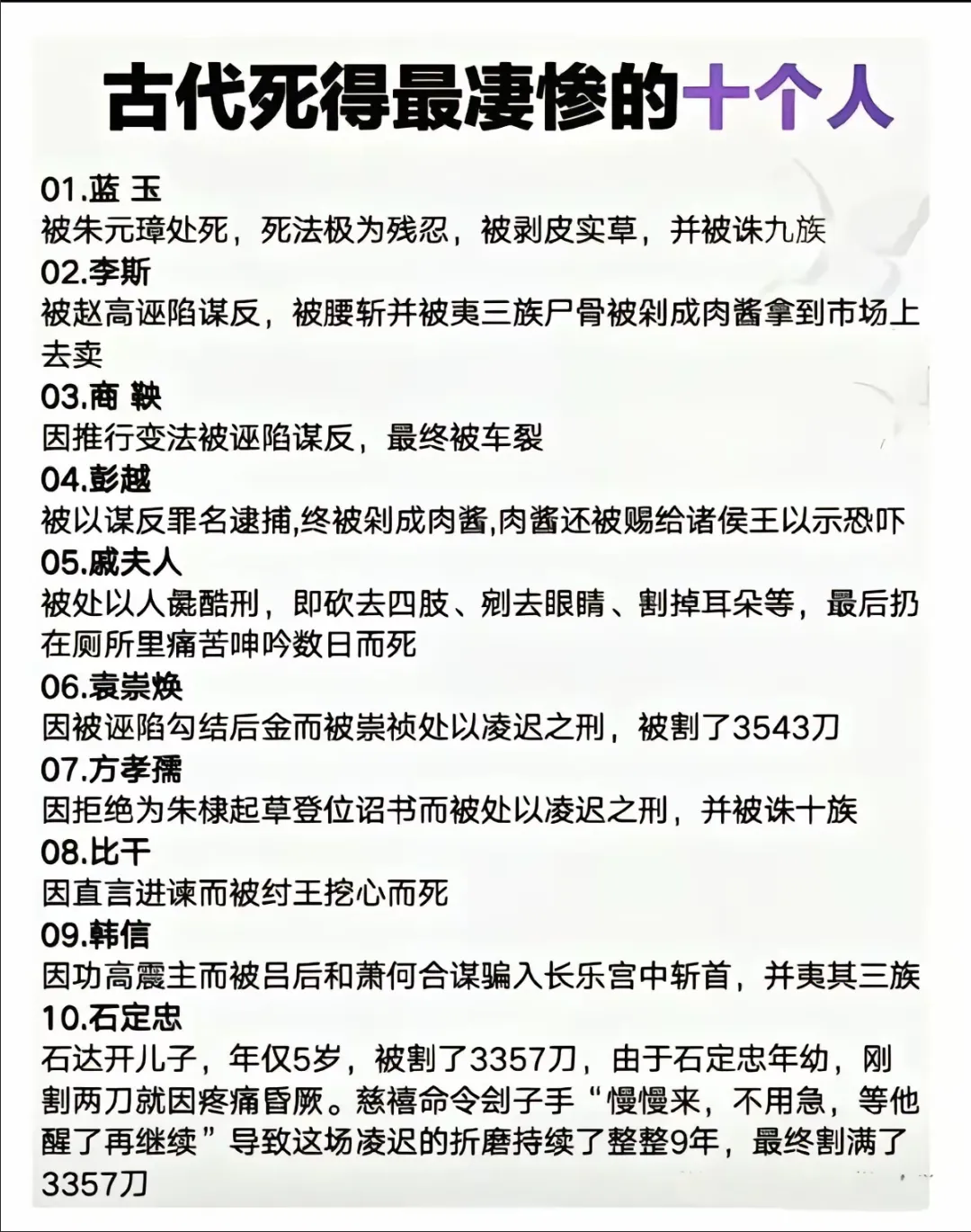1144 年,陆游娶了表妹唐婉,洞房花烛夜,陆游在唐婉耳旁说:“一会吹了蜡烛,我可就不是你表哥了,该改口了。” 只见唐婉低下头,娇羞的笑了,耳尖红得像檐角的灯笼,指尖绞着嫁衣上的并蒂莲纹 —— 那是她绣了三个月的花样,针脚里全是少女的欢喜。 红烛燃到半夜,蜡泪在案头积了小半盏,陆游铺开宣纸,想写首新婚诗,唐婉凑过来,发间的凤钗扫过他手背,凉丝丝的。“写什么?” 她轻声问,气息拂过他腕间。 “写‘一生一代一双人’。” 陆游笔尖一顿,墨滴在纸上晕成小团,像他们此刻没说出口的甜。 那时的他们哪会想到,这凤钗后来会在她发间晃过三年,再晃过沈园的雨,最后沉进坟墓的黑。 三年时光快得像指缝漏沙。唐婉的绣架上,从并蒂莲换成了小儿肚兜,针脚越来越密,却总等不到穿它的人。 陆母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沉,先是摔了唐婉炖的汤药,说 “连个子嗣都怀不上,留你何用”。 后来干脆请了算命先生,拿着两人八字在祖宗牌位前骂:“相克!必断我陆家香火!” 陆游跪在祠堂三天三夜,额头磕出青肿,求母亲再等等。 可当陆母哭着捧出他早逝的父亲牌位,说 “你要让陆家绝后吗”,他手里的笔终于抖得握不住。 休书落下时,墨迹在 “放妻书” 三个字上洇了又洇,像他没止住的泪。 唐婉走那天,绍兴下着小雨。她没带多少东西,只把那支凤钗重新别回发间,转身时裙角扫过门槛,没回头。 陆游站在门后,听着她的脚步声混着雨声渐远,忽然想起新婚夜她笑时,耳尖的红比这雨里的灯笼还亮。 再见面是 1155 年的沈园。杏花落了一地,像三年前她没带走的嫁衣碎片。 陆游喝了半盏黄縢酒,忽然听见假山后传来《梅花三弄》的调子 —— 那是他教她弹的第一支曲子。 他拨开垂落的柳条,看见唐婉坐在石凳上,素裙沾着雨珠,指尖在琴弦上顿了顿,抬头时,两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像两块被雨水泡透的冰。 她身后站着赵士程,那个温润的宗室子弟,正替她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 唐婉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一个字,只转身往长廊走,凤钗在发间晃了晃,像在他心上划了道痕。 陆游踉跄着走到粉墙前,抓起旁边园丁的石灰笔,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红酥手,黄縢酒”—— 写的是刚才那一眼里她的手,他杯里的酒。 “东风恶,欢情薄”—— 骂的是母亲的固执,命运的刻薄;三个 “错” 字刻得极深,石灰屑簌簌往下掉,像他砸在地上的心。 听说唐婉后来看到了这堵墙。她站了很久,雨打湿了裙摆,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砚台,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笔尖蘸着泪,“难、难、难” 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最后一笔晕开,像她没忍住的呜咽。 那年冬天,唐婉就去了。赵士程说,她临终前把那支凤钗放在枕边,喃喃念着 “表哥”。 陆游听到消息时,正在福州做官,手里的奏章掉在地上,窗外的梅花开得正艳,像她当年嫁衣上的绣线。 此后几十年,陆游走了很多地方,从蜀地到江南,贬了又起,起了又贬,却总在梦里回到沈园。 晚年的他白发垂到胸前,再去沈园时,杏花依旧落得满地,他摸着墙上早已模糊的字迹,指尖触到青苔,凉得像当年她发间的凤钗。 他写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写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近万首诗里,总有半首在念她。 85 岁那年,他躺在病榻上,让儿子扶他再看一眼沈园的画,枯瘦的手指划过画里的杏花,忽然笑了:“婉儿,我来陪你了。” 如今沈园的墙重新刷过,却总有人在特定的雨天,看见墙上隐约浮出 “错、错、错” 的影子。 导游会指着那片杏林说:“当年有个女子,把一生的泪,都落进了这雨里。” 而那支凤钗,据说还埋在某株杏树下,每逢花开,根须就缠着它,长出的花瓣,红得像当年洞房里的烛。 有些爱情,就是这样 —— 没走到白头,却让时光替他们记了千年。 参考来源:《宋史·陆游传》,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