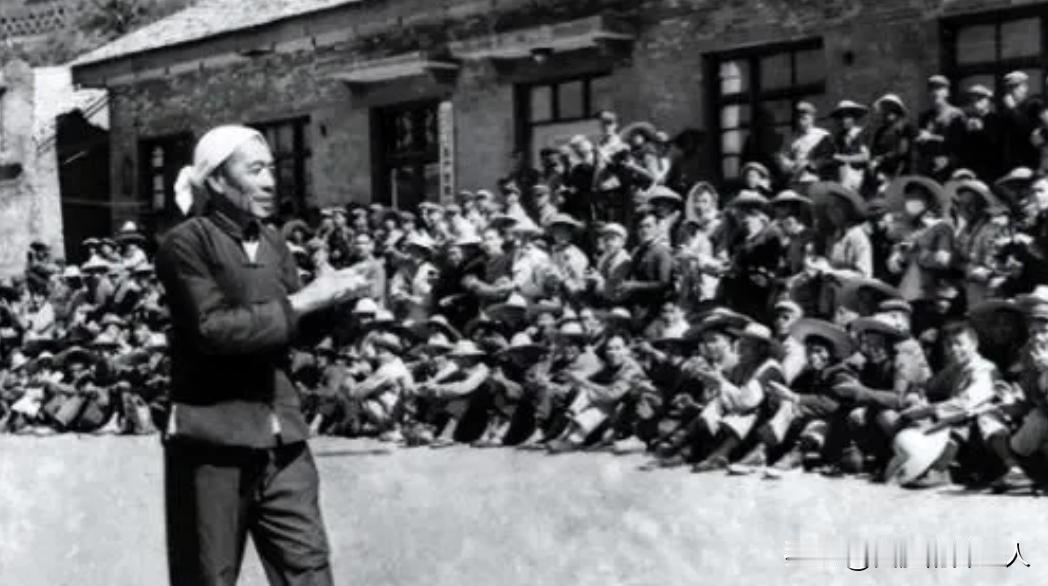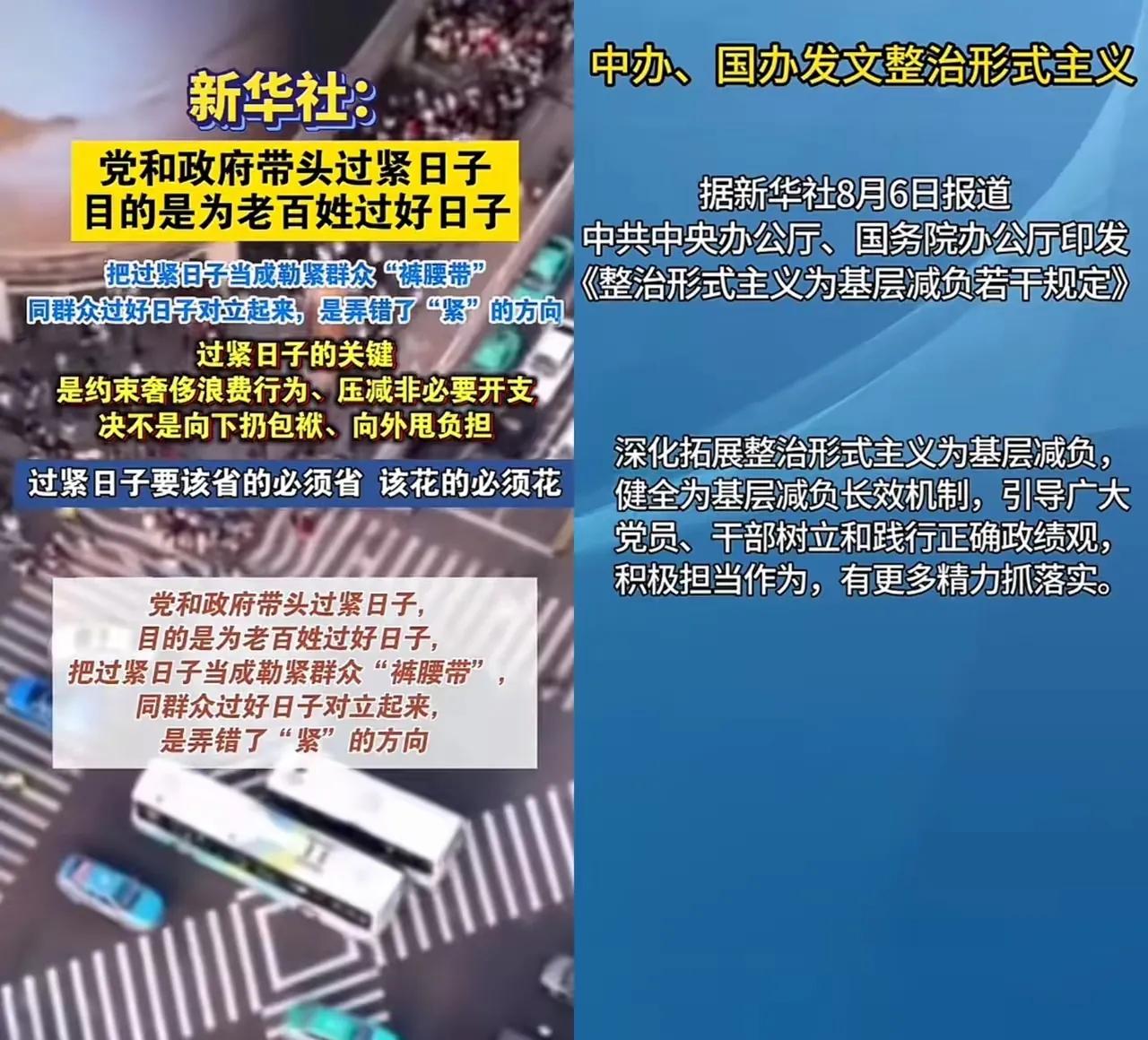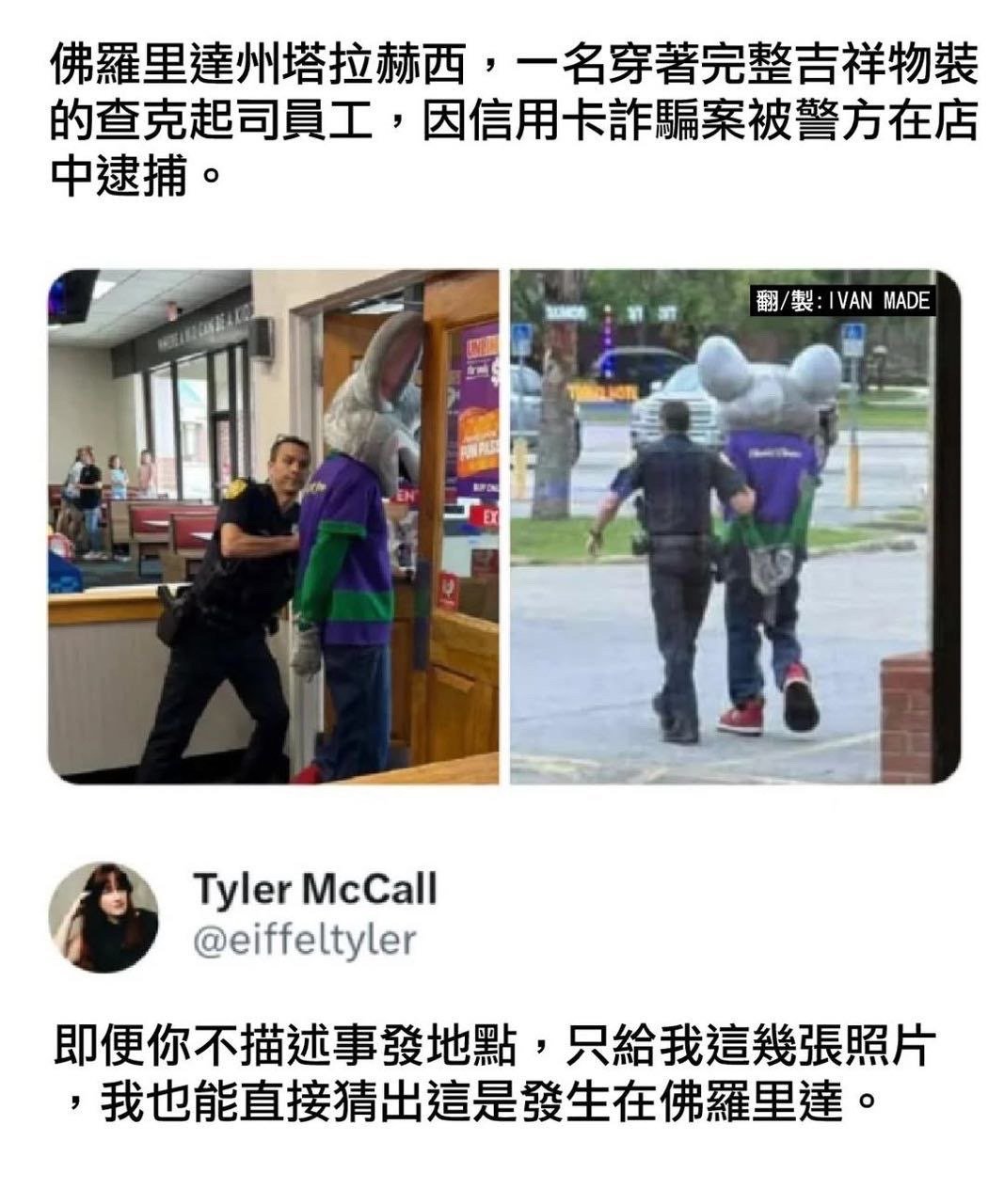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英这样说.….…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86年3月,山西大寨虎头山的风带着料峭春寒。 一座临时搭建的灵棚立在村口,白布在风中猎猎作响。 棚内烛火摇曳,映照着陈永贵的遗像——那张饱经风霜、沟壑纵横的农民脸庞。 大寨的乡亲们臂缠黑纱,默默守候,等待为他们的老支书送上最后一程。 灵棚外,夜色浓稠如墨,一个电话铃声刺破了寂静:县里要求立刻拆除灵棚,否则领导不会出席追悼仪式。 消息像冰水浇进人群。 时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的宋立英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她望向身旁的郭凤英——这位陈永贵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 郭凤英沉默地听着话筒里不容置疑的命令,烛光在她紧锁的眉间跳动。 几秒后,她斩钉截铁地对着话筒说: “灵棚不拆!要拆,也等天亮!” 话筒重重搁回座机,余音在空荡的办公室回荡。 棚外,守夜的老人裹紧棉袄,往火盆里添了把纸钱,火星腾起,照亮他浑浊眼底的倔强。 时间倒回几个月前。 北京木樨地22号楼12层,陈永贵蜷在阳台藤椅上,指尖摩挲着花盆里一株青翠的玉米苗。 楼下长安街的车流声隐约传来,却盖不住他梦里大寨春耕的吆喝声。 确诊癌症后,他拒绝了昂贵的进口药,把病历锁进抽屉。 “黄土埋到脖子的人,别糟蹋国家的钱。” 他这样对抹泪的妻子宋玉林说。 临终前夜,他拉着从昔阳赶来的老伙计,喉咙里滚着痰音: “回去…给我寻块向阳的坡地…四十块钱…够不够?” 儿子陈明亮别过脸,眼泪砸在地板上。 这位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副总理,最后的心事竟是怕死后给乡亲添负担。 灵棚终究没在当夜拆除。 晨曦微露时,白布上凝结的霜花闪着冷光。 乡亲们自发排成长队,沉默地将自家蒸的馍馍、煮的鸡蛋供奉在遗像前。 没有哀乐,只有山风呜咽。 县里的小轿车始终没出现在村口土路上。 郭凤英站在棚前,望着蜿蜒上虎头山的小道。 当年陈永贵就是沿着这条路,带领大伙用铁锹和箩筐,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头地刨成了海绵田。 她记得1963年发大水,陈永贵三天三夜没合眼,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就用树枝在泥地上画重建图纸。 如今,老支书的魂归故里,竟连一方遮风挡雨的灵棚都险些容不下。 追悼仪式草草结束。 下葬时,几个后生抬着骨灰盒往虎头山顶走。 路过当年修梯田炸开的石崖,老石匠突然蹲下身,抓了把混着石屑的黄土,撒进墓穴。 “老陈,这是咱大寨的土,暖和。” 风吹散纸钱,像一群灰蝶飞向沟壑纵横的梯田。 山脚下,新播种的麦田已泛起朦胧绿意。 陈永贵最终长眠在他用血汗浇灌的土地里,而那个深夜要求拆棚的电话,成了大寨人心头一道隐秘的伤疤,与虎头山的岩石一样沉默坚硬。 主要信源:(乌有之乡---陈永贵——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