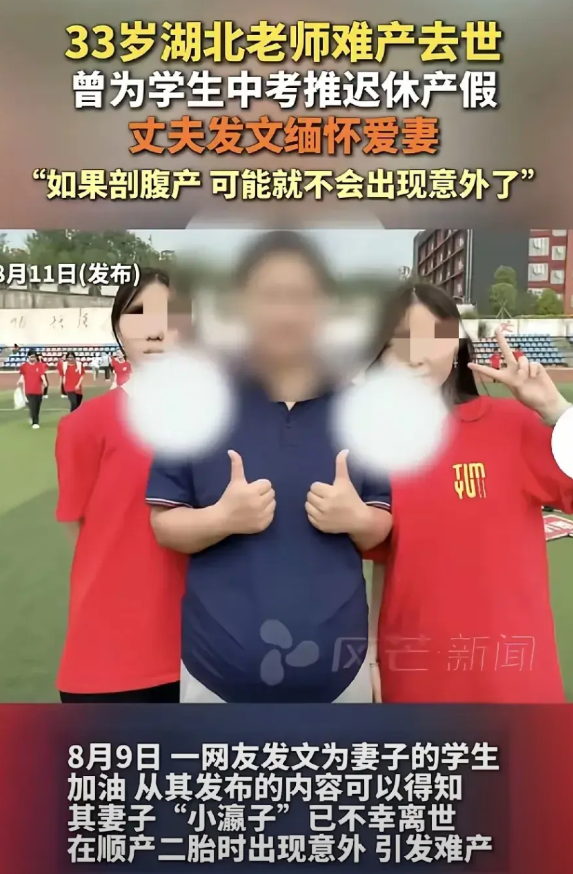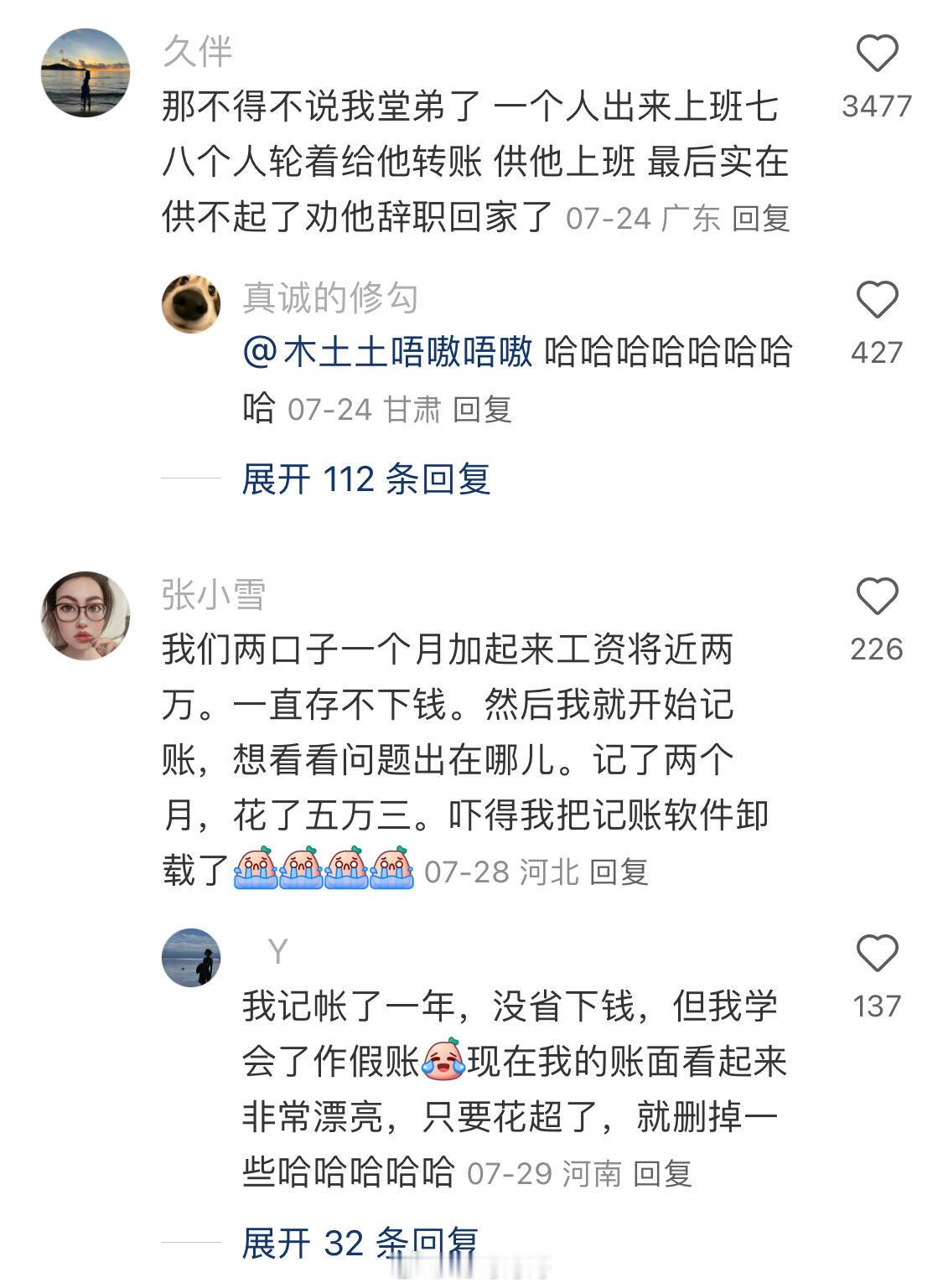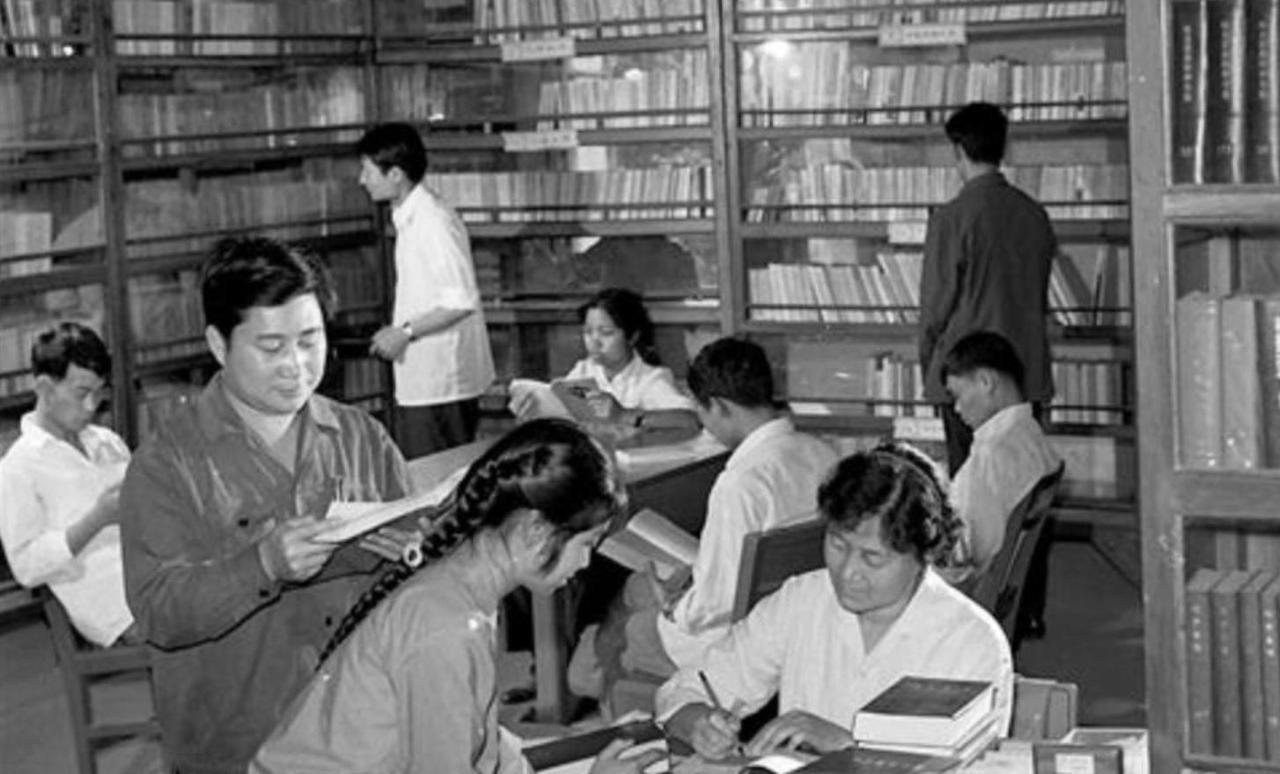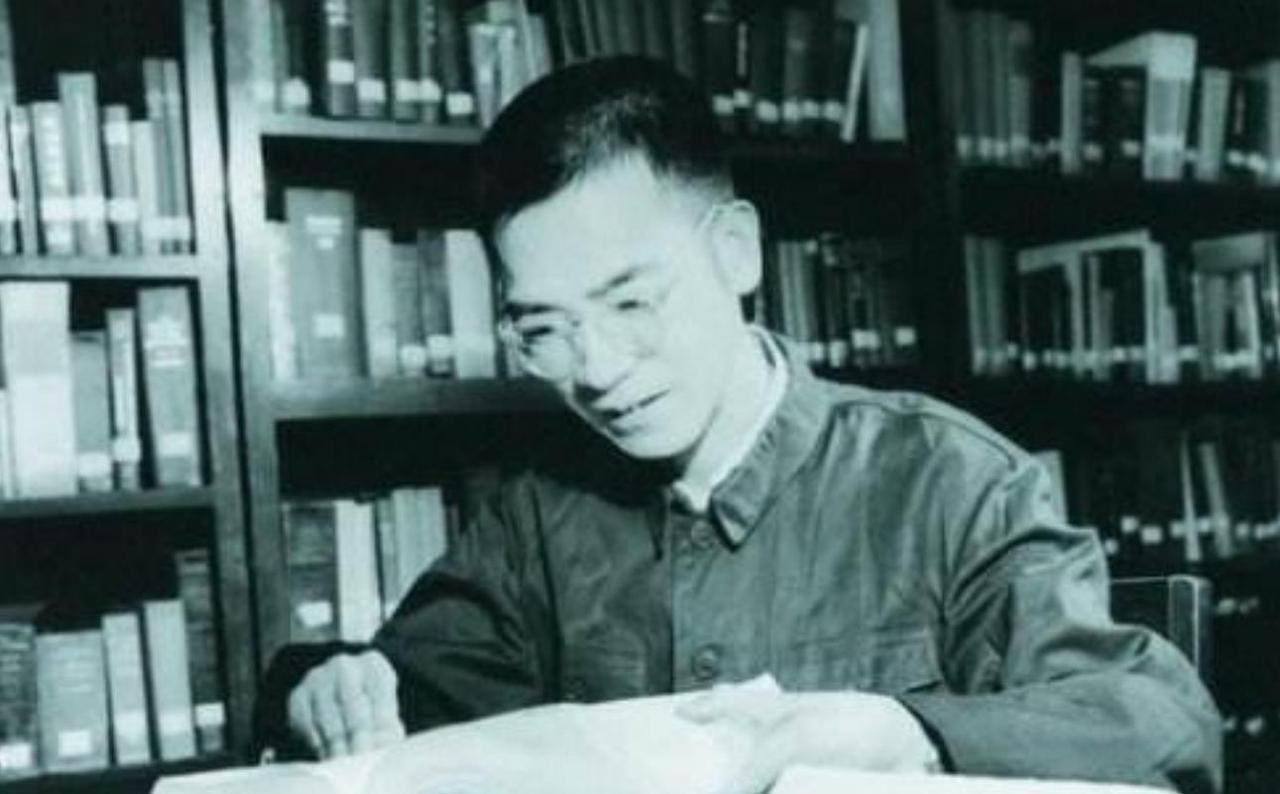1985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迎来了新一批学生。17岁的蒙古族女孩萨日娜和身高一米八二的潘军成为同班同学。三个月后,潘军因视力体检不合格面临退学,他争取到了旁听生资格,代价是没有学位证和毕业分配。
上海戏剧学院的梧桐叶刚黄透那年,17岁的萨日娜第一次见潘军。他站在体检室门口,背着手,肩膀塌着,手里攥着张体检表——表上"视力"那栏画了个红叉,旁边写着"建议退学"。
"潘军眼睛不行,排练时连对手的表情都看不清,谁敢跟他搭?"后排女生嘀咕。萨日娜听见了,没回头。她刚从内蒙古来上海,普通话还带着点口音,总觉得自己跟大家隔着层东西,倒更懂那种"被落下"的滋味。
那天下午排《雷雨》片段,老师让自由组队,没人往潘军跟前站。他靠墙坐着,把眼镜摘下来擦,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擦着擦着就红了眼。萨日娜抱着剧本走过去,往他手里一塞:"我跟你搭。我演四凤,你演周冲。"
潘军抬头看她,愣了愣:"我......我可能记不住走位,眼神也不准。"
"怕啥?"萨日娜笑,露出俩小虎牙,"你看不清我,我凑近点不就完了?"她往后退了两步,又往前凑,"你看,这样你能看见我眼睛不?"
排练时真有意思。潘军总下意识眯眼,萨日娜就特意站在他左前方——他左眼视力稍好点。
有次演到周冲给四凤送票,他该递"票"(其实是张白纸),却差点塞到萨日娜鼻子上。台下哄笑,他脸通红,萨日娜却接过来,顺势说台词:"周冲哥,你咋总盯着我看?"把错处圆成了戏。
后来才知道,潘军是因为小时候得过眼病,视力才这么差。他怕被退学,天天凌晨去操场练台词,嗓子喊哑了就含胖大海。
萨日娜撞见两回,把自己的润喉糖塞给他:"别硬喊,用气发声。"她教他找灯光标记记走位,还把剧本里的关键台词用红笔描粗,"你看不清字,就记红笔画的地方。"
毕业那年,潘军还是没拿到学位证,只能算旁听生,分配更是没指望。他收拾行李时,萨日娜蹲在旁边帮他叠衬衫:"老校长不是挺喜欢你的《茶馆》片段吗?去求求他。"
潘军没敢去,是萨日娜拉着他去了校长办公室。老校长看着他俩,又翻了翻潘军的排练笔记——那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批注,红笔蓝笔划得满页都是。"这孩子是真钻戏。"老校长叹口气,提笔签了字,"特批补发毕业证,总政话剧团刚好来要人,我推荐你去。"
潘军攥着毕业证,手都抖。萨日娜在旁边笑:"你看,我就说能成。"那天上海下了点小雨,他俩走在梧桐道上,潘军突然说:"萨日娜,以后我护着你。"萨日娜没回头,却把伞往他那边歪了歪——她听见自己心跳得比雨声还响。
1989年冬天,萨日娜跟潘军领了证。没办婚礼,就去百货大楼买了枚银戒指,8块钱,圈口有点大,萨日娜总用红线缠两圈。潘军又花250块买了张弹簧床垫,拉到单位分的筒子楼——11平米,靠墙摆张床,剩下的地方刚够放个煤炉和小桌。
"对不住啊,让你住这儿。"潘军擦着窗户上的霜,萨日娜从后面抱住他:"比宿舍强,有煤炉,不冷。"
更糟的是罚款。那会儿规定女的满23岁才能结婚,萨日娜才21,单位说要罚200块。潘军刚发工资,攥着钱去交,回来时脸铁青。萨日娜正蹲在煤炉边煮面条,往他碗里卧了个蛋:"罚就罚呗,咱以后好好挣。"
可日子没那么容易。萨日娜进了全总文工团,团里总说她"形象太朴实,演不了娇小姐",给她的都是跑龙套的角色,后来干脆不派活儿了。整整六年,她没演过一个正经角色。
白天潘军去话剧团排练,萨日娜就在家擦桌子、洗衣服,煤炉灭了就去楼道借火,邻居阿姨总说:"小萨,你这高材生,咋天天围着锅台转?"她笑笑不说话,晚上却蹲在灯下背台词——不管有没有戏,剧本总在枕头边放着。
有天潘军回来,看见她对着镜子练哭戏,眼圈红着,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衣服。他走过去,把衣服抢过来泡进盆里:"别洗了,我来。"
"你排练一天够累的......"
"累啥?"潘军搓着衣服,泡沫溅了一脸,"我娶的是上戏的高材生,不是保姆。你该琢磨戏,家务我来。"他把她往镜子前推,"你看,你眼睛里有戏,等机会来,准能发光。"
从那天起,潘军承包了所有家务。早上六点起来生煤炉,晚上回来买菜做饭,萨日娜背台词卡壳了,他就当"对手"陪她练。有次她练《骆驼祥子》里的虎妞,骂他"你个死祥子",他笑着接:"虎妞姐,我错了",逗得她忘了词。
筒子楼的煤烟味里,总混着萨日娜的台词声。她不知道机会啥时候来,可只要潘军在,蹲在煤炉边背台词,也觉得心里踏实。
1995年春天,《牛玉琴的树》剧组来选角。牛玉琴是治沙英雄,黑瘦、倔强,导演说"要找个能吃苦的"。萨日娜听说了,揣着自己练了半年的陕北口音,直接找到剧组驻地。
"导演,我能演。"她没说自己是文工团的,只说"我能去沙漠待着"。导演瞅她两眼:"去毛乌素沙漠拍三个月,吃沙子,晒脱皮,你行?" "行!"
去沙漠前,潘军帮她收拾行李,往包里塞了两罐防晒霜,又缝了个布套罩在水杯上:"沙漠风大,别把杯子吹倒了。"他送她到火车站,火车开时,萨日娜看见他站在月台上,手一直挥,直到变成个小黑点。
毛乌素真苦。白天太阳晒得脸疼,沙子往眼睛里钻,晚上冻得盖两床被子还发抖。萨日娜跟着牛玉琴学种树,天天扛树苗、浇水,手上磨出了茧,脸晒得跟当地人一个色。收工后别人都睡了,她还在帐篷里翻剧本,潘军寄来的信压在枕头下——信里没说自己累,只说"邻居阿姨教我做你爱吃的焖面,等你回来做"。
三个月后,萨日娜回来了,瘦了十斤,黑得潘军差点没认出来。可剧播出后,她凭牛玉琴拿了飞天奖一等奖。领奖那天,她穿了件潘军给她买的红裙子,站在台上说:"谢谢我先生,他让我知道,就算蹲在家里,也能等到来风。"
风真的来了。之后找她拍戏的人排着队,《闯关东》《母亲》,她成了"国民母亲"。可她越忙,潘军越"闲"了。
1999年女儿出生,萨日娜刚拍完一部戏,抱着孩子掉眼泪:"我又要接戏了,孩子咋办?"潘军摸着女儿的小脸蛋,突然说:"我不演了,在家带娃。"
萨日娜愣住了:"你爱话剧啊......"
"爱啊,但你更需要人托底。"潘军笑,"你在台前发光,我在幕后把家看好,一样是干事业。"
他真的退了。推掉了话剧团的戏,专心在家带女儿。萨日娜拍《闯关东》时,女儿才三个月,半夜总哭,潘军就抱着女儿在屋里走,唱着自己编的儿歌哄睡;女儿断奶,他试了七八种奶粉,才找到孩子爱喝的;萨日娜在东北拍戏,他每天发女儿的照片,说"今天会叫爸爸了"。
有次萨日娜中途回家,推开家门,看见潘军背着女儿在厨房做饭,围裙上沾着奶粉渍,女儿揪着他的耳朵笑。她站在门口,眼泪掉了下来——她拿金鹰奖时说"丈夫的支持成就了我",哪是客套话?那是他把自己的舞台,让给了她。
2022年白玉兰奖颁奖夜,萨日娜坐在台下,手心直冒汗。手机震了下,是潘军发来的:"别紧张,我在家看直播,闺女也在。"
她抬头往屏幕看,镜头扫到后台,恍惚看见三十多年前的自己——那个在筒子楼背台词的姑娘,怎么也想不到,有天会提名最佳女主角。
"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的是——《人世间》萨日娜!"
她站起来,裙摆扫过椅子,脚步却稳。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灯,突然看见观众席角落里,有个熟悉的身影——潘军没在家,悄悄来了,正举着手机拍她,眼睛亮得像当年在排练厅看她演四凤时。
"谢谢我的先生潘军。"她声音有点抖,"三十多年了,他把家里的煤炉烧得暖,把女儿带大,让我能安心在外面闯。我拿再多奖杯,都不如他给我的那个家珍贵。"
台下的潘军,偷偷抹了把脸。
现在他们住的房子大了,有宽敞的厨房。潘军的厨艺早练得顶呱呱,红烧肉炖得酥软,女儿总说"爸做的比外面好吃";萨日娜还是只会煮面条,偶尔想露一手,炒个青菜能糊锅底,潘军笑着抢过锅:"你歇着,我来。"
有人问他们婚姻的秘诀,萨日娜总说:"他懂我的价值。在我觉得自己啥也不是的时候,他说我眼睛里有戏;在我想往前冲的时候,他说'我给你守着家'。"
潘军不怎么说话,却总在行动。萨日娜拍戏晚归,门口总有双摆好的拖鞋;她背台词忘词,他还能接上下句;去年她在央视重现《人世间》"李素华临终"的片段,他坐在观众席第一排,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她,跟1985年那个在排练厅看她演四凤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片段演完,萨日娜鞠躬,台下掌声雷动。她往潘军那边看,他冲她竖了个大拇指,嘴角笑着,眼里闪着光。
后台采访时,记者说:"您先生牺牲真多。"
萨日娜摇摇头,眼里有笑:"不是牺牲,是相互成全。他让我在台前活成了自己,我也让他在幕后,把日子过成了他喜欢的样子——你看,他现在炒的红烧肉,比当年话剧团的盒饭香多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也落在她提到潘军时,眼里化不开的软。三十多年的日子,就像那枚8块钱的戒指,磨掉了银亮,却攒下了暖——原来最好的相伴,从不是谁追着谁的光,而是你往前闯时,我给你当靠山;你站在台上时,我在台下,比谁都懂你眼里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