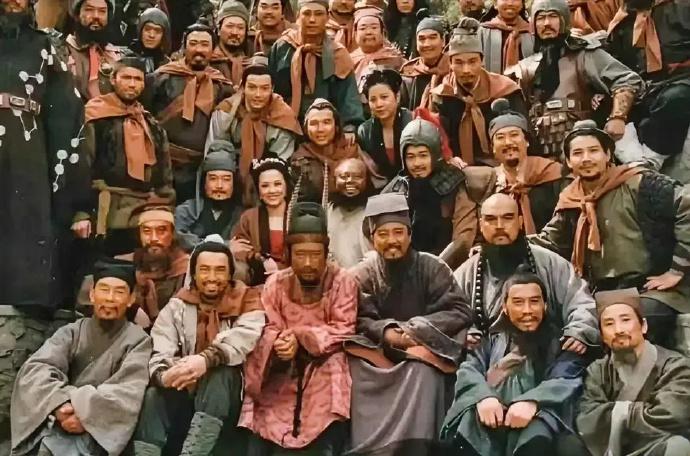在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里,亲情从来不是简单的血浓于水。它时而被利益裹挟,时而被权力扭曲,变成了一张剪不断、理还乱的网。《红楼梦》中那些扭曲的亲情关系,正是封建大家族无可避免的悲剧缩影。 林黛玉初进贾府,见到外祖母贾母时,原本需要行一套繁琐的见面礼。但贾母却“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这一举动看似违背了贾府重视礼数的传统,却流露出贾母对逝去女儿贾敏的思念与悲痛。她毫不掩饰地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也不能一见,今见了你,我怎不伤心!” 贾母对黛玉的疼爱,带着怜惜与感伤的色调。这其中既有着对早逝女儿的思念,也有对黛玉孤苦无依处境的同情。 然而贾母对王熙凤的宠爱,则显得截然不同。凤姐那“彩绣辉煌”的打扮和“放诞无礼”的举止,在规矩森严的贾府中显得格外突出。 贾母甚至用戏谑的口吻向黛玉介绍凤姐:“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这种亲昵的调侃,背后是对凤姐聪明能干和阿谀逢迎的赏识与信任。 在所有晚辈中,贾母最溺爱的非贾宝玉莫属。这种爱几乎是无原则的,即使宝玉“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在正统人物眼中是个“混世魔王”,贾母也全然不顾。 当宝玉在她面前狠命摔玉时,贾母不是恼怒,而是焦急地搂着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接着又是哄又是劝,还亲手把玉给他戴上。 在第三十三回中,宝玉被贾政暴打,贾母闻讯后怒不可遏地痛斥贾政,抱着宝玉“哭个不了”。她根本没有问宝玉到底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对宝玉的溺爱让她不能容忍孙子受任何委屈。 贾母为何如此溺爱宝玉? 有几个关键原因:第一,贾珠英年早逝的教训让贾母担心宝玉也会早逝;第二,宝玉长得像爷爷贾代善,爱屋及乌;第三,宝玉衔玉而生的不凡之处;第四,宝玉对贾母也很孝顺。 贾母的溺爱客观上给了宝玉较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他能够发展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萌芽和叛逆性格。但这也加剧了贾政与宝玉之间的父子矛盾。 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几乎代表了封建家庭中典型的教育方式冲突。 贾政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贾母则充当了孙子的“保护伞”。这种教育理念的差异,使得宝玉在父亲面前如同“老鼠见了猫”,而在祖母那里却可以肆意撒娇。 在宝玉挨打那一回,贾母虽然愤怒地斥责贾政,但却流露出了对父子二人的双重关爱。她对贾政说:“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不觉滚下泪来。 这句话很有深意——贾母不仅是心疼孙子,也是想起了当年贾政被父亲暴打的情景,作为母亲的心疼与无奈。她其实是在提醒贾政:你自己曾经受过暴打的苦楚,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呢? 然而这种教育方式的代际传递,几乎成了贾家的传统。赖嬷嬷曾经对宝玉说:“当日老爷小时候那挨打的情景,谁没见过!何曾像你们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从荣国公宁国公到贾宝玉这代,贾家的教育就是一个“打”字。然而这种粗暴的教育方式并没有培养出人才,“除了贾敬是中了进士,其他人都是从袭官到皇帝‘施舍’,然后到了最后这代干脆就只能买官了”。 在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中,亲情往往与利益纠缠在一起。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贾赦作为嫡长子理应继承荣国府当家的权力,邢夫人也应该主持家庭内部事务。 但由于贾母的偏心,荣国府的家政大权落到了贾政夫妇手中,王夫人又把实际操作权交给了自己的内侄女王熙凤。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为家庭内部派系斗争埋下了根子。 贾赦对此显然是不满的。在中秋夜宴中,他讲了一个母亲偏心的笑话,有意来刺痛贾母。母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和睦。 但有意思的是,贾赦在某些事情上却表现出重视亲情的一面。黛玉进府时,他怕相见会引起伤感,特意传话安慰她:“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 在第二十五回,宝玉和王熙凤被马道婆诅咒而生命垂危时,贾赦的表现也比贾政更有人情味,“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而贾政则已经放弃,认为“儿女之数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 即使是看似不近人情的贾政,内心也有着父爱的矛盾。在宝玉挨打后,他“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这种后悔的心情,或许才是隐藏在严厉外表下的真实父爱。 《红楼梦》中描写的各种亲情关系,折射出封建家族的深层次问题。正如贾探春所说:“咱们是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这种亲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正是贾府走向衰败的重要征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也是对人性与亲情的深刻洞察。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也是《红楼梦》历经百年依然震撼人心的原因。 家的温度,不在于宅邸多大,而在于其中流淌的爱能否纯粹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