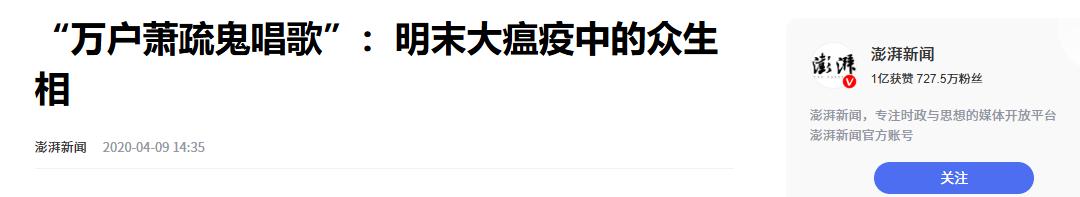明末,闹饥荒,郭六的丈夫觉得家里没粮,自忖活不下去,就把父母托付给妻子郭六。郭六颇有姿色,但一介女流如何养家? 1724年,在淮镇,旱魃肆虐,赤地千里。 饥饿如同瘟疫,吞噬着淮镇的生息。 郭六的丈夫蹲在门槛上,望着空米缸和灶台边的父母,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他猛地起身,走到妻子郭六面前,“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爹娘老了,走不动了,我得出去寻条活路!家里就托付给你了!” 而郭六,这位荆钗布裙也难掩清丽容颜的农家女,默默扶起丈夫。 “你放心走。爹娘在,我在。” 随后,丈夫背起仅有的半袋麸皮,一步三回头地消失了。 丈夫离去后,郭六成了这个家庭的唯一支柱。 然而,家中早已断粮,野菜、草根成了救命稻草。 她每日天不亮便出门,在荒芜的田野、河床边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 回到家中,她将寻来的“食物”仔细清洗、捣碎,混入少许麸皮,熬成稀薄的糊糊,先盛给公婆,自己则常常只喝几口汤水。 而家中,公公咳得撕心裂肺,婆婆却连水瓢都端不稳。 郭六知道,此时仅靠挖野菜,无异于杯水车薪。 她必须另寻生路! 郭六翻出丈夫留下的旧棉袄,棉絮早已板结如石。 她坐在油灯下,一点点拆解,挑出尚能使用的线头,捻成细麻线。 又将婆婆早年织就、因眼疾未能完成的半匹粗布仔细整理。 次日拂晓,她揣上两个窝头,背上粗布,徒步三十里赶往县城。 城门守卫见她孤身妇人,搜身时草草了事,她藏在鞋底的半块救命盐巴得以保全。 布铺掌柜嫌弃布料粗糙,只肯出三个铜板。 郭六陈述:“婆婆眼睛花了,每针都多绕两圈,只为结实耐用。” 掌柜最终心软,添了一枚铜板。 四个铜板在手,她直奔粮铺。 糙米价高,四个铜板仅换得半勺。 她毫不犹豫掏出那半块盐巴:“掌柜,添一勺,行吗?” 盐巴在饥荒年十分珍贵,掌柜叹口气,多给了半勺。 归途,见一户人家正剥着树皮。 郭六从怀中米袋里捧出一小捧米:“煮水泡软,或能多撑两日。” 那家媳妇泪流满面欲跪谢,被她一把扶住:“都是熬日子的人。” 到家,公公正偷偷嚼着草根。 郭六将米倒入瓦罐,拿出盐巴:“今日有咸味的米汤了。” 夜里,公婆在里屋自责拖累。 而郭六坐在灯下,故意大声说:“我男人走时说了,南边的麦子快黄了,等收了麦,日子就好了。” 这语气十分坚定,像是安慰公婆,也是在给自己新的希望。 而郭六的巧手渐渐传开。 县城富户小姐出嫁,嫌绣坊花样俗气,听闻郭六能绣野趣,便召她入府。 小姐指着仙人掌:“绣这个,要见刺。” 郭六在绣架前三日不眠不休,最终绣品让小姐大喜,赏她一升白米。 然而,随着灾情日益深重,针线活计也日渐稀少。 村中几个素来觊觎郭六姿色的富家子弟,见机纷纷登门,言语轻佻。 “嫂子,何苦硬撑?跟了我们,保你公婆衣食无忧。” 郭六见此,闭门谢客。 但米缸终究见了底。 一日,她将村中尚存的老弱邻居请至家中,对着众人竟跪了下去! “我夫临行,以双亲相托。如今什么都不剩了,恳请相邻们,能伸手拉一把,若无,” 她顿了顿,“若无,明天我郭六便卖笑求生,奉养公婆!望诸君勿笑。” 最终,众人摇头散去,留下郭六一人跪在地上。 当夜,郭六在公婆床前长跪不起。 第二天,她洗净脸庞,换上最整洁的旧衣,打开了家门。 富家子弟们闻风而至。 她强颜欢笑,听到有人掷金求宿,她咬牙应承。 最终,她用身体换来的银钱,不仅让公婆活了下来,竟还略有盈余。 她用这笔钱,买下邻村一个被卖的穷苦女孩,藏于后院。 三年光阴,旱灾终于过去。 某天,郭六的丈夫回来了! 他衣衫褴褛,满面风霜,本以为家中早已是白骨荒冢,却见父母安坐院中,面色虽苍老却无饥馑之色,妻子郭六更是迎上前来,嘘寒问暖。 他惊愕不已,待郭六平静地引他拜见公婆,然后说道:“父母都健在,我没有负你所托。今将二老,完璧归赵。” 说完,她喊出后院那个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孩,推到丈夫面前:“此女,可配为君妻。妾身已污,不堪为君妇。” 丈夫闻言目瞪口呆,尚未反应,郭六已转身进入厨房,说要为他做饭。 厨房里,锅中新粥翻滚,米香四溢。 郭六站在锅台前,拿起那把剪刀刺向了自己的脖颈。 县令闻讯赶来,验尸时见郭六双目圆睁,似有滔天冤屈。 邻里作证,泣述前情。 县令虽感慨其孝义,却囿于礼法,判其不得与夫合葬。 公婆闻讯,抚尸痛哭:“贞妇!儿子不能养父母,连累你了!如今你失节是天大的冤屈啊!这是我们的家事,不劳官断!她务必要葬在我们在祖坟!” 这时,郭六圆睁的双眼,竟缓缓阖上。 她以血洗净了卖笑的污名,以死捍卫了灵魂的清白。 郭六的名字,最终未能刻上贞节牌坊,却以另一种方式,深深镌刻在淮镇百姓的记忆里。 主要信源:(《民间故事》改编、澎湃新闻——“万户萧疏鬼唱歌”:明末大瘟疫中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