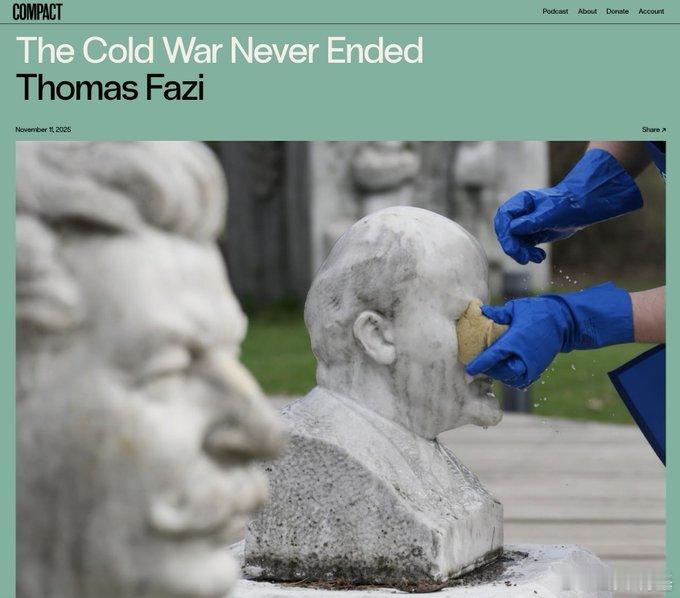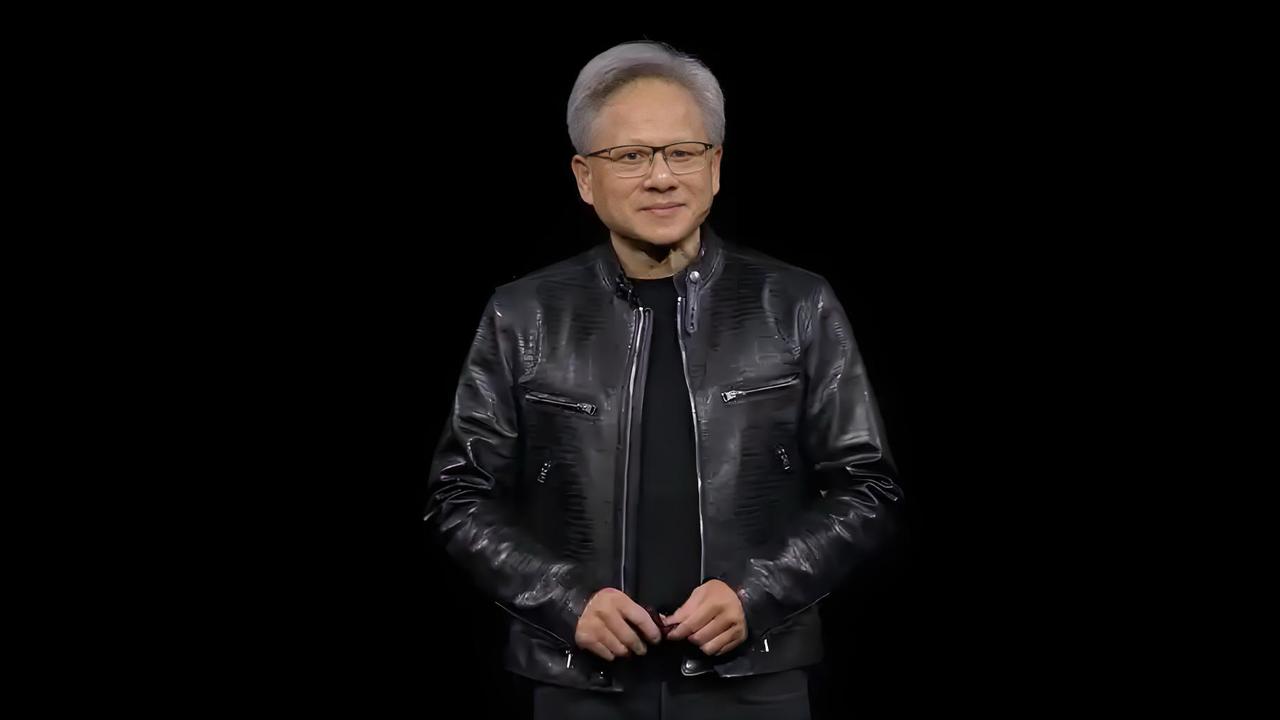1944年,一群美国士兵闲着无聊,就把日军尸体的衣服扒下来,里面塞进干草,再在衣服外面写上东条英机的名字。 聊这事,得先回到那个血肉模糊的太平洋战场。1944年,美日之间的岛屿争夺战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美军士兵,一帮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子,前一天还在本土吃着汉堡喝着可乐,后一天就被扔进了炼狱般的丛林。他们的敌人是谁?是一群信奉“玉碎”冲锋,把投降看作奇耻大辱的日本兵。 你可能听过很多故事,说日军会在投降的最后一刻拉响身上的手雷,或者在裤裆里藏着引信和刀片。这不是夸张,这是当时美军的日常。硫磺岛一战,光是从日军尸体上搜出来的引信就装了两大箱。所以在战场上,扒掉俘虏的衣服,首先是一个标准作业流程,无关羞辱,只为活命。 更别提太平洋那要命的湿热环境,虱子、登革热、丛林腐烂症,比子弹还可怕。 但流程归流程,人心归人心。当照片传回美国,民众看到几百名日军俘虏赤条条地蹲在塞班岛的沙滩上,而旁边的美国大兵笑得前仰后合,把这当景点打卡时,舆论炸了。有人拍手叫好,觉得解气;也有人开始反思:“我们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仇恨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当这些美国兵亲眼见过“巴丹死亡行军”里,自己的战友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挂在树上当靶子练;当他们听说马尼拉大屠杀的惨状时,你还指望他们去跟对手念叨《日内瓦公约》?更何况,日本陆军省自己压根就没签那份公约。你不是宁死不降,要为天皇“玉碎”吗?那好,美军就干脆帮你把最后那点“体面”也撕个粉碎。后来美军的心理战部门统计,这种脱衣审讯的方式,让日军残兵的投降率翻了四倍。你看,数据冷冰冰,却写满了“人一旦放弃尊严,命就变得很便宜”的残酷逻辑。 所以,回到我们开头那个场景——把日军尸体做成稻草人,写上东条英机的名字。这已经不是为了安全,也不是为了防疫。这是一种纯粹的、发泄式的憎恨,是一种“你把我兄弟不当人,我连你的尸体都不当人”的原始报复。 这种通过剥夺衣物来摧毁对手尊严的玩法,是刻在人类历史骨子里的。时间往前倒推八百多年,看看北宋的“靖康之难”。金人是怎么对付宋朝皇室的?他们发明了一种叫“牵羊礼”的仪式。把皇帝赵桓、皇后、妃子、大臣三千多人,无论男女,全部扒光,只披上一张羊皮,然后用绳子套着脖子,像牲口一样在地上爬。 皇后和王妃们被直接送进“浣衣院”——这名字听着文雅,其实就是军妓营。宋钦宗赵桓就在旁边跪着看,哭到昏厥。金国的史书写得极其直白:“使南人知天命已改。”一句话,把你的身体、身份、国格、尊严全部注销。这跟几百年后美军档案里那句剥夺他们的尊严,简直是异曲同工。历史从不重复,但总会惊人地押韵,押的都是“先剥衣,再剥皮”的韵脚。 那么,盟军对日军的恨,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在堪培拉的国家战争纪念馆里,二战展厅的入口处,曾经把一面日本旭日旗当作脚垫,后来改成了投影。每个进去参观的人,都必须踩着“日本军旗”过去。日本外务省抗议了无数次,连安倍晋三都亲自出面,但澳大利亚人鸟都不鸟。 为什么这么记仇?因为他们忘不了。1943年,澳大利亚陆军中士伦纳德西夫利特在新几内亚被俘,日军在海滩上将他斩首。行刑的军官,甚至还命令手下把这残忍的一幕拍了下来。战后,美军在一具日军尸体上发现了这张照片。这是唯一一张记录澳大利亚战俘被日军虐杀的照片,当它刊登在国内报纸上时,这个当时人口仅700万的国家,瞬间就有100多万人报名参军,誓要复仇。 如果说斩首还只是肉体上的折磨,那另一件事则彻底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吃人。1945年,在距离东京不远的父岛,驻守日军在补给充足、甚至能喝上清酒的情况下,杀害了8名被俘的美国海军飞行员,并肢解、烹食了其中5人的尸体,仅仅是为了“鼓舞士气”。 这种刻骨的仇恨,荷兰人也有。二战时,超过10万名荷兰军民家属被关在日军位于印尼的集中营里。一位叫柏西科维纳斯的幸存者回忆,日本兵每天都会从集中营里带走几十名白人妇女轮奸,连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她的母亲也曾当着她的面被日本兵糟蹋。所以,当1971年裕仁天皇访问荷兰时,他的座驾被愤怒的民众泼满了粪尿,种下的“友谊之杉”被连根拔起,根部还被撒上了浓盐酸。 讲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1944年那个被做成稻草人的日军尸体。现在你还觉得,那只是一群美国大兵闲着无聊的恶作剧吗?不,那是无数血债凝结成的一个冰冷的符号。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日本却在篡改历史的路上越走越远,把自己打扮成原子弹下的“受害者”,资助西方学者将“慰安妇”写成“自愿卖淫女”。这种行为,比战场上的刺刀更恶毒,因为它企图谋杀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