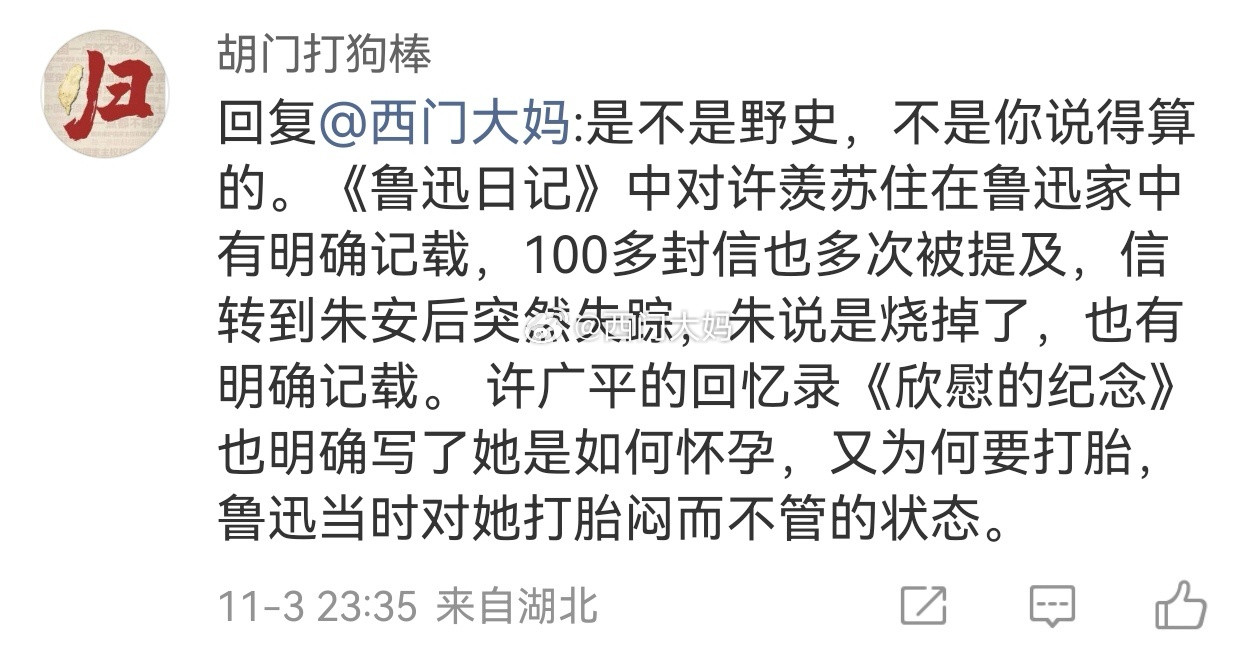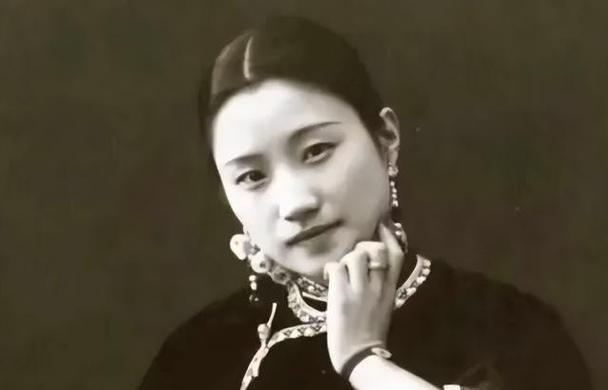1946年,周海婴与母亲许广平站在父亲鲁迅的墓前。周海婴出生时,鲁迅已48岁(许广平32岁),友人询问孩子姓名,鲁迅答:“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婴儿,就叫‘海婴’吧。”有人认为此名草率,鲁迅在《答客诮》中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对许广平笑称:“若孩子长大后嫌名字俗气,可自己改掉,反正我取的名字只算暂用。” 上海滩的雾气中,一个迟来的孩子落地,父亲随口取名“海婴”,旁人笑称太随意。谁知这名字后,藏着鲁迅对儿子的深情嘱托?十年光阴弹指过,墓前母子凭吊,那份家国情怀,又如何在新时代延续? 说起鲁迅一家,那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上海说起。那时候,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欺压的乱局里,鲁迅先生作为革命文学的战士,用笔杆子戳破黑暗,唤醒老百姓的觉悟。他和许广平女士,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早年许广平投身妇女运动,两人走到一起,共同扛起那份为民族担当的责任。 1929年9月27日,海婴出生在上海的砖木平房里,那年鲁迅四十八岁,许广平三十二岁。这个儿子来得晚,却像一盏小灯,照亮了他们战斗中的小日子。上海租界区的汽笛声天天响,街上黄包车来来往往,鲁迅先生一边写文章,一边操心家事,许广平女士则操持着家务和孩子的起居。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动荡年头,显得格外珍贵。它不光是个人小窝,更是革命者对未来的寄托。 孩子出生没多久,友人来探望,客厅里挤满人,大家端着茶碗闲聊。有人问起名字,鲁迅先生想了想,说生在上海,就叫海婴吧。意思简单,直白,就是上海的婴儿。话一出口,有人觉得这命名太草率,没什么讲究,像随口说说而已。鲁迅先生没争辩,只是笑了笑,继续抽他的烟。没过几天,他提笔写下那首《答客诮》,里面有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这诗直戳人心,意思是说,对孩子有点疼爱,怎么就不是大丈夫了?那些说闲话的,其实没懂鲁迅的真意。他后来对许广平说,这名字要是孩子长大觉得俗,就让他自己改,反正我取的也只是暂时的。许广平听了,点点头,继续照顾孩子。这事传开后,大家渐渐明白,鲁迅先生取名不求花哨,只求实打实。他一辈子写文章,都是为了接地气,帮老百姓说话,这名字也一样,朴实中带着对儿子的期望:长大后要像海浪一样,奔腾向前。 鲁迅先生对海婴的教育,从来不搞空洞说教,而是从生活小事入手。他知道,革命者要教孩子,也得从实际抓起。海婴小时候,鲁迅先生常在夜里写稿,海婴就爱钻进书房,在纸上乱画。鲁迅先生见了,不生气,还把那画贴墙上,说这比他年轻时写得有气势。这样的鼓励,让海婴从小就知道,动手试错,才是学知识的门道。 鲁迅先生从日本带回铁皮玩具,鼓励海婴拆开研究。海婴把留声机拆坏了,鲁迅先生没骂人,反而和他一起看齿轮怎么咬合,说懂了原理,比东西完好更要紧。后来,海婴得到儿童显微镜,用来看苍蝇腿,不小心摔碎了镜片。鲁迅先生安慰说,看清一半也算收获,下次找个结实的。这些事,都在上海的旧宅里发生,门外是租界的喧闹,屋里是父子间的传授。许广平女士在一旁帮忙,提醒别太惯孩子,但她也明白,鲁迅先生这是用实际行动,教海婴做个求真的人。 鲁迅先生的教育,还带着对民族未来的眼光。他希望海婴别走弯路,长大后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别当空头文学家。那时候,上海是半殖民地城市,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就是要让中国人醒醒神。家里虽小,却总有文友来往,大家讨论时事,海婴听着听着,就懂得了国家大事。鲁迅先生偶尔放下笔,陪海婴玩积木、折纸,甚至趴地上当马骑。许广平女士说小心腰病,鲁迅先生笑称这是周家的健身法。这些小插曲,表面上看是家常,骨子里是革命家风的延续。鲁迅先生知道,孩子将来要面对的,是更复杂的斗争,所以从娃娃抓起,教他独立和动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北京逝世,那年海婴才七岁。许广平女士强忍悲痛,带着儿子整理遗稿,守护鲁迅的著作。她们母子从上海迁到内地,又北上北京,继续生活。鲁迅先生的离去,让海婴早早懂事,他开始帮母亲分担家务,也继承父亲的求真精神。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广平女士教育海婴要自立,要投身实际工作。海婴听了,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当工程师,还搞摄影,一辈子拍了两万多张照片,记录老百姓的日子。这些选择,都源于鲁迅先生的遗愿:做个实干家,别空谈。 十年过去,1946年,许广平和海婴回到上海万国公墓,站在鲁迅墓前。那是秋天,松柏肃穆,母子俩默立良久。海婴那时十七岁,已是半大小伙,他看着墓碑,想起父亲的教导。许广平女士拉着儿子的手,轻声诉说往事。这次凭吊,不是简单的缅怀,而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鲁迅先生一生的战斗,海婴用实际行动接棒。他后来从事无线电工作,参与国家建设,还整理父亲的遗作,让鲁迅精神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