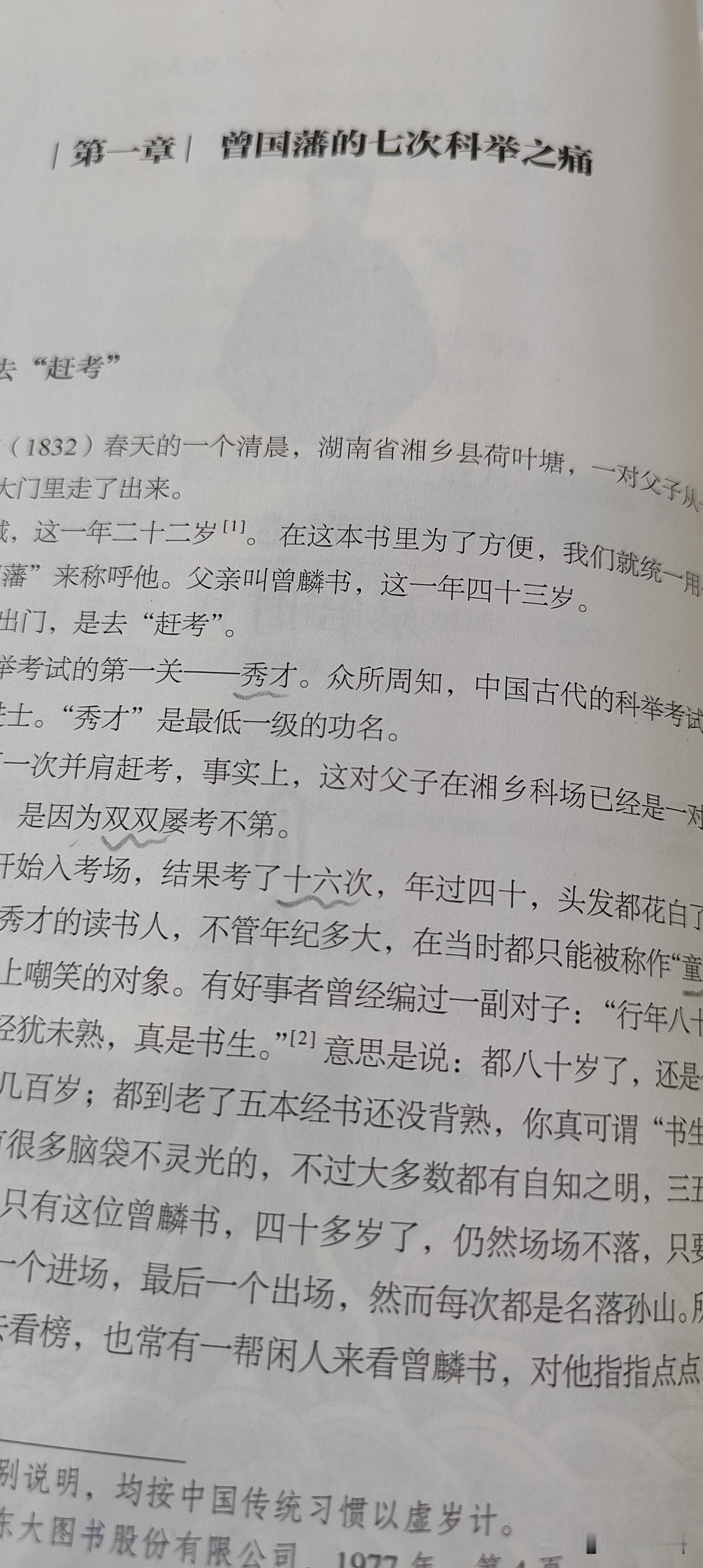西汉功臣集团何时有了拥立新君的心思? 西汉功臣集团的拥立新君之心,实则萌发于吕后称制后期,成型于诸吕覆灭的刀刃之上。 这不是一场临时起意的政变,而是刘邦死后十七年里,功臣集团与吕氏外戚、刘氏宗室三方势力反复拉扯的必然结果。 刘邦临终前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看似为功臣集团撑起保护伞,实则埋下了权力结构的死穴。 汉初分封的十八列侯,萧何、曹参等文臣尚可安居相位,周勃、灌婴等武将却始终被刘邦用吕氏外戚制衡——太尉周勃空有军职却不得入北军,樊哙娶吕后妹吕氏更成刘邦监视功臣的眼线。 这种"用你却防你"的微妙关系,在刘邦死后随着吕后逐步夺权而激化。吕后封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时,功臣集团发现当年的盟誓成了空文:吕氏外戚可以突破"非刘不王",功臣集团却连军权都被吕氏子弟瓜分。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吕产掌控南军、吕禄节制北军,长安城防尽落外戚之手,周勃身为太尉竟"不得入军门",这种羞辱让功臣集团意识到:若吕氏坐稳江山,他们或将步韩信后尘。 真正让功臣集团动了换君念头的,是吕后临终前的政治布局。她任命吕产为相国、吕禄之女为少帝皇后,等于将皇权与军权死死绑在吕氏战车上。 此时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陈平、周勃已达成共识:吕氏不除,功臣必亡。但诛吕易,立新难——刘邦子嗣中,齐王刘襄兵强马壮,却有母族驷氏"虎狼之患";淮南王刘长年幼,背后是吕后抚养的复杂背景。 唯有代王刘恒,母亲薄氏出身低微,封地贫瘠且远离中枢,更重要的是,刘恒从未介入吕后时期的权力斗争,对功臣集团没有历史恩怨。 这种算计在诛吕当晚便初见端倪。当刘章斩杀吕产的捷报传入太尉府,周勃没有立即拥戴随军的齐王刘襄,反而派刘泽前往代地"迎驾"。 表面看是遵循"立长"祖制,实则是功臣集团在算三笔账:其一,齐王刘襄在诛吕中擅自发兵,暴露了他不甘居人下的野心,若让其继位,难保不会重演刘邦清洗功臣的旧事;其二,刘恒母族薄氏"无势力根基",符合功臣集团"弱主易控"的需求。 正如陈平所说,"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这些标签背后都是功臣集团的安全考量。 其三,刘恒继位前主动诛杀吕氏妻族,既向功臣表了忠心,又彻底斩断了外戚复辟的可能,这种政治默契让周勃等人确信:这是个能与功臣集团"共治"的皇帝。 更深层的动因,藏在功臣集团的集体记忆里。自刘邦剪除异姓王开始,萧何下狱、樊哙险死、韩信夷族的教训历历在目。他们太清楚,皇帝的"仁孝"远不如权力制衡可靠。 吕后称制时,功臣集团尚能凭借资历勉强存活,但若新君是强势宗室,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新一轮清洗。代王刘恒的"无害性",恰恰源于他十七年的边缘处境。 当齐王刘襄在山东经营封地、淮南王刘长在长安受宠时,刘恒在代地"亲耕于野,薄葬以教",这种远离权力中心的经历,反而成了功臣集团眼中的"安全认证"。 公元前180年闰九月,当刘恒的车驾驶入渭桥,迎接他的不仅是群臣跪拜,更是功臣集团精心设计的政治契约:皇帝承认功臣的拥立之功,功臣保证不干涉皇权。 这种默契在刘恒继位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他迅速册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却在三年后借"日食异象"罢免周勃,既维护了功臣颜面,又收回了军权。 这场看似平和的权力交接,实则是功臣集团用拥立新君的机会,为自己换取了最后二十年的政治安全。 从吕后驾崩到文帝登基的四十三天里,功臣集团完成了从"保身"到"造君"的蜕变。他们的拥立新君之心,始于吕后对白马盟誓的践踏,成于对刘氏宗室的猜忌,最终落子于代王刘恒的"可控制性"。 这不是简单的政治投机,而是一群经历过刘邦清洗、吕后压制的幸存者,在皇权真空期的集体自救。 当刘恒在渭桥下车的那一刻,西汉初年的三方博弈正式落幕——功臣集团用拥立之功换取生存空间,刘氏宗室以弱势之姿重掌皇权,而那个被史书称为"仁孝"的文帝,早已在代地的风沙中,学会了如何与功臣集团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