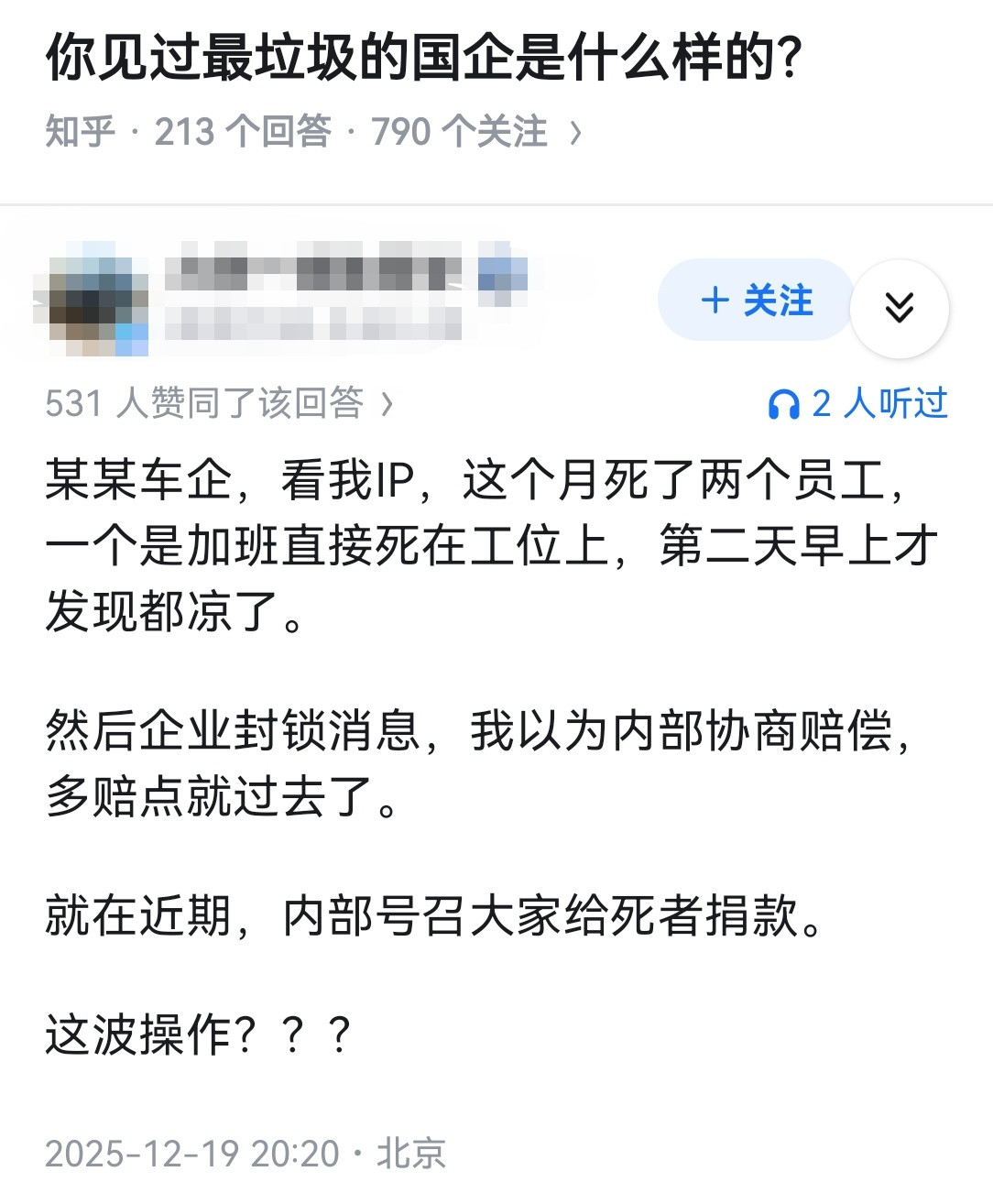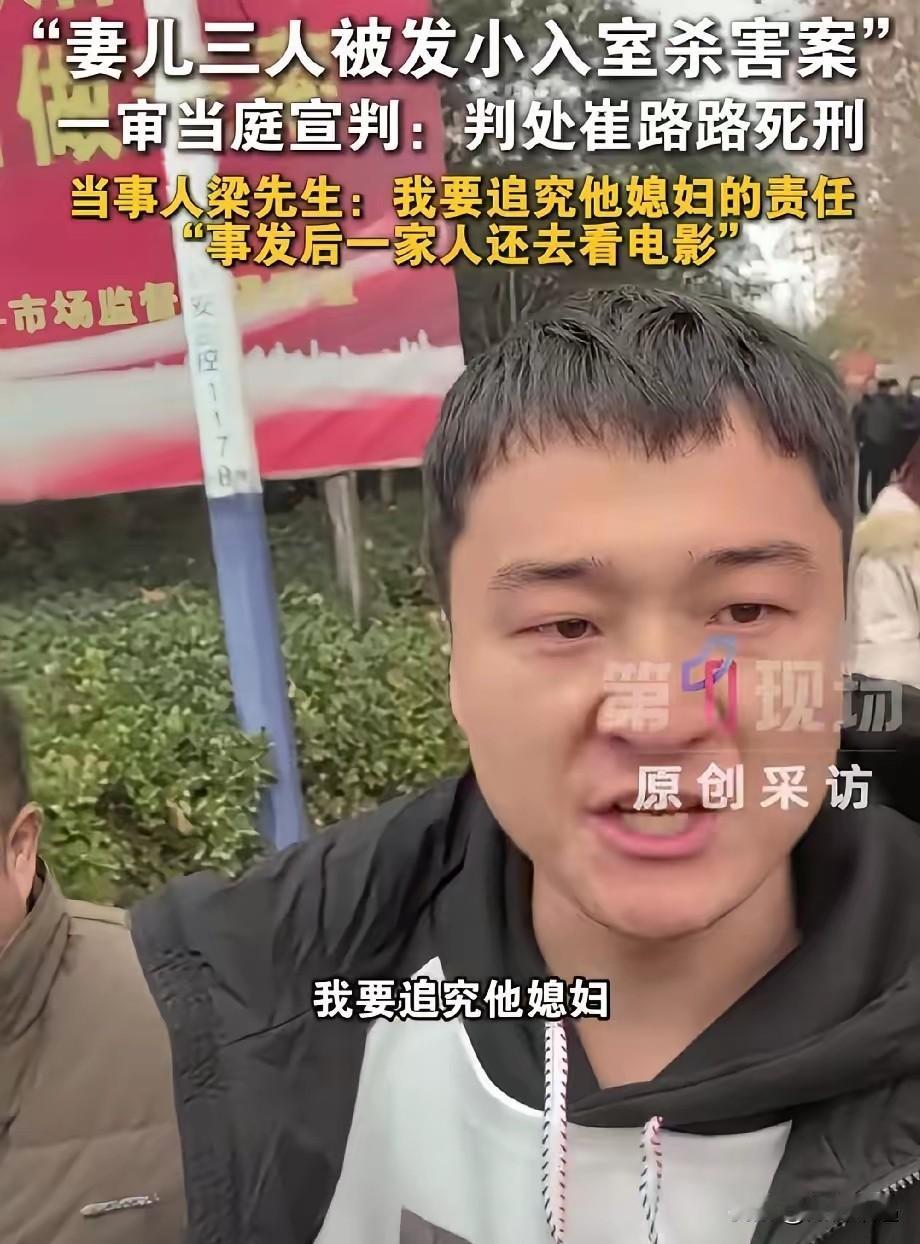对门老张头走了有三个月,他老伴就开始收拾东西。那天我下楼倒垃圾,看见楼道里堆着老张头的钓鱼竿、象棋盘,还有那件他总穿的棕色皮夹克。我停下脚,盯着那根钓鱼竿看了半天。老张头生前最宝贝这个,退休后几乎天天扛着它去护城河,回来要么拎着半桶鲫鱼分给邻居, 对门老张头走了三个月,他老伴张阿姨终于开始收拾东西了。 那天我拎着垃圾袋下楼,刚拐过三楼平台,就看见楼道里堆着半人高的物件——最显眼的是那根翠绿色钓鱼竿,竿梢缠着圈旧胶布,旁边是磨得发亮的象棋盘,还有件眼熟的棕色皮夹克,拉链头掉了半颗齿,是去年冬天老张头帮我够阳台花盆时拽坏的。 空气里飘着点樟脑丸的味道,混着皮夹克上洗不掉的河腥味——那是护城河的水、水草和老张头身上烟草味揉在一起的味道。 我停住脚,盯着钓鱼竿发愣。 老张头退休后几乎天天扛着它出门,早上去护城河,傍晚踩着夕阳回来,要么拎半桶活蹦乱跳的鲫鱼,挨家挨户敲门分;要么空着手,坐在楼道台阶上跟下棋的老李叔念叨“今天水凉,鱼不上钩”,手里却总攥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给张阿姨买的糖炒栗子。 “小周啊,倒垃圾呢?”张阿姨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抱着个纸箱,额角沁着汗。 我赶紧把垃圾袋放墙边,帮她扶了扶快歪的纸箱:“张阿姨,这……这些都要处理啊?” 她低头扫了眼那堆东西,嘴角往下撇了撇:“放着占地方,他走了,钓鱼竿没人扛,象棋盘没人摸,皮夹克……我穿着也不合身。” 我指尖碰了碰钓鱼竿的胶布——去年冬天他在河边滑了一跤,竿梢磕在石头上裂了小口,我找了卷电工胶布帮他缠,他当时拍着我肩膀笑:“还是小周手巧,这竿子跟我十几年了,比老伴还亲呢!” 现在那胶布边缘有点起毛,像谁悄悄哭过的痕迹。 “其实……”张阿姨突然蹲下身,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个用塑料袋裹着的小本子,“他走前半个月,手抖得拿不住笔,还硬要写这个。” 我接过来翻开,泛黄的纸页上是歪歪扭扭的字:“钓鱼竿送给老李,他总说我竿子软;象棋盘给三楼小王,他家小子爱下棋;皮夹克……留给老伴吧,天冷穿,就是拉链得修修——” 后面还有行更小的字:“要是修不好,就放衣柜最上面,闻闻味儿也行。” 我鼻子一酸,抬头看张阿姨,她正用袖子抹眼角:“这些天我翻箱倒柜,把他写的字条、捡的鹅卵石、钓上来又放回去的小鱼鳞都收进铁盒子了——堆楼道的这些,是他生前总念叨要‘送朋友’的,我怕忘了,一条一条对着本子理呢。” 那些我以为要被丢弃的物件,原来每一件都带着他的“安排”;那些张阿姨说“占地方”的东西,其实是她捧着回忆在完成老伴的心愿。 老李叔来取钓鱼竿时,摸着胶布愣了半天,突然说:“下周我还去护城河,替老张钓条大的——他总跟我吹他钓的鱼最大。” 三楼小王抱着象棋盘,蹲在楼道里摆了局“马后炮”:“张爷爷上次跟我下就用这招赢的,我得学会了,以后教我儿子。” 张阿姨站在门口看着,脸上的皱纹里慢慢漾开点笑:“你看,他走了,这些东西倒替他‘说话’了。” 那些我们以为会随着人离开而消失的痕迹,原来都藏在物件的温度里——一根缠着胶布的钓鱼竿,一盘磨亮的象棋子,一件掉了拉链的皮夹克;它们不会开口,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楚地告诉你:爱从来不是减法,是把一个人的温度,分给更多人。 现在每次路过护城河,总能看见老李叔扛着那根翠绿色钓鱼竿,身边跟着小王的儿子,举着个小抄网;傍晚他们回来,照样挨家分鲫鱼,只是到我家门口时,老李叔总会多放一条:“给你张阿姨留的,老张说了,他老伴最爱喝鲫鱼汤。” 楼道里的樟脑味散了,河腥味却好像更浓了些——那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光,给世界留下的、带着暖意的回声。 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要留下点什么才算没白来? 或许,就是让那些你爱过的、在意过的,带着你的样子,继续热气腾腾地活着。
我出差一个月回来,发现邻居在两个门之间放了一个防盗门护栏,虽然说没有越界到我家这
【7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