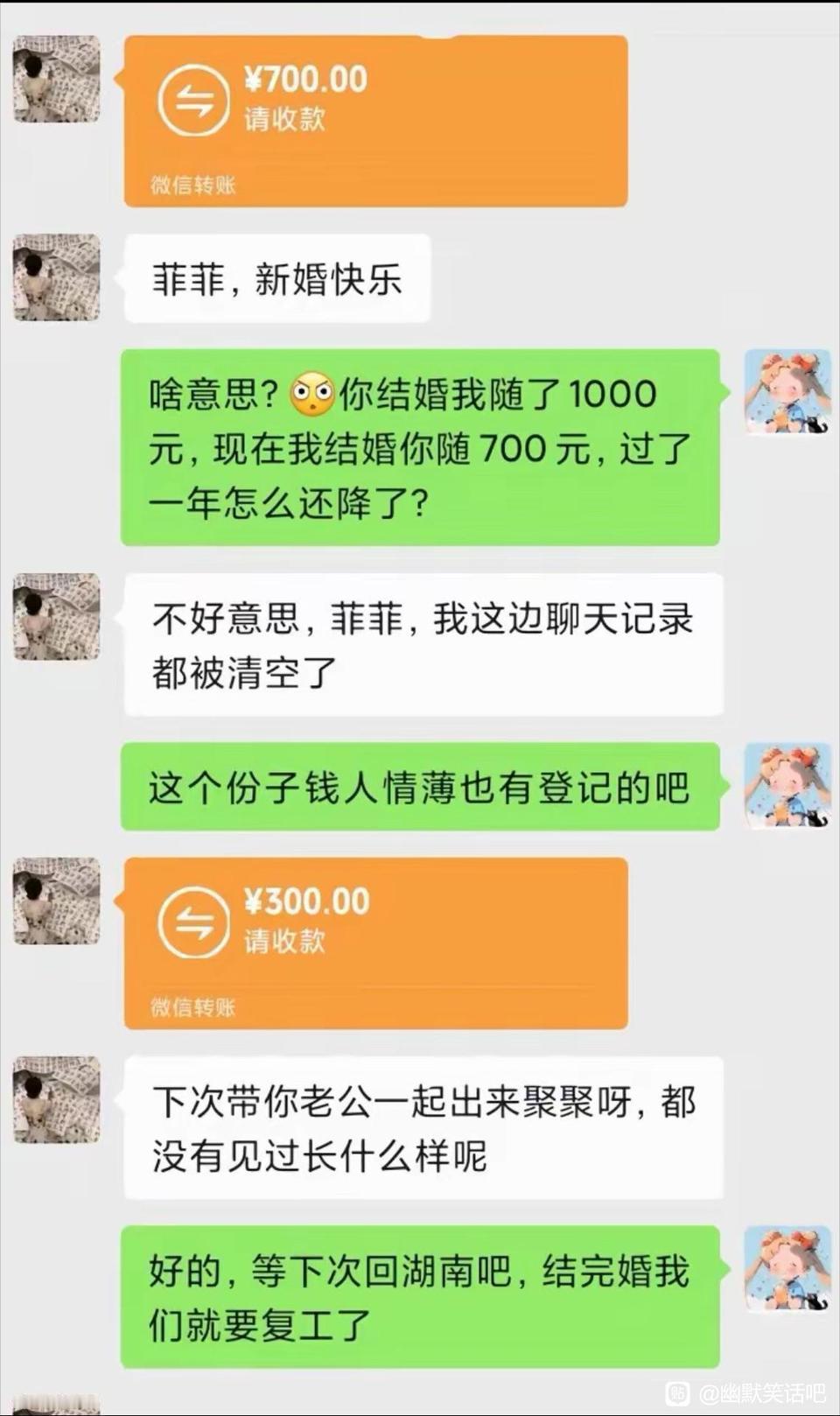这辈子,我有两个爹。一个是我的亲爹,一个是邻居张叔。亲爹走得太早,没享过我一天福;张叔和我没血缘关系,却在我家天塌的时候,硬生生替我们撑住了那根柱子。 我叫李伯农,1956年出生在荣昌的农村,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母亲自从生了小妹后,身体就一直不好,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撑着,日子过得有些艰难。 1974年冬天,我抓到一个绝佳的机会:参军入伍。那时候当兵是农村青年少有的出路,不但能为家里省下口粮,还能将积攒下来的津贴寄回家改善生活。 父亲是个木讷寡言的人,在我离开的时候,竟然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心里话。他还往我兜里塞了两个煮鸡蛋,“伯农,到了部队干出个名堂。有我在,屋头的事你不用管。” 那时候,我以为父亲真的就像老家的大山那般可靠。可正当我在新兵营接受训练时,一封电报却让我措手不及。上面只有五个字:父病危速回。 这个五个字让我一阵恍惚,从小到大我还没经历过这般慌乱的时候。我拿着电报哭着去找领导请假,领导很通情达理,批准了我的假期。 一路上我都在祈祷,希望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可当我跌跌撞撞冲进家门,看到的不是父亲坐在板凳上抽烟,而是堂屋正中间那口棺材。 那一刻,我愣在了原地,直到母亲哭晕在我怀里,四个小的抱着我的腿喊“哥哥”,我才“哇”地一声哭出来。父亲是在地里干活时突发心梗走的,没能留下一句话。 我们家是外来户,爷爷当年逃荒落脚到这儿,村里也没啥亲属。在农村,家里没壮劳力,又是外姓人,办丧事是最难的。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一时之间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家里六神无主的时候,邻居张叔站了出来。张叔是个暴脾气,大嗓门,但心肠很热。他到处张罗,还把自家儿子和侄子叫过来帮忙。我犹如提线木偶,在他的指挥下操办完了葬礼。 那天,张叔带着张家人,硬是帮我把父亲体体面面地送上了山。我回部队之前,去张叔家道谢。我跪下给张叔磕了几个头,他连忙将我搀扶起来,头一回听他那般和声细语道: “伯农,你回部队安心好好干,你家里的事我会留意的。你在部队发展的越好,就越没人敢欺负。有啥事,你给我写信就行。”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张叔就是我的亲人,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回到部队后,从老兵口中得知,像我这样新兵请假回去的,后面在部队不好发展。我心里一惊,这要是就当个三年就回了家,我怎么对得起父亲的遗愿,怎么对得起张叔的教诲。 我像疯了一样训练,不但缩短了和别人的差距,在出营时还得到了营里的嘉奖。下连队时,我被分到了侦察连。后面我在部队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当时请假的影响。 当兵第二年被提拔为副班长,第三年入党提班长,1978年底,我作为预提干部被推荐到了教导队。从教导队出来后,我回侦察连提干为排长,算时间赶上了提干的末班车。 1979年夏天,我回老家探亲,这也是我当兵几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我带了不少礼物去拜访张叔,这些年他没少帮忙。 张叔很直爽,并没有因为我成了军官而拘谨,反倒喝的很愉快。走之前,母亲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跟张叔的小女儿慧琴接触接触。 “伯农,这些年咱家多亏了你张叔。慧琴那姑娘,我也是看着长大的,是个实诚人,对咱家没二心。以后你长期在部队,咱们还是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你不要嫌弃她是农村户口……” 慧琴此时才18岁,小的时候我带她玩过,但自从她上初中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她了。我想了想,便让母亲去探探口风。等我回了部队,我们先通信联系。 等我回到部队没多久,就收到了慧琴的信。信里面透露出一丝温婉,几封信后,我也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1981年,我回家拎着两瓶酒、两斤肉、两斤点心去张叔家提亲。可待我说明了心意后,张叔却脸一沉,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出两个字:“不行。” 我和母亲都愣了,母亲连声说道:“张老哥,你看俩孩子都互相喜欢……” 张叔摆了摆手,“伯农啊,你马上要提副连了,将来还可能当连长、营长、团长,慧琴就是个农村丫头,初中都没读完。这门亲事,不般配。我也不能让你被人戳脊梁骨,说你是报恩才娶的她。” 原来张叔是怕耽误我。那一刻,也没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这次,张叔没拦住。 “叔,要是没有您,我爹走的那天这个家就撑不住了,我只有早早退伍回来。这些年,在我心里,您早就是我爸了。我不图别的,就图慧琴人好,咱们两家知根知底。我也不是啥首长,我就是农民的儿子伯农,是您的半个儿子!” 张叔的旱烟袋掉在地上,眼泪顺着那张黑红的脸膛往下流。躲在门帘后面的慧琴也冲了出来,哭成了泪人。 后来,我和慧琴结了婚。虽然她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她有着农村女人的坚韧和善良。我在部队干了二十五年,她替我守了大半辈子的大后方,照顾母亲,扶持弟弟妹妹,拉扯孩子。 现在我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常常和慧琴在老家院子里晒太阳。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除了当兵,就是娶了这个邻居家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