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8岁的徐悲鸿逝世,92岁的齐白石前来奔丧,只听扑通一声,老人直接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这吓坏了徐家人,赶紧阻拦,不料他痛哭道“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为过”。 那时候齐白石已经满头白发,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得靠人扶着才能动。可一到徐悲鸿的灵前,他猛地推开身边扶着的人,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单薄的身子对着灵位重重磕了三个响头,每一下都磕得特别实在,在场的人看着都跟着揪紧了心。 徐家人吓得赶紧上前想把他扶起来,毕竟老人都九十岁了,这么折腾太伤身体。可齐白石一把推开他们,双手撑在地上哭得停不下来,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哽咽着反复念叨,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算多。 在场的人见了这情景,没有一个不感动的,没人觉得这举动不合时宜,都明白这几个头里,藏着齐白石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情分。 大家都知道,齐白石原名叫齐璜,生在湖南乡下一个穷苦人家。小时候为了混口饭吃,他跟着师傅学做木匠,刻花雕梁就是他的本事,手里的刨子、凿子握了几十年,就靠这门手艺勉强养活自己。 后来年纪大了些,他凭着对画画的痴迷,慢慢改成靠卖画过日子。他把在田里、山野里常见的虾蟹虫鱼、花草果蔬都画到宣纸上,笔墨里全是烟火气,画得特别鲜活逼真。可这种接地气的画风,在当时的北平画坛根本没人看得上。 那时候的北平画坛,全被一群穿长衫的文人把控着,他们只推崇守规矩的古法画作,对齐白石这种没受过正统训练、画风又野趣的作品特别看不起,动不动就嘲讽他的画是“野狐之禅”,还说这种沾着泥土味的东西,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 那些年齐白石在北平过得特别难,就是个苦苦挣扎的“北漂”艺人。他的画挂在琉璃厂的铺子里,就像放在没人搭理的煤铺角落一样,常常摆好几天都没人多看一眼。 就算有人问价,给的钱也少得可怜,一个扇面只卖两圆银币,比当时普通画家的价格低一半,照样没什么人买。北平画坛的那些大佬,比如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北京美术学校校长余绍宋等人,对他的画更是冷嘲热讽,还公开批评他画画不守古法,简直荒谬至极。 甚至有人放话,说齐白石的画根本不入流,就是个匠人瞎画的。有一次他去一个官家的应酬场合,因为穿得朴素,身边又没有熟人为他周旋,一桌子的有钱人没一个愿意搭理他。那份难堪他记了一辈子,也更懂了人世间的冷暖。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他只能一边琢磨着改进画画的技法,在画好的花卉上添上精细的草虫,让买画的人觉得值这个钱,一边靠刻印章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温饱都快顾不上。 齐白石这一辈子,遇到过两个懂他的贵人,一个是陈师曾,另一个就是徐悲鸿。陈师曾曾经把他的画带到日本展出,这让他的作品第一次卖出了高价,还指点他完成了“衰年变法”,创出了独一份的“红花墨叶”画风。 可陈师曾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没人搭理、孤立无援的境地。就在他快要被画坛彻底排挤,画画的路子走不下去的时候,徐悲鸿向他伸出了手。 这份帮助不是简单的可怜,而是打心底里的尊重和扶持。那时候徐悲鸿是海归派艺术的代表人物,在画坛地位很高,可他偏偏看重齐白石的才华,不顾身边人的反对,非要请这位民间老艺人去大学里当老师。 当时学校里不少教国画的老师偏见特别深,还放话说要是齐白石从前门进学校,他们就从后门走。但徐悲鸿顶着这些压力,硬是把齐白石请进了课堂,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让他彻底摆脱了“画匠”的标签。 徐悲鸿对他的帮衬可不止这些。每次有画展,他都特意抬举齐白石。有一次他看到齐白石的画被挂在展厅角落,标价才八块大洋,连三流画家的画都比不上。 他当场就把这幅画挪到了展厅最中间,亲手把价格改成八十块大洋,还把自己作品的价格降到七十块,就是想让世人看到齐白石的价值。为了扩大齐白石的名气,他还说服中华书局出版《齐白石画册》,亲自整理画册内容,还写了序言。 序言里他极力称赞齐白石的画,说他的画能细致地描绘事物,完全是独创的风格,把那些人诟病的“野趣”,精准说成了艺术上的独到之处。 平时生活里,徐悲鸿也格外照顾齐白石,常常花三倍的价钱买他的画,暗地里帮衬他的家用。这份知遇之恩,让一辈子受够冷眼的齐白石心里特别暖和。 齐白石曾经真心实意地写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这句话把他对徐悲鸿的感激全说透了。在那个看重出身、讲究门派的年代,没人愿意正眼瞧一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家。 只有徐悲鸿,不在乎他的出身背景,也不纠结他的画风合不合正统,只凭着作品本身的好坏,给了他最高的认可。 是徐悲鸿,把他从被画坛排挤的边缘,拉到了艺术殿堂的中央,让他的才华被所有人看见。也正是因为徐悲鸿,他才从一个卖画都难的匠人,变成了后世都敬仰的艺术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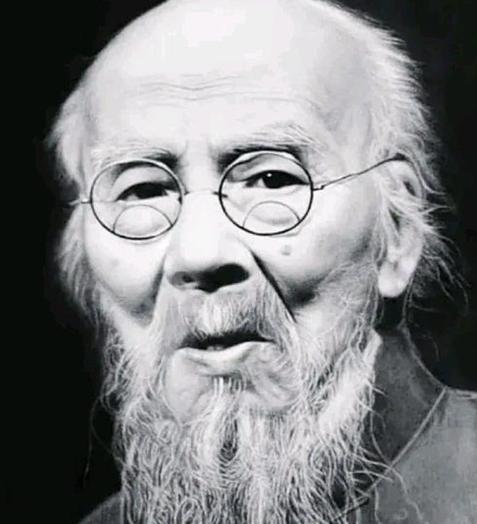


![大清朝想退回老家的,我们教导员眼光长远[赞]](http://image.uczzd.cn/1488546175183482161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