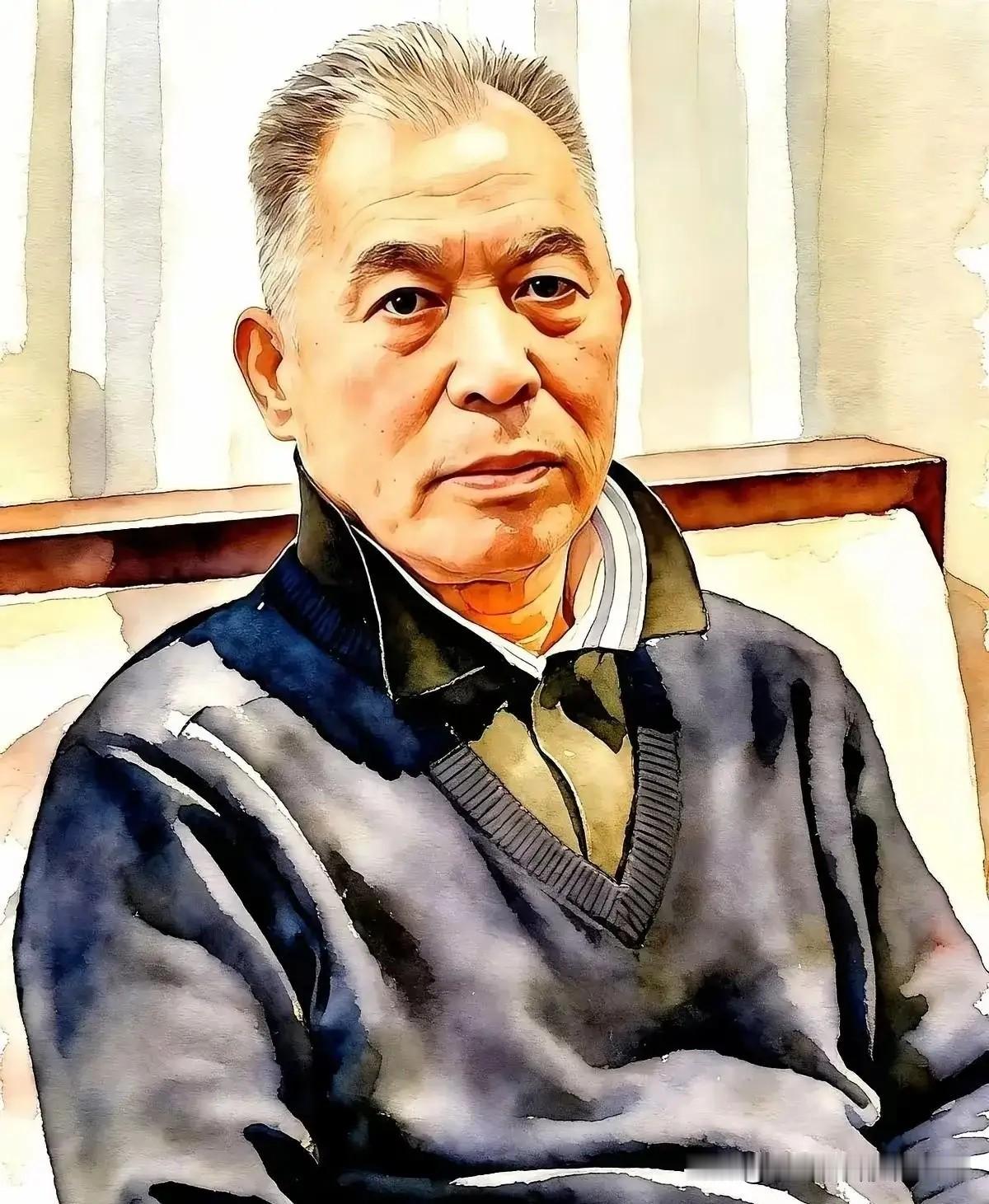我爷爷的一缸银元,我爸和我伯挖了几晚上没挖到,这个秘密是我爷爷咽气前说的。 挖完那几晚上,我爸和我伯脸都绿了。枣树下就剩个半米深的坑,土翻得乱七八糟,啥也没找着。两人在院子里吵了一架,都说对方偷摸藏了,最后摔了铁锹各走各的。那之后,兄弟俩好几年没搭话,老宅的门锁锈得厉害,推都推不开。 去年开春,村里突然来了通知,说老宅那片要划给开发商建民宿,限期搬空。我爸捏着通知单,坐在沙发上抽了半包烟。第二天一早,他喊我回去收拾,说赶在拆之前把能拿的拿走。老宅里一股霉味,阳光从破窗户斜进来,灰尘在光柱里打转。我爸闷头进了西厢房,盯着那个长满草的坑看了会儿,转身去搬爷爷的旧衣柜。 衣柜后头有个暗格,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爸掏了半天,摸出个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不是银元,是两张发黄的房契,还有一封信。信纸脆得碰不得,我爸小心翼翼展开,就着窗口的光看。风扇在墙角吱呀呀转,吹得信纸边角直抖。 信是爷爷写的,字迹歪斜,说那缸银元早就没了。六几年闹饥荒的时候,他偷偷把银元分批卖了,换粮分给了村里最难的几户人家。“枣树下三尺,埋的是咱家的良心,”信里这么写,“别怪爹骗你们,爹是怕你们兄弟俩眼里只剩钱,忘了人该怎么活。” 我爸捏着信,半天没动弹。外头忽然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停在了院门口。是我伯,他听说要拆老宅,也赶过来了。两人在院子里碰见,都有些尴尬。我爸把信递过去,我伯蹲在门槛上读完,眼圈慢慢红了。 那天下午,他们没再收拾东西,反而一起找了铁锹,把那个坑边的杂草清了清。我伯从摩托车上拿下来两瓶水,递给我爸一瓶。两人就坐在枣树底下喝,话不多,但肩膀挨着肩膀。 后来老宅还是拆了,但兄弟俩合资在县城开了个小铺子,卖农具种子。铺子后院种了棵枣树苗,是从老宅那棵树上截的枝。我爸说,等树长大了,也许就能明白爷爷到底留了什么——反正不是银元,是比银元更难挖出来的东西。
“你是要我跟你一起过苦日子吗?”这话,是一个漂亮空姐,对着相亲的28岁小伙子说
【11评论】【7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