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再一次爆发了。
逼仄的琴房里,秀玮沉着脸问女儿Sasa:“左手这里弹得乱七八糟,你在弹什么?”一个小时的钢琴练习之后,是一个半小时二胡,Sasa疲惫不堪,起身要去找外婆告状,秀玮走出房间,并给房门上了锁。
对于九岁的女儿,秀玮有两个期待。一个是未来考进新加坡青年华乐团,另一个是在不久后的GEP考试(天才班选拔)中入选。职业音乐演奏家是秀玮自己未能完成的梦想,而“天才班”,每年只有1%同龄学童能入选。
这是纪录片《了不起的妈妈》中一个普通华人母亲的故事,纪录片是一年前的母亲节前夕推出的。导演为这一集取名为《在新加坡养娃,如何成为“卷王”》。众所周知,在基础教育领域,新加坡教育位于“卷”的金字塔尖。
拍摄之初,导演姜又兮和团队访谈了一百多位妈妈,最终,12位女性的教育故事呈现在纪录片里,这其中有被新加坡教育分流体制追赶的秀玮、有想把儿子送到早培班的海淀妈妈李琦,还有不愿让孩子待在上海弄堂里上“菜小”的妈妈阿胖。
每个教育故事都无法绕开“妈妈的选择”。但姜又兮希望观众们不要去寻找“什么是最好的教育”的答案,而是要看到母亲们托举下一代的爱与耐心。事实上,这三位对孩子有着宏大教育理想的妈妈,最终都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原本的想法。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直以来,母亲一词被赋予爱与奉献的崇高意义。但为什么是母亲承担了愈加繁重的教育责任?
“那不是我的梦想”新加坡的小学下午一点半放学,下午和晚上,大部分学生会参加不同的课外活动。每个周一,Sasa要留在学校上高等华文课;周四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其他日子还有武术、舞蹈、潮剧等课程。回家后,她还要完成作业,之后就是每天固定的钢琴和二胡时间。秀玮常常无法忍受女儿错掉的音,“只能强撑着听下来”。
秀玮希望女儿能感受在音乐中发现美,和自己一样。秀玮出生于福建漳州,20岁时考入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此后在新加坡工作、结婚、生子,成为新一代移民。
9岁的Sasa在读小学三年级。在新加坡久负盛名的基础教育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每年8月,新加坡教育部都会组织三年级学生参加高才教育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简称GEP)选拔。通过两轮考核,全新加坡大约有五百名学生能够进入“天才班”学习。

纪录片《了不起的妈妈》截图,Sasa在练二胡。 (资料图/图)
“天才班”意味着更好的教育资源。在三年后的分流考试中,“天才班”将有近60%的学生进入直通车计划,未来可以不经过被称为新加坡“中考”的O水准考试(Singapore-Cambridge GCE' O' Level),不必面临分流,到六年后直接参加A水准考试(Singapore-Cambridge GCE' A' Level,相当于中国高考)或其他相等文凭考核。非“直通车计划”则面临着在O水准考试后被分流到非学术类学校的可能(类似于新加坡版“普职分流”)。
四千多公里外,北京海淀妈妈李琦在为小升初发愁。李琦的大儿子小帅12岁,在著名的人大附小读六年级。为了能顺利升入人大附中,李琦曾考虑让孩子参加人大附中早培班的考试。
相较于已经在学初高中数学的同学而言,小帅的成绩常常排在班级的中下游。而人大的早培班是在全市五年级的小学生中选拔约180人,往年的招生标准显示,入读孩子应当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品德优良、智力超常,具有特殊才能和创新潜质,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明显超出同龄人。
纪录片中还有一位上海妈妈阿胖,为了让儿子小田进入上海教学质量最好的民办小学,阿胖在小田幼儿园中班时,就安排他学小学一年级的内容,练习入学考试真题,上面试辅导班,甚至准备了一段英文自我介绍。
然而,随着2019年上海幼升小入学新政出台,小田被摇号摇进一所离家不远的普通公立小学。得知结果时,阿胖在办公室哭出了声。但很快,阿胖就找到了一个转学中介,中介费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交了钱后,小田就开始排队等待优质校的转学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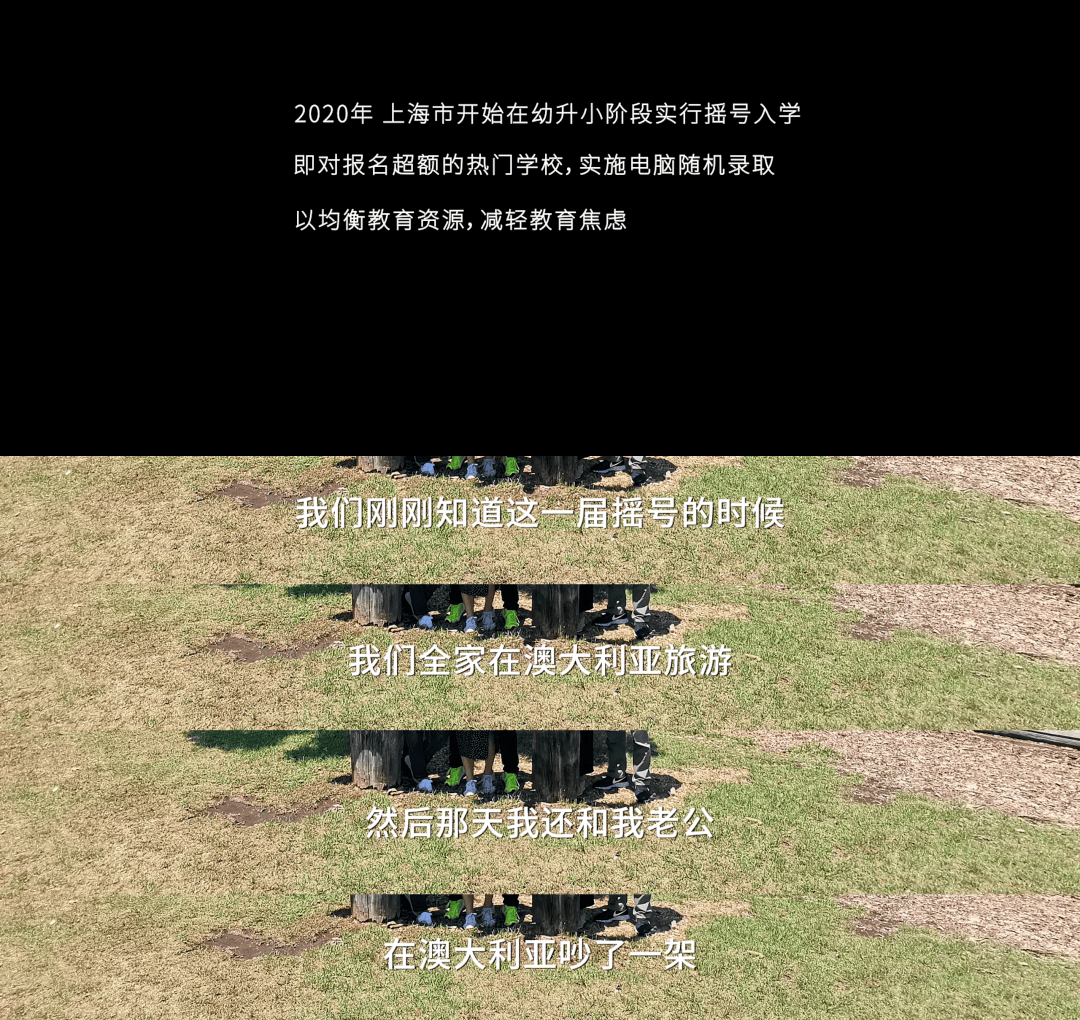
纪录片《了不起的妈妈》截图,小田被摇号摇进菜小。 (资料图/图)
这些妈妈对孩子的期待不止一个。
秀玮对Sasa阶段性的期待是她能够考进二胡奖学金计划,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和表演机会。但Sasa的二胡老师许文静并不赞同,许文静是新加坡华乐团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她认为Sasa年纪还小,而且练习奖学金面试的曲目会耽误原有的学习进度。
“反正就是要考进,我妈妈逼我考进。”
画面外导演问:“你觉得你能考进吗?”
“我不懂,因为那不是我的梦想。”
保持层次不掉队为了让孩子在竞争中胜出,妈妈们想了很多办法。
那一年,人大附中早培班数学考试的最后一题是图论题。李琦请教了两位清华毕业的同事,其中一位在高中入选奥赛国家队,另一位是计算机博士——但他俩也没能做出那道图论题。
李琦想过请名师对儿子一对一辅导,但又不想让他压力太大。小学阶段,她曾经为小帅报过五花八门的课外班,但对提高课内成绩成效不大,最终小帅只保留了数学、英语、编程和体能四个课外班。
同样焦虑的还有阿胖。在给转学中介交了钱之后,真正的鸡娃才刚刚开始。阿胖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在外企工作,她把鸡娃当做一个工作项目,认真制定KPI。
三点放学,阿胖要带小田去辅导机构上乐高课,为编程打基础。吃完晚饭,她为小田安排了各科练习,由她亲自辅导。阿胖认为这些练习能够很好地检验小田的知识是否掌握牢固。练习结束后,小田还要练习1个小时大提琴,阿胖仍然要在旁边全程监督。完成这些,已经到了晚上十点。
阿胖的父母觉得她太“鸡血”,劝她放养,就像她小时候那样。但阿胖希望小朋友能学更多东西,在未来多一些选择。这跟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大学时,阿胖一直想读中文系。但爸爸觉得法律和经济的就业前景更好,于是阿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走了一条更稳妥的道路。她不希望小田未来也只能选择“稳妥”。
有时,家长会尽力去寻找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他们期待孩子能显露出某些能让他们逃离教育焦虑的天赋。
在这个意义上,小帅又是幸运的。李琦发现,小帅喜欢玩游戏,擅长编程。他已经拿到中科院计算所的一级程序员证书,经常在知乎给想买电脑的网友出配置单。小帅还在B站当UP主,有八百多个粉丝,他的梦想是当程序员或者全职UP主。小帅很有商业头脑,学校的排球队去宁波,小帅用两百块钱买了同学爱吃的辣条和可乐。目的地没有小卖部,同学们又渴又累,小帅把原价三块钱的可乐翻倍卖出,最后赚了六百多块钱。
教育的方式千变万化,但家长对于孩子最终的期待却是相似的,“不说跨越阶层了,保持层次不掉队就很难了。小田如果没有考上高中只考上职校,那可能就完全脱轨了。这并不代表他一定活得不开心,至少我这个旁观者会觉得好可惜”。

2023年2月15日,上海某小学开学。 (视觉中国/图)
学习成为母亲这样的焦虑,或许与母亲们的成长之路息息相关。每一位母亲都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学着如何成为一名母亲,这中间,她们要学习如何与日渐增长的照料责任、个人梦想和自我实现妥协,也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冲突。
秀玮在一个华侨农场长大,居民们大部分是东南亚归国华侨和他们的后代。在这个音乐匮乏的环境中,秀玮的母亲咬牙给女儿买了农场里的第一架钢琴。学琴过程中,周围的同龄孩子纷纷放弃,只有秀玮坚持了下来。做教师的母亲严厉且认真,即使下大暴雨,也要用摩托车载秀玮去学琴。
秀玮最终没有走向职业音乐演奏家的道路。20岁时,她被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流行音乐专业录取。那时她对流行音乐兴趣寥寥,又担心毕业后的生计,也没有考取奖学金的信心。
那是2007年,新加坡的酒店业正在蓬勃发展,母亲建议秀玮换到酒店管理专业试试。毕业后,秀玮进入一家知名酒店集团。六年后,她所在的团队接手了一家新的酒店,他们想让秀玮担任一个部门的领导。秀玮还记得新酒店定位高端,卫生间里的用品来自奢侈品品牌,这让她有些恐慌。她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无法承担起管理整个部门的责任。
秀玮离开酒店后的职业选择,则往往会考虑如何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她去了新加坡华乐团,后来又到一家科技公司当文员。在此过程中,除了照料孩子外,她也一直没放弃钢琴。
与秀玮相比,其他母亲的成长之路稍显顺遂。
李琦和丈夫都有海归背景,他们从没为学习发过愁。丈夫从小学开始就一路保送,念“西城四大金刚”的北京八中,现在是央企设计院研究员。李琦从内蒙古考到北京,毕业后进入互联网公司,自己攒够学费之后去美国留学。2005年,李琦从硅谷回国,作为创始员工参与谷歌中国创办,回国时,与李开复搭了同一架飞机。阿胖和丈夫都是上海本地人,他们的生活是本地家庭稳扎稳打、按部就班的典型。
这些母亲都需要平衡工作和育儿之间的关系。而家庭中的父亲,“可以出现,可以不出现”。纪录片中,当阿胖在鸡飞狗跳地辅导小田功课时,镜头对准了阿胖的丈夫:他在沙发上打游戏、看视频;过了一会儿,他去厨房给阿胖和小田切了些水果。
对于李琦这位事业型女性而言,孩子的到来间接让她错过了几次升职加薪的机会。她1999年就进入互联网行业,几年内成为总监,但有了孩子后,她几经周折,不再带团队,“可以更好地陪伴小帅和小亮”。
刚有小孩的一两年,李琦在平衡家庭和职位晋升中反复纠结。当时她的实习生是心理学专业的,她请实习生帮忙分析她的心理波动。实习生让李琦写下十个对她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再一项一项删掉,最后只保留三个。在最后的三个答案中,家庭都排在了事业之前。
秀玮说,《了不起的妈妈》播出后,丈夫主动承担起监督Sasa练琴和二胡的任务。不像秀玮紧紧盯着五线谱,纠正Sasa的错音,大部分时间他只是坐在女儿身边打游戏。没有了高压的环境,Sasa练琴的效果似乎更好了,比之前有了更大的进步。秀玮也终于能在一天中有短暂的可以喘息的时刻。
事实上,秀玮也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周末在家开钢琴补习班,从早上8点45分开始到晚上9点半才结束,收入是全职工作的四倍。现在她与拍档有七十多位学生,每个学生每月学费两百多新加坡元。这项收入占了全家收入的大头,然而Sasa的教育支出也同样高昂,每个月达到两千多新元。
塑造“鸡娃妈妈”接受采访的三个家庭中,妈妈们并没有经过与伴侣协商的过程,自然地承担了更重的教养责任。正如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两位学者金一虹、杨笛的实证研究,教育大多由母亲承担,父亲并不是全然不参与,但都是间断性、“一时兴起”式的。这背后是在全球兴起的竞争型教育和家长主义。巴斯大学教育系教授劳德(Hugh Lauder)等人提出,肇始于1970年代的全球性社会转型让世界各国均处于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恐慌中,而因教育效能降低而丧失竞争力的危险最为突出。家长主义的逻辑则是家庭要为教育的失败负责,性别化的家长主义则是母亲应为家庭教育的成败负责。
在东亚,日本是“教育妈妈”概念的发源地。“教育妈妈”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以教育子女为“职业”,而这一群体在日本十分庞大。一些研究显示,东亚的母职和子女的学业实则已经捆绑为一体,母亲的核心劳动不再是照顾子女的生理性发展,而是高度介入教育,并不断将自身的母职实践与媒体话语中的理想母亲形象、专家育儿信息等相互比照。
妈妈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焦虑的?阿胖原本坚信“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直到小田要上幼儿园,阿胖考察了家门口的一家公立幼儿园,她原本很满意,后来慢慢被朋友科普,开始对比公立园和私立园的区别,就被推上了鸡娃的不归路。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梦在研究中指出,在中产阶层的精细化育儿趋势下,家庭对理想母亲的期待逐渐超越传统性别分工所指向的体力密集照顾责任,对母亲的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提出更高要求。
纪录片拍摄完成后,团队成员意识到,每一位妈妈都穿越了无数的困难,她们对子女的爱是十分确定的东西,却无时无刻不被严苛地审视着。即使是全网零差评的李琦,依然有观众在弹幕中写道:“这位妈妈再管理一下身材就好了。”李琦告诉姜又兮:“我确实应该锻炼,接受大家的意见。”姜又兮十分理解她的处境,生活中多重任务已经将她压榨到了极致,她在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付出到了极限,实在挤不出时间去做形象管理。
“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中年女性,你看她好像挺从容的,其实她也很焦虑的。但她要去克制自己,要去穿越这些困难,背后她们的那些连滚带爬、狼狈不堪,我们可能是看不到。大家会觉得爸爸总是风轻云淡,是因为那些实打实的任务没有在他身上。”姜又兮说。
但每位母亲心中不免都有一个虚幻的理想。阿胖心中理想的母亲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能平衡好个人兴趣爱好、家庭和工作,又能把小朋友教育得很好,小朋友又非常听她的话。”阿胖的微信朋友圈中就有一位这样的完美母亲,这让她压力巨大。
这种来自完美妈妈的比较压力,或许印证了发达的社交媒体是“鸡娃妈妈”现象形成的原因之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一书中指出,女性受到社交媒体的伤害可能比男性深,她们更容易受到社会比较的负面影响(美颜技术尤其)。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美]格雷格·卢金诺夫/[美]乔纳森·海特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
不过,纪录片中的三位妈妈,最终还是和现实握手言和。
阿胖最终放弃了让小田转入更好的学校。她发现即使在菜小,老师们也很优秀,他们在教学上有很多独到的方法,也许让小田一直骄傲地、快乐地过完六年更为重要。
李琦没有让小帅去报名人大附中早培班考试,“这是在挑神仙,我们是凡人,我们就不要去和神仙竞争了”。
秀玮则觉得,女儿读邻里学校也没什么不好。她常常提起的例子是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的故事,这位在2022年4月被确定为下一任新加坡总理的官员,当年分流时也是入读邻里中学,后来从初级学院毕业后,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