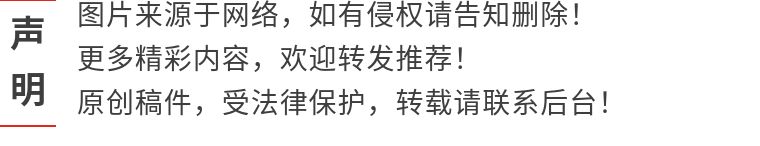文 | 周元
编辑 | 美龄
12月9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APP名单的通报,下架的APP多达106款,豆瓣APP也在其中。当天,豆瓣下架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迅速获得3.5亿阅读。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关于豆瓣被下架的具体原因是高频次索取权限、非法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而不是之前人们一直诟病的“平台治理不力”“内容不合规”等问题。

当天晚间,豆瓣官方回复了这次下架所涉及到的问题:

豆瓣表示,将认真进行整改,对各安卓版本进行严格测试,并将整改后的版本提交至相关机构进行审核,确保后续版本不再存在此问题。
今年是豆瓣成立以来,受到处罚频率最高的一年。从1月到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豆瓣网实施20次处置处罚,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罚款,累计罚款900万元。

过去大家对豆瓣的印象是“文艺青年的精神角落”,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觉得这个精神角落已经变味。让人不禁感慨,曾经高口碑的文艺青年聚集地,为何走到了如今这一步。
在2007年,豆瓣的用户就达到了100万。截至2019年年底,豆瓣的注册用户超2亿,月活跃用户超4亿。不过,这些年豆瓣也是争议不断。
融资早已停滞,上市遥遥无期,新品接连扑街,这些年来,围绕豆瓣的声音多是恨其不争的旋律。豆瓣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想来并不是盈利以及开源节流的问题,而是整顿、清朗、反思。

下一步计划如何走,还无人知晓,豆瓣创始人阿北(原名杨勃)也并没有给出准确的回答。以他此前数次身处漩涡中心依然淡定的先例来看,这次他依旧平和。
阿北曾经说,“当方向明确后,所有问题会慢慢在时间里有解。”我们想知道的是,未来,掌舵人阿北将带领豆瓣走向何方?

阿北从小到大都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作为货真价实的学霸,他16岁就摘得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金牌,直接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20岁,他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读博士,毕业后进入IBM 担任顾问科学家。

博士毕业后,阿北进入硅谷IBM的研发团队工作,从事下一代磁记录设备的计算模型工作,纯粹的技术工作。他决定辞职回国,而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这个工作太稳定了,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像得到几十年后自己的职务、薪资福利。”
回国后,阿北并没有想好自己能做什么,他本来想加入一家互联网公司,最后在清华大学同学翟学魂的说服下,加入了供应链管理公司快步易捷,出任CTO。

4年后,阿北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选择辞职去创业。最初,阿北想做一个自助旅游的网站,名字都取好了:“驴宗”。页面刚做了一半,他发现这个计划太小众,这么边缘化的网站很难聚集人气,遂作罢。
阿北很快又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他要为和他一样热爱阅读、音乐和电影的人提供可以分享交流感受的平台。“假如有这么一个网站,里面有和我差不多的人,我们可以相互交流,知道现在什么是比较好的东西,并且能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感觉,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网站。”

2004年12月,阿北总喜欢待在朝阳门外豆瓣胡同的星巴克里写代码。他抱着一台脱了漆的苹果笔记本,埋头编程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阿北喜欢在咖啡馆里工作,店员们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每次他来就直接上一个中杯的今日咖啡就好。在他看来,“咖啡馆不错,可以抬头看各色人等。有时候还能听到邻桌八卦。有一次还碰到过说英语的国际骗子。”
2005年3月6日,豆瓣正式上线,取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源于它最初诞生的地方——豆瓣胡同。他自豪地说:“豆瓣是草根的感觉,而且没有两颗豆瓣是一样的,就像我们,那么与众不同。”

豆瓣网由阿北一个人开发、运营,是集合书评、影评、乐评的网站,口号被确立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阿北对豆瓣网的定位,是“帮助你发现喜欢的东西”。而且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做豆瓣网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它对我是一个机会,我喜欢它就能够一直做下去。”

豆瓣创立的那些年,世界互联网科技浪潮风起云涌。国际上,有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埃文·威廉姆斯推出Twitter,华人陈士骏的Youtube上线……国内则有百度赴美上市,刘强东转型电商,马化腾收购张小龙的Foxmail……

几年以后,席卷中国互联网的人人网、微博、土豆优酷等应用上,几乎都可以找到海外版的前身。而豆瓣则是中国第一批完全原创的互联网公司,对于创业的回顾,阿北曾经表达过:“别人做过、做得成熟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会做。”
在这样的浪潮之下,阿北依然是不徐不疾的,并没有太多的流量焦虑。当时的豆瓣网站上“关于豆瓣”那一栏写道:“口味最类似的人却往往是陌路”。
在阿北看来,他希望“豆瓣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群,力图包纳百味。无论高矮胖瘦,白雪巴人,豆瓣帮助你通过你喜爱的东西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通过他们找到更多的好东西。”这些文字,16年来从未变过。

阿北的光杆司令一直当到豆瓣上线快一周年,他才迎来了第一位员工——洪强宁,后来洪强宁成为了豆瓣的首席架构师。
此后,在阿北的引领下,豆瓣的人气成为了“乌托邦”和“唯一的精神角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此,豆瓣甚至成为了文艺青年的新标签,勉力为用户提供心灵栖息地。
2007 年,用户量达到了 100 万,豆瓣从最初的豆瓣音乐、豆瓣图书、豆瓣电影扩展到社区的泛兴趣,新增了“小组”“同城”等功能。虽然后者与豆瓣此前的用户群体并不重合,但书影音依然能与小组和平共存,让文艺青年和吃瓜群众都共同留存在了这里。

很多小组的名称很抖机灵,比如“你想不想早上有很多人叫你起床”小组、“鄙视公共场所听歌不戴耳机”小组、“胖子都有颗敏感的心”小组、“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小组、“我们爱讲冷笑话”小组……而这似乎也是微博话题最初的雏形。

无论是豆瓣还是阿北,其实都错失了很多机会,比如豆瓣的“我爱化妆品”“这件衣服好看吗”等种草和分享小组,完全有机会做成小红书;而下厨房APP就是由豆瓣的“下厨房”小组孵化的,创始人还是豆瓣的前员工王旭升……

再比如豆瓣电影“中道崩殂”的商业化,豆瓣二三十人的团队把“猫眼踩在脚下”,形势一片大好之下,阿北迅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给的理由是:卖电影票不赚钱。2019年2月4日,猫眼在港交所开启了上市之旅。
在进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路上,豆瓣起初想做产品矩阵,把每个产品都做成一个独立APP,原本网页上的各个独立功能都被独立拆出,最后却受制于精力分散,顾此失彼,难以聚焦发力,甚至将原本聚拢在一起的用户割裂开来。
直到2014年,豆瓣才上线汇集了小组、书影、阅读等功能的综合型APP“豆瓣”。在这样“起大早赶晚集”的商业窘境之下,豆瓣只能眼睁睁看着网易云音乐、猫眼、陌陌等后来者一点点蚕食掉自己的领地。

压力之下,阿北也不得不在2014年的年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决策让豆瓣错失3年移动浪潮的最好时机。
丧失这一战略先机后,豆瓣逐步在凶猛的移动互联网大潮中迷失方向。此后的多次调整和改变,也都差强人意。当豆瓣已经不再只是那个文青们的精神角落和自留地,它注定要接受更多考验。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豆瓣的价值观是什么?阿北自己的回答是:“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至上。”最常规的流量变现自然就是广告,阿北并不抗拒商业,但他执着于以优雅的路径来实现。

豆瓣制定的广告规则是:每天的开屏只开放1/4的流量给广告,而广告如果不符合“足够的调性”,豆瓣会宁愿选择不接也不会上线。至于调性,其实就是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
阿北对于产品策略的坚持理性又固执,有时也不被用户理解,在豆瓣上被用户“骂”过许多回。用户还专门成立了“反对阿北独裁”小组,其中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歇过,但骂归骂,骂完他们继续在豆瓣里点标记、发动态、看影评、逛小组。
在商业化方面,豆瓣慎之又慎,成立至今只融过4轮资,至今没有上市,也没有好的营利模式。曾有人问阿北,不去涉足热门的盈利模式领域,是不是怕落入庸俗而损豆瓣的形象定位?他回答说:“盈利一点也不庸俗,只有庸俗是庸俗的。”

曾经,找不到好的盈利方式是豆瓣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而现在,内容审核之痛开始更多地困扰阿北,作为内容社区,豆瓣广播功能被迫下线整改,小组因“清朗行动”被不断整顿。
如今,阿北和豆瓣都到了不得不更彻底地改变的时候。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希望豆瓣能有更好的发展。因为,豆瓣没有改变世界,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