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初叶的江西于都,一个名叫丁盛的少年,因不甘于平凡的农耕生活,16岁时毅然选择了当地最危险的职业——排客。站在木排之上,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迈,犹如将军般在波涛中穿行。然而,命运的齿轮总是出人意料,当他因年龄太小被迫离开排客行业时,一支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队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7岁的丁盛带着六个玩伴参军入伍,从此开启了一段传奇般的军旅生涯。令人唏嘘的是,与他一同参军的六个玩伴全部壮烈牺牲,而他却在命运的眷顾下活了下来,并在此后的岁月里真正成为了一名将军。

赣江岸边少年郎 贫苦家中见天日

江西于都罗江乡上溪村上水排村,座落在一片凸起的山冈之上。这里青山环绕,溪流潺潺,不远处的百里小溪在大拐弯处汇入贡江,形成了赣江的发源支流。

村庄紧邻赣江水系,六百里赣江从武夷山脉西麓的石城石寮岽发源,一路奔流向南。水流经瑞金、会昌等地,汇众山之水,在赣州与章江交汇,随后北上注入鄱阳湖,最终汇入长江。

丁盛出生在这个依水而生的村落,在五兄弟中排行最小。按照当地的风俗,爷爷偏爱长子,父母则格外疼爱幺儿,这使得丁盛在贫困的家庭中得到了特殊的关照。

每到寒冬腊月,一家人都靠着地瓜果腹,唯独母亲会给丁盛蒸上一碗白米饭。丁盛的母亲是村里有名的手艺人,精通制作果脯和年果,常被邻里请去帮忙。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水果是稀罕物,母亲帮工得到的果子,总会留给丁盛享用。这样的生活待遇让丁盛的发育比同龄人更好,身材也长得较为高大。

村里的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稳,丁盛与小伙伴们经常在两江汇合处的洲滩上放牛。洲滩草地绿油油一片,油菜花开得热烈张扬,孩子们在这片天地里自由玩耍。

不同于其他农家子弟,丁盛对农活并不感冒。田间地头的劳作,他总是能推就推,怕雨怕风,更害怕打雷,这让他在村里落下了"好吃懒做"的名声。

日复一日的放牛生活中,丁盛常常被江面上往来的木排吸引。整条赣江上,木排如长龙般延绵数里,排客们赤裸着上身,吆喝着号子,在波涛中搏击前行。

这样的生活在村民眼中充满了危险,当地有着"有一升米吃,也不去放排"的说法。可对于厌倦了平淡生活的丁盛来说,这恰恰是他向往的人生。

这个时期的丁盛,虽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却因为母亲的偏爱而得到了不一样的成长环境。正是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排客行当险且艰 少年意气犯潮头
上世纪初叶的赣江,是一条繁忙的水上运输大动脉。那时陆路交通尚未发达,赣州直到世纪末才修通铁路,水运成为最主要的商贸通道。

江面上漂浮的木排,用竹篾绳扎成,能连接成数里长的巨龙。排上设有绞车,排首前方配备一只"毛船"负责导航,船上的掌扇与绞车之间用百余米长的竹篾绳相连。

每到南方的梅雨季节,雨水增多,河水上涨。四月到六月间,水流湍急,正是运送竹木的黄金时节。这时的木排顺流而下,在江面上掀起千堆雪浪。

排客们要在排头挥舞着装有铁钉钩的竹篙,或是操控着木制大舵。几个副手配合默契,在险滩急流中搏击前行,躲避着暗藏的礁石和陡峭的崖壁。

十六岁的丁盛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去当一名排客。他的身材优势让他很快得到了机会,跟着老排客开始了学徒生涯。

排客的生活异常辛苦,下暴雨时别人往家跑,他们却要往外赶。夏日烈日炎炎,寒冬刺骨严寒,排客们都得在江上坚持。

水浅的冬季,木排只能停在沙滩上等待春汛,这种情况被称作"旱排"。丁盛和其他排客一样,在江边的简易棚子里过冬,等待开春后重新扬帆。

但年轻的丁盛并不畏惧这些困难,他像模像样地学着前辈们的样子,在波涛中穿梭。站在排头的位置,俯视着奔腾的江水,让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豪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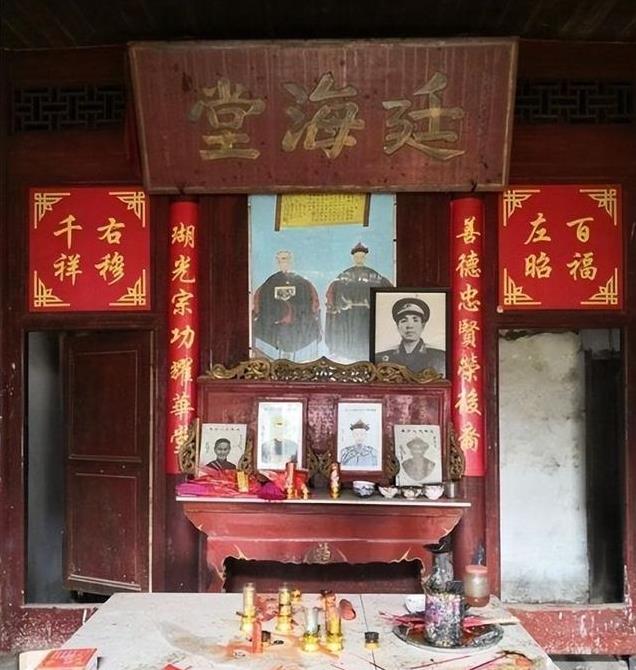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年龄太小,老排客们担心他的安全。一次险些翻排的意外后,丁盛被迫离开了这个充满危险的行当。

在离开排客行当后,丁盛常常站在岸边,看着那些如长龙般的木排驶过。江面上的号子声、竹篙击水声,依然让他热血沸腾。
对于当时的丁盛来说,排客生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冒险。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人生的道路或许不该局限在一亩三分地上。

井冈山下红旗展 少年从军踏征程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井冈山下的红军部队开进了于都县。红色的旗帜在赣江岸边招展,宣传队的鼓声和号子声传遍了罗江乡的每个角落。
红军战士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脚上缠着白布条,但精神抖擞。他们走村串户,向群众讲述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请乡亲们吃大锅饭。
这支队伍的到来,在上水排村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议论,有人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有人说参军能学文化,还有人说能走出大山见世面。

丁盛刚满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失去排客工作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在村里闲逛。看到红军战士们昂首挺胸的样子,让他想起了站在排头的感觉。
一天傍晚,丁盛召集了六个要好的玩伴,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商量参军的事。这些年轻人都是放牛时的伙伴,从小就一起在江边玩耍。
第二天天没亮,七个人就偷偷溜出了村子。他们担心家里人阻拦,连夜赶到了红军驻地。一群毛头小子,站在招兵的队伍里,个个都挺直了腰杆。
红军干部问他们的年龄,七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满十八了。其实除了丁盛,其他人都只有十五六岁,但红军看他们身强力壮,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消息很快传回了村里,丁盛的母亲赶到红军驻地,哭着要把儿子带回家。她说家里就这一个小儿子,不能让他去当兵送死。
但丁盛态度坚决,他对母亲说:"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村里,当排客都不让我干,现在有机会参军报国,您就让我去吧。"母亲最终含泪答应了。
入伍第一天,七个人就被分到了不同的连队。临别时,他们在营地里抱头痛哭,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互相照应。
新兵训练异常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练操,白天还要学习识字和军事知识。丁盛因为身材高大,被选为队列训练的标兵。
在训练场上,丁盛像当年站在排头一样挺直腰板。教官说他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看样子将来能当个好班长。

丁盛和六个玩伴踏上了从军之路。他们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命运的转折点就此开启。
岁月长河浪淘沙 六友埋骨为苍生
一九二八年春,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丁盛所在的部队辗转于赣南、闽西地区,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丁盛不断打听六个玩伴的消息。他们分散在不同的部队,有时能在战场上偶遇,有时能通过其他战友传递只言片语。
第一个噩耗传来时,是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最小的玩伴在一次突击中中弹牺牲,年仅十六岁。战友们将他葬在了山坡上,用乱石堆砌成坟。
长征开始后,丁盛失去了与其他玩伴的联系。红军主力北上,有的部队断后,有的部队分散游击,沿途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过草地时,又一个玩伴倒下了。他因为体力不支掉队,被沼泽吞没。连尸首都找不到,只留下一顶染血的军帽。
到达陕北后,丁盛打听到第三个和第四个玩伴的消息。他们在突破湘江时壮烈牺牲,与数千名红军战士一起长眠于湘江之畔。
抗日战争爆发,remaining两个玩伴分别在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其中一个临终前还在询问其他几个伙伴的下落。
十年后,丁盛带领部队重返故地。站在当年的榕树下,曾经约定要常来常往的七个少年,如今只剩下他一人。
江西于都县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革命先烈的名字。丁盛在碑前驻足良久,找到了六个玩伴的名字。
那些年,赣江依旧奔流不息,木排依旧往来如织。丁盛已经是一位将军,但他时常想起当年在排头指挥的情景。
命运的齿轮总是出人意料,当年七个并肩参军的农家少年,竟只有他一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六个玩伴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战歌。
岁月匆匆,丁盛白发苍苍,但他始终记得那个冬天。七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在榕树下立下誓言,要为理想奋斗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