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黄昏,肯特郡坎特伯雷火车站。
列车将开往伦敦,我和福尔摩斯面对面端坐着,小桌上摆着两杯热茶。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啜着茶,翻着报纸,”明天肯特郡谋杀案将会见报。“
“你又要名扬欧洲了,但你在探案时也离不开我。”我得意地拿起了茶杯。
“那是当然,因为你的错误判断总能启发我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白了他一眼,看向窗外,“大波波娃还一个人在伦敦呢。”
“你急着见到她?”
“90公里,1小时10分钟,感觉有些慢了。”
“如果是中国高铁,我们20分钟就能到伦敦。”
“你是说中国高铁时速能跑300公里?”
“并不止300公里,中国的发展就像它的高铁一样快。”
“歇洛克,你看到的可能是假象,《经济学人》说北京经常有数百名流浪汉睡在市中心。”
福尔摩斯放下了茶杯,“它们亲眼看到了?”
“是的,除了《经济学人》,BBC等媒体也拍到了。”我向他展示了照片。

福尔摩斯叹了口气,“看起来好惨,他们甚至连帐篷都没有。”
“就在天安门附近,凌晨三四点,夏天经常有这种情况。”
“华生,这样的话,北京全城可远不止数百名流浪汉吧。”
“谁说不是呢,美国人凯乐看了《经济学人》报道,他就持怀疑态度。他居住的波特兰市有数千名流浪汉,而波特兰只有100万人口,所以,2000万人口的北京,怎么可能只有数百名流浪汉?”
“美国式的分析不无道理。”
“于是,按照《经济学人》报道的内容,7月份,凯乐在网上宣布自己飞往北京,寻找更多的流浪汉,网友在X上等待他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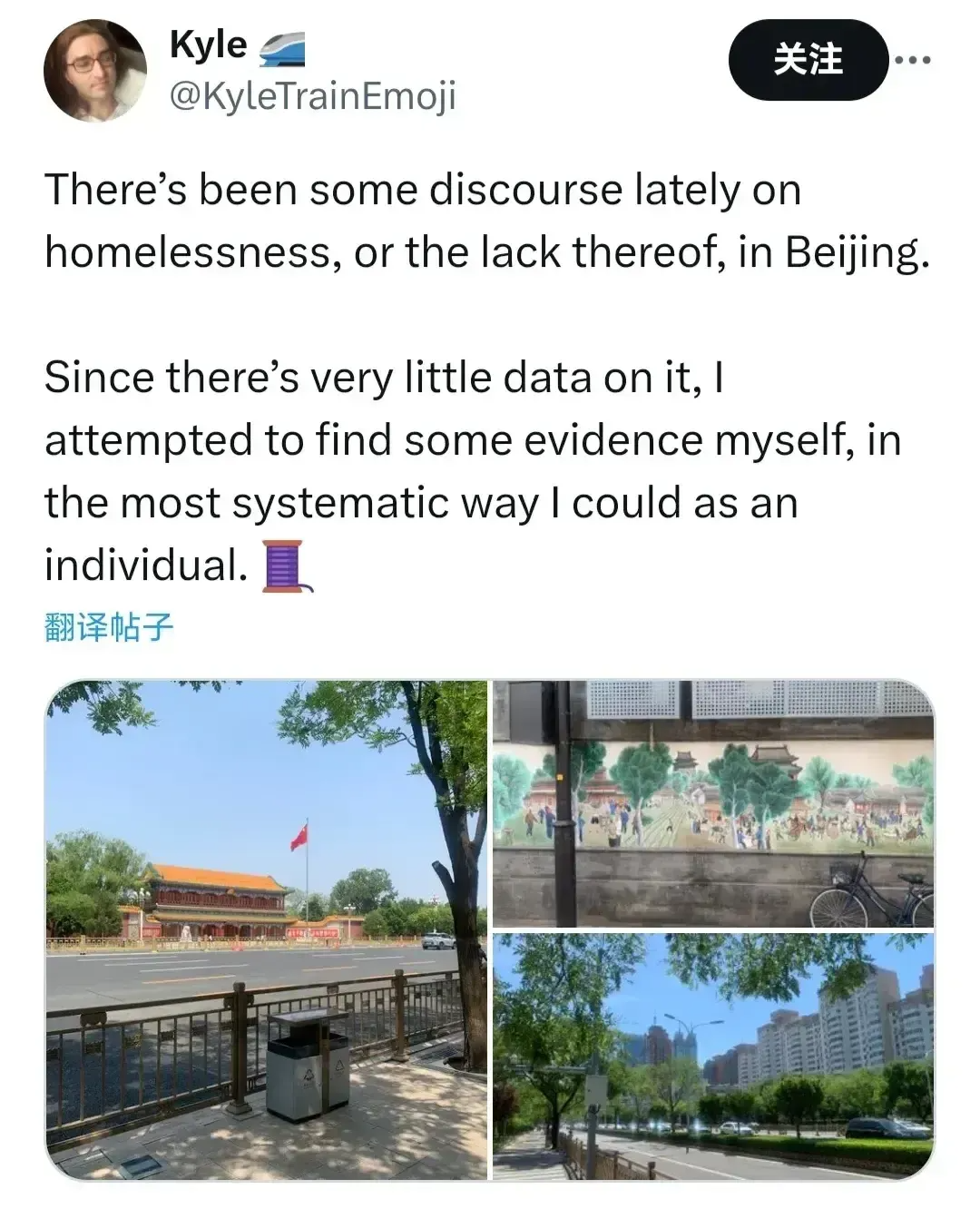
“华生,他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吗?”
“呃……怎么说呢,结果确实很惊人。”
“找到了流浪大军?”
“并没有,他说自己什么都没有找到,他甚至根据美国经验到了人行隧道里面,但隧道里不仅没有流浪汉,还格外干净,他说自己有些感动。”

“华生,他没有去北京的胡同里看看?”
“是的,凯乐去了胡同,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睡觉的空隙和角落,但一无所获。”
“那他应当去四合院找找。”福尔摩斯阴险地笑着。
“没错,他来中国之前,听人说那里是北京的贫民窟,有很多穷人,但还是一无所获。”
“北京四合院,贫民窟?中国人没有把他当成傻子吧?”
我拿起了茶杯,“一周后,凯乐回到了美国,他发文说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在北京找不到任何流浪汉。即便有,也不可能是《经济学人》声称的数百人那么多。”
“华生,但《经济学人》、BBC它们拍到的流浪汉又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这令我非常困惑。在凯乐的评论区里,去过中国的网友都认为凯乐看到的是真实的中国,而不是BBC报道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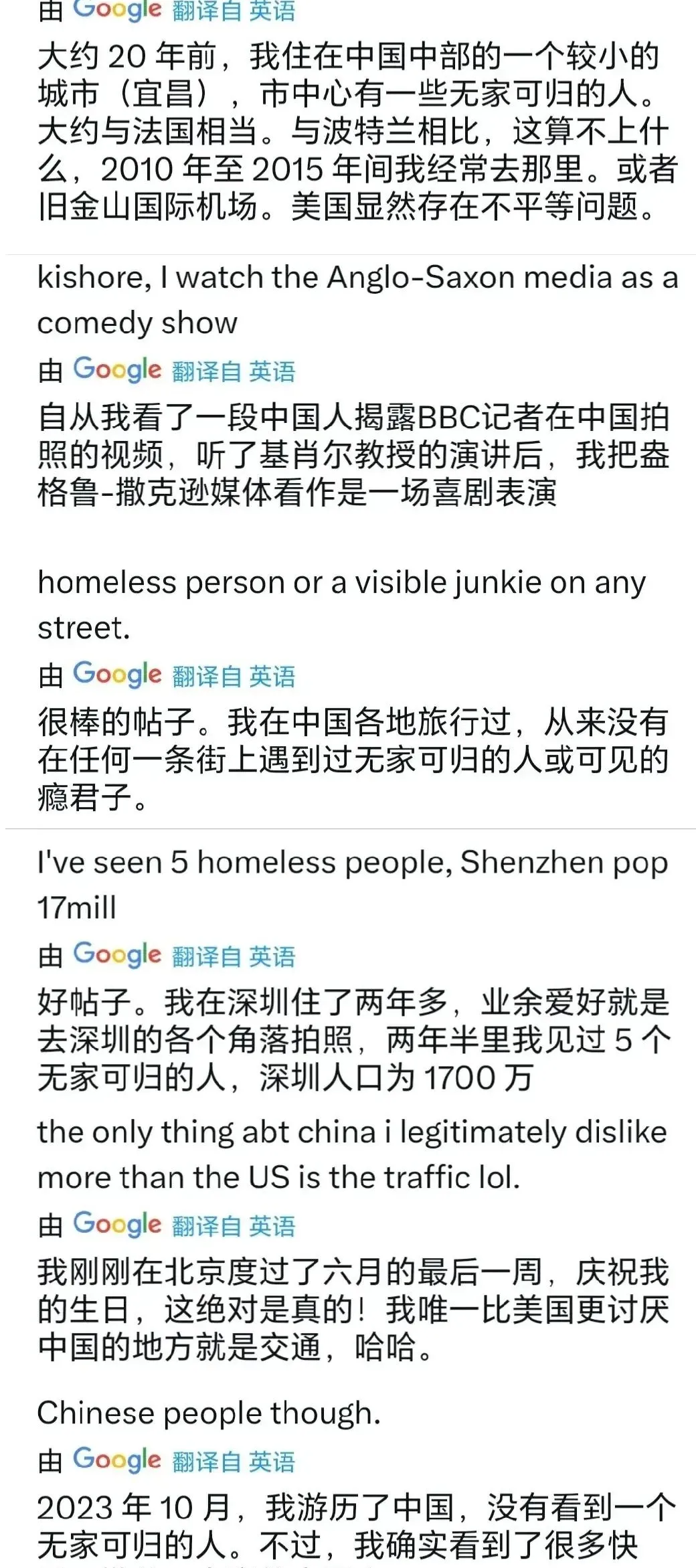
“华生,那么你怎么看我们主流媒体报道与网友所见的反差?”
“或许,中国将流浪汉藏了起来?有些中文账号是这么评论的。”
“那些中文账号不必理会,它们是流落在外的反华分子,最见不得中国人过得好。我是说,你怎么看?”

“我也糊涂了,我见过的流浪汉聚集地,边上往往会有毒品、针头、脏东西,还有僵尸一样的表情,但这些中国人整洁、干净、放松……难道,这里在拍电影?”
福尔摩斯向服务员叫了两杯咖啡,“华生,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在参加一种仪式。”
“仪式,宗教的?”
“不,比宗教更神圣,更实际。”
我接过送来的咖啡,“你知道?”
“这是为了天安门的升国旗仪式。”
“啊”,我的咖啡抖了一下,“那为什么不等天亮?”
“天亮?天亮还有好位置吗?如果你到了北京,想在人山人海中占个有利位置,你就得在凌晨准备睡马路。”
“宁可离开宾馆?”“看完升旗仪式再回宾馆,可以睡得更香。”
“游客有宾馆不睡……”我摇了摇头。
“起来后还得百米冲刺,就为升旗那一刻。”福尔摩斯喝完了咖啡。
“我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 歇洛克,但《经济学人》、BBC它们难道也不懂这些所谓的流浪汉吗?”
“它们对中国的歪曲是系统性的,也是一种任务,与懂不懂无关。”
“我觉得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仪式,比如在海德公园升国旗,我会去睡大街。”
“海德公园?”福尔摩斯冷笑了一下,“昨天有几千人在那里要求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又要入欧,又要公投?”
“是的,这叫强大的纠错能力,体制的优越性。”
“那三年后,另一帮人又要脱欧,又要公投?”
“那说明我们体制更加优越,纠错能力更强”。
“歇洛克,我觉得很悲哀,这种事怎么能推给民众决定呢?”
“到伦敦还要半个小时。”福尔摩斯看了下表。
“这该死的火车。”我有些急躁。
“喝你的咖啡吧,火车慢有慢的好处。”
“哦?”
“如果提早到家,你和大波波娃可能都会被对方吓到。”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感觉怪怪的,“歇洛克,我们将被中国甩在身后,《经济学人》、BBC这样报道中国,可能是为了让心里好受些。”
“如果北京不下雨,临近国庆,它们还将看到北京流浪汉将睡满大街,还得预约。”福尔摩斯大笑起来。
“其实,中国人到北京参加升旗仪式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这就是中国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生生不息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