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前言苏轼作为词人的影响当然很大,但还原他当时的创作场景却并非易事,因为,尽管后世关于他的词评汗牛充栋。
 新的词评观念
新的词评观念在当时,他的同辈人中却很少有人对此发表议论,黄庭坚关于他的一首黄州词的跋文是少有的几篇文献之一。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上阕中,孤鸿与幽人彼此相“见”,是暗夜中唯一的醒者,下阕的关注点则完全转向孤鸿,它感到“恨”,感到孤寒畏缩,“拣尽寒枝”却找不到栖息之所,正如流放中沮挫的苏轼。

黄庭坚的盛赞,不仅停留在写作技巧和表达能力方面,他对这首词的评价之高,绝不亚于他对某首高妙的苏诗(甚至是杜诗)的评价,他丝毫不因为这是首词而感到遗憾。

参考资料
不只是《卜算子》,苏轼有许多其他的词,也是一样被毫无保留地推崇,除了用韵和音律上的差别,这首词读起来也的确像诗,无论是词旨,用语,或是笔调,它都和传统的词不同。
在黄庭坚看来,它不仅是东坡高妙写作技巧的证明,也是他的内心写照和内在人格的外在呈现。

我们从《卜算子》里读出了他的博学,他的脱俗,还有他非凡的文学表现力:他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流寓黄州的苦闷之情,而不是直截了当。

通常情况下,词是“不如其人”的,词只为公共表演而作,为配合歌伎的演唱而作,词与作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疏离,它可以和作者没有关系。
因此,词评往往会将作品与作者分而论之,毕竟词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大众而生、为“俗”而生的。

但是,这篇跋文中黄庭坚却说东坡词是“语意”自“胸中”出,作品语意高妙,皆因作者其人无一点尘俗气,词在黄庭坚这里得到了彻底的翻案和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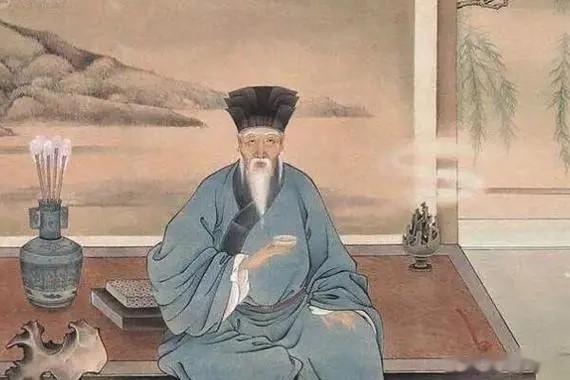
诚然,黄庭坚只是针对苏轼的一首特定的词作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事实上,不在11世纪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词都在挣扎着,力图获得合法地位。
特别是当花间词传统被打破后,词应当何去何从,成为困扰许多词人的一大难题,如果将黄庭坚这番赞许放在上述背景中看,就不难得知苏轼作为词人的努力和他探索的分量。

那绝非无足轻重,要想在某个新的审美领域中开疆拓土,一个发起范例的人有多么重要,对于宋词而言,这种开拓就更加艰难。
 苏轼在词之中的地位
苏轼在词之中的地位北宋词史在时间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源”,却有一条不断的“流”,一个又一个词人在这一进程中留下印记。

苏轼算不上他们中的前辈,但却是第一个写出了在品味和分寸上都完全合理、合度的作品的词人。
词到苏轼,才真正被接受了,黄庭坚的跋便代表了时人对苏轼在这一文体上的探索的高度评价。

苏轼的努力证明,的确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词的“不体面”这一痼疾,如果这种努力来自一个无名小辈,那可能无关紧要。
但是苏轼一旦开始努力探索、大量作词,并且是以一种无可指摘的方式,那词的“翻身”便指日可待了。

参考资料
苏轼冒着葬送名誉的危险涉入了这一领域(因为写词,柳永的名誉完全葬送,欧阳修也几乎葬送),并开创出一个新纪元。

这是词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是由一位少年得志、驰誉文坛的天才完成的,一位因政治迫害和流放而成为士人偶像的英雄,苏轼的介入,对词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在许多资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苏词和柳词异同的品评比较:
子瞻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东坡为之绝倒

这里所说的“大江东去”则是苏轼最著名的词作之一,是他词风最典型的代表,因此这条材料历来很受重视。
 苏轼词的风格
苏轼词的风格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柳词和苏词的对比:一婉约,一豪放;前者专于“情”,意象精致,婉转细腻;后者品评王朝兴衰、沙场征伐,雄健磅礴。

苏轼的风格显然被认为胜过了柳永,因为他将柳词擅长的那种缠绵阴柔的气息一扫而空,首先,苏轼自己也写过与豪放词截然不同的阴柔婉约的作品,明人王世贞就曾含蓄地指出这一点:
“昔人谓铜将军铁绰板,唱苏学士大江东去…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

但与此同时,苏轼“至咏杨花《水龙吟慢》,又进柳妙处一尘矣”。王世贞的意思是,苏轼两种风调兼长,并非只会一味豪放。

他提到的“杨花”,通常与美人娇眼(或睫毛)并提,苏轼详尽地描写了杨花随风飘逝、落地成泥的景象,在繁复的比喻中唤起思妇离人的孤寂之情。
伤春惜时,感叹红颜难驻,青春蹉跎,这首《水龙吟》同是苏词名作,被王国维判为咏物词之“最工”者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苏轼的确豪放,但也可以阴柔。

再者,苏轼不仅自己写这些他本不该写的作品,而且偶尔还会对别人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第三,苏轼的豪放词一方面广受追捧,但另一方面,对豪放词的质疑也从未停止,在词风和词旨上“指出向上一路”毕竟会削弱词阴柔和娱情的本色,而当初吸引士大夫写词的恰恰是这一点。
苏轼的同代人纷纷就此发表议论,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心意思却一致:苏轼对词的改造使词偏离了言情传统。

有人说苏轼的词不能唱,有人说他的词“短于情”,还有的说他“非本色”,比如陈师道就曾是“以诗为词”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陈师道的意思是,雷大使舞剑宫廷其实不合常规,通常情况下宫中舞者都是女性,目的是娱帝王耳目。

除了上述明确的批评,时人对苏轼改革词风词旨的抵制态度,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一个被广泛援引的事实便是:苏轼自己的门生,如秦观、晁补之、陈师道和黄庭坚,都不曾在这方面追随他,也就是说,即便是和苏轼关系最密切的人,也不愿意学他的词风。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豪放、婉约并存——苏轼词作反映的宋代词风》马列。
【2】中国知网——《论苏轼词的创作风格及其影响》陈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