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是弘一法师跨越红尘与佛门的一叶扁舟,承载了他从风流才子到律宗高僧的悲欣人生。从天津茶庄的少东家,到西湖茶馆的文人雅士,再到福建佛寺的苦行僧,茶始终是他心灵的伴侣与修行的媒介。一盏清茶里,既有俗世的热烈,也有佛门的清凉。
一、茶香浸润的少年时光:津沽茶缘1880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粮店后街的盐商世家,母亲俞氏来自经营茶庄的芥园俞家。自幼饮用的西湖龙井,按时由俞家茶庄供应,茶香浸润了他早年的生活。家中茶具陈列青花盖碗、紫砂壶,少年李叔同常手书元稹的宝塔诗《茶》,将茶与诗画相融。十七岁奉父母命迎娶茶商之女俞氏,虽婚姻终成遗憾,却让他与茶结下更深羁绊。在天津名士赵元礼门下学诗时,师生常“促膝品茶论文”,茶成为他感知传统文化的启蒙。
1902年,他首次赴杭州乡试,常在涌金门外茶馆凭栏远眺西湖,茶烟与湖光交织,种下对江南的眷恋。这段经历如茶汤初沸,预示着他与西湖的宿命之约。
二、西湖茶烟中的红尘转身1912年,李叔同任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居所邻近西湖。他常独坐景春园茶馆二楼,或泛舟湖心亭品茗,将茶与艺术创作相融。某日与夏丏尊、姜丹书夜游西湖,特命童子“治茗具”,三人高谈阔论,留下《西湖夜游记》的茶香墨迹。正是在这样的茶叙中,夏丏尊一句“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戏言,成为他日后遁入空门的伏笔。
茶亦见证了他人生最戏剧性的转折。1915年冬,挚友许幻园因家道中落冒雪造访,临别时的一句“叔同兄,咱们后会有期”,让他在茶凉之际写下传世之作《送别》。这杯离别的茶,既终结了“天涯五友”的风流岁月,也催生了以教育救国的教师李叔同。
三、佛门茶事:从“执象”到“忘言”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剃度前夜,他将收藏的印章封存于西泠印社孤山鸿雪径,却唯独带着一只粗陶茶盏入寺。出家后,他常以茶待客,曾对弟子昙昕法师坦言:“若得饮雪峰茶,身心即入清静境。”在南安雪峰寺,他轻啜当地野茶后赞叹不已,却谨守“过午不食”戒律,克制饮茶欲望,展现修行者的自律。
晚年驻锡福建期间,茶成为他连接尘缘的纽带。他常与性愿法师互赠安溪铁观音、永春佛手茶,书信中写道:“承赐佳茗,至感。”在惠安净峰寺讲经时,他亲自汲水烹茶款待信众,将茶席化为传法的道场。茶于他,已非风雅之物,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禅意具象。

弘一法师的茶道,彰显着“平常心是道”的佛理。他用咸菜佐饭时说“咸有咸味”,饮白水时言“淡有淡味”,这种超然态度亦体现在茶事中。当世人追逐名器佳茗时,他坚持用粗陶碗饮野茶,认为“心不在茶上,纵饮甘露亦无味”。某次有人以紫砂名壶奉茶,他淡然道:“泥胎纵贵,不及清水映月。”
这种哲学亦凝结于西泠印社为他特制的纪念茶具:盖碗取形华严经塔,茶杯底钤“叔同”金印,包装题写“如梦如幻”“放下”禅语。器物之精美,反衬出他“喝茶莫为器所役”的教诲,恰如他晚年偈语“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的深意。
五、茶烟散尽:月圆茶凉的终章1942年秋,弘一法师预感大限将至,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写下绝笔“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临终前,他特意嘱托弟子:“灵前须上茶供。”这些茶叶,或许承载着他对红尘的最后眷恋——既是津沽少年的味觉记忆,也是西湖文人的风雅残梦,更是修行者穿透苦乐的禅悟。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茶始终是映照其生命境界的明镜:少年时,茶是诗画风流的点缀;中年时,茶是聚散离合的见证;晚年时,茶是悲欣交集的禅机。正如他留给世人的启示:真正的茶道不在茶叶贵贱、器皿精粗,而在饮者能否如月映清泉,照见本心。当我们在西湖畔品饮龙井时,杯中荡漾的不仅是茶汤,更是一个灵魂从绚烂归于平淡的生命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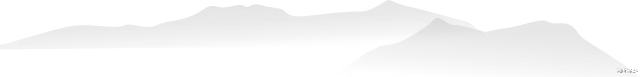
本文来源:图文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留言告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