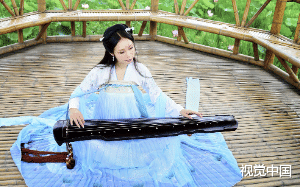第一章
我死了,我又活了。
我名吴念姝,是吴中八绝之一善卜风候的吴文则后人。奈何时局动荡,家道中落,自父亲成年后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我五岁时,祖父携一家老小迁往太原投靠外曾祖母崔氏一族。
自此,我与崔白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十六岁时便嫁与他为妻。然而,世事难料,青梅终究抵不过天降,我们无缘终老。
还清晰记得我死去的那夜天空飘着大雪,风寒彻骨,我只身一人穿着单薄的里衣拖着残破不堪的身躯,从京城望乡台上一跃而下。
温热的血四溅开,我却一点儿也感受不到疼,双眼定定望着天空飘落的雪,空洞、麻木、绝望……
转眼,记忆回到那晚,红烛烫夜天、光影幢幢,硕大的囍字贴在窗格上,醒目又喜气,这是我和夫君崔白的新婚夜。
他用玉如意挑开我的红盖头,深情地望着我,对我许下一生一世的诺言。
因为我俩自幼相识,我自是无比相信他的承诺。可叹造化弄人,我们终究还是离分。
清晨,亮光刺眼,我从混沌中醒来,眼前是熟悉又陌生的红帐,扭头看去,窗格上大红的囍字醒目惊心。
“我不是死了吗?”双手攥着鸳鸯喜被,我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切。
正在我愣神之际,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挺拔的身影端着铜盆走来,我看着向我走近的穿着靛蓝长衫器宇不凡的英俊男子一时怔住,“他怎么会在这里?”
许是我的表情太过讶然,男子将铜盆放在架上,走到床边坐下,牵过我的手握住,笑着问我:“娘子怎么了?”
我浑身一激灵,拿出自己被握住的手,朝床里缩了缩,试探地喊道:“崔白?”
看到我生疏地表现,他一下愣住,随即闷闷地说:“娘子,你该唤我夫君了!”
呃,夫君?好生疏的称呼,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唤过他了。此时竟有些说不出口,我俩一时无话。
我抱着头皱着眉看他,脑袋生疼,眼中充满探究,眼底透着哀伤。怎么回事?他不该在这里的……
崔白见我迟迟不语顿时慌了神,凑近揽过我的身子,着急地问:“娘子,你怎么了?”
他眼中的紧张不似作假,我喃喃开口:“我头疼。”
他一听立马将手贴上我的额头,然后说道:“是有些热!”随后又问道:“娘子除了头疼可还有哪里不舒服?”
这些寻常的关心话语在我听来恍若隔世,何况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但此刻,他眼里的担忧与自责我看得明明白白,一时间我心中不由泛起一阵悲痛,不知不觉眼里竟噙满了泪花,一眨眼,泪滴如掉线的珠子贴着脸庞砸下。
泪珠滴滴掉落砸在鸳鸯喜被上,浸湿一大片。
崔白见状慌乱地替我擦拭泪水,不停地问我“怎么了?”
我一把抱住他,将头埋在他的胸口,低声呜呜哭着,任泪水打湿他的衣衫。
不知哭了多久,我竟哭得昏睡过去。
睡梦中,无数的记忆向我砸来搅得我不得安宁。我脑袋里被填满了新颖又熟悉的记忆,我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只是一本书。我穿书而来,在书中的角色是男主的炮灰前妻。
男主是我的夫君崔白,女主则是京城才女柔嘉郡主柳婵依,我只是书中一笔提过的次要人物,竟然只存在于男女主某次的对话中。
可我拥有自小到大的所有经历,我有血有肉的活着直到死亡,我分明度过了极其可悲的一生。这难道只是世界完善剧情背景的一部分吗?
剧情的开始是在崔白进京后,他因为在途中遭遇劫匪失了所有盘缠以及和我失散,整个人萎靡不振。幸而遇到上山祈福的柔嘉郡主柳婵依,得她相助开解,他才度过难关顺利考取功名。
二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渐生情愫,但是碍于我的存在,崔白没有表露心意,柔嘉郡主尊重他,一等就是三年。圣上感念柔嘉郡主情深,特意赐婚,二人喜结良缘、终成眷属。
可对我来说,这不公平。与崔白失散后,我被定安候次子嘉平伯宋辞书救下,但他认为我和劫匪是一伙的,执意送我去官府。我的身份路引丢失,无法自证,只能跟随他辗转来到边关。
在去往边关的路上我一直向家中寄信,但无一回复。
等尘埃落定,我的身份明晰时,边关战事频发。一次偷袭战事中,我不幸被草原大将阿史那丹俘获,流落到草原,幸而我得祖传能卜风候被草原巫看中留得一命。
边关苦寒,草原部族勇猛,我在草原一待就是三年,直到宋辞书再次将我救出。
他戍边期满,回京述职时顺道将我带回。我在京城听闻夫君崔白已再娶,新夫人是宋辞书表妹柔嘉郡主柳婵依,二人乃皇帝赐婚,天赐良缘。
我深知自己无名也无力与郡主相争,只想上门见崔白一面,但或许三年前走散之时我们的缘分就尽了,最后一面早已见完。
宋辞书却在此时说钟意我,我在他后院得一良妾位,但终日不得踏出院中一步。我怀疑他为表妹柔嘉郡主软禁我,但我无所谓,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好,何况他待我不算差。
本以为余生就此苟活,不巧,几个月后皇帝指婚尚书府嫡女徐佳颜给宋辞书,二人婚期将近,我被定安候夫人撵到别院。岂料,他们婚期前一月我突发风寒,一病不起。我知道我是碍了有些人的眼,恐怕时日无多。
身体破败的我在他们婚期之日看守松懈之时,溜出别院登上望乡台,清唱一曲《离人泪》,终了后随着满天飘雪一齐落下。
这就是我颠肺流离、短暂凄惨的一生。
现在来告诉我,我的一生只是书里微不足道的一个故事背景,甚至未曾在故事主线中被提及,简直可笑!可笑至极!
如今,我在我与崔白新婚的第二日醒来,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梦,还是真的重来一回。
“娘子,娘子……”
舒润清朗的声音从我耳边传来将我唤醒,我睁眼望去是崔白在唤我,他手里正端着一碗药。
我起身坐好,他将药放在桌上眼神关切地看着我说:“娘子,现下可有舒服些?都是为夫不好,让你受累了!”
闻言我一愣,看向他,我怀疑他在开车但没有证据。
我对他点点头示意好些了,他又说:“刚才大夫来过,说你伤怀入骨,思绪不宁,娘子你有什么伤心事?可是为夫哪里做的不好?”
我心想“大夫医术不错,这都看得出来。可惜无解,令我忧思的事我恐怕无法说出口与人分享。否则只怕会叫人说成是疯魔或是得了癔症,我可不想再‘被病故’。”
因而开口和他说:“我只是做了个噩梦,被吓到了,没什么大事,你很好,不必介怀。”
说完,只见他幽怨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意识到我语气中的生疏忙改口:“夫君,如今你是我夫君了,我只是还有些不习惯,夫君不会怪我吧!”
他见我这样,瞬间展颜一笑如夏日荷花般灿然放晴,伸手刮了刮我的鼻梁,拥我入怀说道:“怎么会呢?娘子是这世上最好的娘子,我怎会怪你?”
听到这话我不争气地红了眼眶,还记得从边关回来知道他消息时我曾登门寻他,他没来见我,只是柳婵依出面将我赠他钗归还于我,留下余生再不相欠,再不相见的绝情话。
往事如风散去,我收敛心神不再去回忆,从他的怀里退出,笑着问:“夫君,刚刚端来的是什么药?”
崔白回答:“这是大夫给你开的舒肝解郁的药,一日两回。”
说罢他将药碗端来,用勺舀起吹了吹打算喂我。
我向来吃不得苦,怎么可能忍受这么一勺一勺地苦味折磨,立即把头偏向一边满脸拒绝。
他无奈哄着我说:“娘子乖,喝了药病才能好,你才会舒服。”
我不为所动,仍是一脸拒绝,他见状又说:“我准备了蜜饯,娘子喝了药再吃蜜饯就不苦了。”
我闻言伸手,示意他先把蜜饯交出来,他无奈将药碗递给我起身端来一碟蜜饯。
我满意地点点头,端起药碗咕嘟咕嘟将药一口喝了个干净,然后立刻塞了一块蜜饯含在嘴里。
他笑着看我的动作,将药碗收拾好又端来一盆温水,随后将我拦腰抱下床准备帮我梳洗。
真大可不必,我虽四肢乏力,却也不至于瘫痪到如此地步。我拨开他,自己洗漱一番,待收整好后问他:“母亲那边如何?”
我清楚今天一早本该去敬茶,然后听婆母王氏给我立规矩。想想我曾经是怎么做的?哦,我忍着身体的疲累早早地就到王氏跟前侍候敬茶,可王氏却将我晾了许久,直到我晕倒在她门前。
可如今我不仅大早上没起,还没去,不知王氏又会如何。
崔白沉思一刻,面露苦恼又很快收敛下去,安慰我说:“我今早已经和母亲说过了,她嘱咐我让你好好休息,别担心!”
我哪能真的信他说的话,自古婆媳间天然的就存在矛盾,王氏恐怕已经想好怎么磋磨我了。
崔白的母亲王氏是一个令人敬佩的铁娘子,自崔白的父亲离世后,她一个人撑起了一片天为崔白遮风挡雨。
我的母亲常常赞叹她,认她为好姐姐,我在她眼前长大,两家人算是知根知底,如今我成了她的儿媳更是应该亲近几分。我原也以为我们之间因着这些关系不会像别家婆媳一般难以磨合,谁能想到我至死也捂不热她的心。我在去往边关路上寄出的信,我不信她一封也没收到。我家也不知为何在我出事后便搬离了此地杳无音信,如不是这样,我那时又怎会答应宋辞书作他的妾只为了一个容身处。
第2章
向王氏请过晚安,我又在崔白的监督下喝了一碗药,尽管蜜饯在口,嘴里仍是苦涩。
独自坐在梳妆镜前,我看着十六岁的自己,青春靓丽,圆润的脸庞如银盘一般明媚光洁。这是一个少女最好的年纪,但我眼底透出的哀伤明晃晃地昭示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年纪。
无论我如何在铜镜前假装,我始终不是十六岁的吴念姝,所以真的是重来吗?这是独属于我的幸运吗?
吹熄蜡烛,我在侧身面墙,崔白贴身环抱住我,他轻声说:“娘子今日有些奇怪?你心中有事尽可与为夫说,莫要憋在心里。”
温热的气息缠上我耳廓,我知他是关心我,他向来对妻子温柔、爱护、体贴,他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并未答他的话,而是转身窝在他怀里回抱住他,轻声说:“睡吧!我困了!”
他没在说话,只是将我拥得更紧了些。
翌日,我醒来,身旁无人,崔白应该是早早地去书房温书了。他是一个既有天赋又十分努力的人。
听说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质疑他未来无量的前途,我也曾对他充满了期待,可惜他功成名就时身旁的人已不是我。
请过早安,用过早膳,我独自出门,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着久违的一切,小食摊前的小吃香味扑鼻,街边货郎的叫卖声竟然也悦耳动听,我站在街口深深地呼吸着,感受着自由活着的滋味。
路过书画摊子,我止步看着画中肃杀的山水,久久未挪眼。
画摊老板是个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士服看样子也是个读书人。他见我久久没有离开,热络地向我介绍画中山水:“姑娘好眼力,这幅画画的可是雁南山呢!你看这画工,笔力深厚,寥寥几笔就将山的奇伟、险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可是少见的佳作啊!”
我点点头,记忆里的边塞山峦确实如此,肃杀、冷寂,却又如巍峨的城墙一样护住关内万里山河。
画摊老板还想继续游说我拿下这幅画,我出声止住了他的夸夸其谈,“先生,您代写和离书吗?”
他好似没听清我的话,讶异地看着我,我只好又轻声重复一遍:“先生,您代写和离书吗?”
这下可算听清楚了,他虽还是意外却也点头应声:“写啊。”
我说了我和崔白的名字,然后安静地站在一旁等他书写。
他写得不快,还要连写三份,可我却觉得眨眼间三份和离书就写好了。
我看着和离书,这上面只差我和崔白的签字以及官府印章。只要三样齐全,我和他就再没关系了。一想到这些,我竟有些难过,但还是将和离书叠好收进袖袋。
我不想沾惹书中主角的一切了,只求这一世平安顺遂。
回到家,崔白竟在房里等我,他关切地问:“娘子去哪儿了?”
我指了指手里的包裹,柔声说:“去街上逛了逛,买点零食。”
他知我向来贪嘴,没有责怪只是说:“为夫可陪娘子一起去,娘子下次记得喊我。”
我说:“好。”
见他又拿书看起来,我犹豫着是否在此刻拿出和离书,但我们才成亲不久这显然不是个好时机。
况且这似乎对现在的他不公平,不是吗?他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用以后的他来衡量现在的他。
一想到这些,我纠结起来,也许我可以改变以后发生的事呢?也许在变数中书里那些都不会发生呢?崔白他还会是我的丈夫,我一个人的丈夫。这难道不是我重来一次的意义吗?
思来想去,我没有立刻拿出和离书,把它放到了首饰盒的最底层。
后来的日子,我如同曾经一样做着这世间所有新妇做的事,为他操持家业,打理家中大小事物。但却没有了曾经的笨拙。
如今崔白的家中说不上富裕。开支多进项少,这些年攒下的家底统共那么点,一分一厘都要计划着来。
毕竟,他的青云路哪一步不需要白花花的银两?
我曾经做得不好,只能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没有找到什么生钱的路子。他没怪过我,只是加紧读书,花最少的时间考取功名,闲暇时还帮人做事补贴家用。
我们就这样相携着走过了许多困难的日子。他总会温声对我说:“辛苦了,娘子。”我也会笑着回他:“不辛苦。”
现在仔细想来,这些自觉甜蜜的时光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
又是一年二月,因我有着曾经的记忆,日子过得愈发顺遂。我终于不用再为碎银几两忧心伤怀,崔白也能专心读书。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左手臂出现一条鲜红的血线。
刚发现时,我紧张不已,跑遍了镇上所有的医馆查探它的来因,可是一无所获。
正当我放弃关注它时,它一天一天地一点一点变短,变浅,直到消失不见。接着我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又一次死亡。
我清楚地知道那是死亡的感觉。
黑暗并非无声,它呜呜地回响在每一处,昭示着死亡空间的深邃,空荡。
我像是一缕融入暗夜里的烟,飘荡、飘荡寻不到落处。
不知道过了多久,轰隆一声炸响,我见到了久违的光,它亮的刺眼,仿佛要将我灼烧。等光暗下来,我打量四周,这里还是我的家。
我起身,难以置信地推开房门,崔白正在院子里剪枝,见我出来,他朝我开颜一笑。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怔住,良久,我才如有千钧重负般,一步一步艰难朝他走去,站在他面前定定看着他。
他不明白我想做什么,奇怪地看着我,从他眼里我看到了我的影像。
我问他:“我是不是很奇怪?”
他眨了眨眼,不自然地说:“哪有呀?你怎么会这么说?”
他在说谎,我知道。我不想去追问,只是换了个问题,“今天是哪一天?”
他眼中异色更甚,却还是回答我:“卯月初五。”
我口中喃喃着:“卯月初五,卯月初五……”失魂落魄地回屋。
卯月初五是我发现手臂红线存在的那天,一想到这,我慌忙撸起袖子查看,皓腕如霜,上面什么也没有。
这难道是什么警示吗?我开始留意起一切可能令我死亡的人和物。
没过几天,竟真让我发现了些端倪,我一直喝的补药有问题。
我本不爱喝药,嫁给崔白后,婆母王氏以调理身体为由,时常为我熬制补药。我自小身弱,不好拂了婆母的一片拳拳之心,只得应头喝下。
曾经一样,现在也一样,自我嫁来后补药未有断过。
从医馆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如寒冬里的坚冰,凉彻到了骨子里。
原来,原来我喝的并不是什么补药,反而是药力加重的避子药,只是配方实在精妙,普通人难以察觉。
曾经,在嫁给崔白几年里,我一直无所出,为了能顺利添丁,补药是越喝越多。
没成想,这喝的那是什么补药呀!分明是要命的毒药。
照我原来懦弱的性子,定是不敢把这事闹大了去,默默隐忍不发是我的选择。
但现在的我,怕什么?我才不是那个唯唯诺诺,看婆母脸色过日子的傻儿媳了,如今有的是脾气。
崔白从外面回来推开门就瞧见我黑着脸坐在桌旁等他。
他不解,上前关切地问:“娘子怎么了?是谁惹你生气了?”
我指了指桌上的药说:“你自己看吧!”
崔白看了一眼药,又拿起医馆大夫给我的诊断单子仔细看起来,越往下看他的脸越黑。
我知他是真的生气了。
他强忍下怒气,对我说:“娘子,我会给你一个交待的。”说完就怒气冲冲地去找他的母亲。
直到半夜他才回来,可我今晚并未给他留灯,是以他只能摸黑进屋子。
话说我虽早早地就躺下了,但却并未睡着,听得他蹑手蹑脚地进屋又轻轻躺在我旁边,小声唤我:“娘子。”
我本不欲答他,却又觉得反正我俩都睡不着,不如和他好好聊聊。
“崔白,你说的交待呢?”我沉声问他。
他满怀愧疚地说:“对不起,娘子,对不起……”
我气极,起身一脚把他踹下床,“你今晚去书房睡吧!”
被踹下床的崔白愣了愣,似是从没见过我这凶悍的一面,半刻后才起身独自去书房。
第3章
这是我单方面和崔白冷战的第三日,我不理他,他却比平时更粘我。
我被他烦得气闷,直接回了娘家。
顾忌两家人的颜面和往日的情意,我没对我母亲坦白崔白母亲王氏所做的事。只声称想家了,回来看看。
崔白不敢催我回家,只巴巴地每日等在我开的铺子里。
他说:“娘子,母亲那边我已经说过了,她日后断不会再做出这样的事。你和我回去吧,我让母亲给你赔罪。”
我不看他,也不回他的话。因为我没想好要怎么样面对他的母亲。
崔白着急了,他拉住我的袖口,小心翼翼地喊:“娘子……”
我站住,终于看向他,沉声说:“放手。”
他不舍地一点点松开我的衣袖,看我继续忙碌起来,时不时热情招呼客人,却就是不肯理睬他。他的目光片刻不离地追随着我的身影,严重影响了店里的生意。
我发现了这一点,心中火气更旺了,只好过去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出店外。
到了店外,我想要松开他的手可是却挣脱不开。气得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却笑嘻嘻地看着我,像一个吃到了糖的少年。我一时看花了眼。
他这样,我怎么舍得怪他呢?
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回了家,看见熟悉的大门,我只想说:“恋爱脑真该死呀!”
他的母亲王氏正站在院子里等我,我不想见她,转身要走,崔白拦住了我,恳求道:“娘子,给我母亲一个解释的机会吧!好不好!”
我定定地看着他,轻叹一口气,然后向他母亲走去。
“母亲安好。”我微微屈膝向王氏行了个见面礼。
“念姝,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怨我。我不怪你,毕竟这事确实是我对不住你。”王氏的语气平淡,听不出来有什么愧疚之意,就好似她只是在谈论今日的天气一样。
我不回话,只平静地看着她的脸,静等她的下文。
果然,她又说:“虽然是我对不住你,但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你身子不好,本就不适合受孕,阿白他忙着读书考取功名,你们现在不适合有孩子。”
我听了这番话,心中没有什么波动,我能指望她真的意识到我的生育权是属于我自己的吗?
可我还是想问:“母亲,你知道你给的药我一直吃下去的话会永远也怀不上子嗣吗?你知道我喝的药里有相克的成分,再继续喝下去的话会直接死掉吗?这些你都知道吗?”
王氏听了我的话惊得后退一步,没敢再看我,口中喃喃道:“怎么会?怎么会?”
崔白见状不对劲,立马走过来,“母亲你怎么了?”
看着这母慈子孝的一幕,轻笑一声独自一人回了自己的家。
我母亲见我又是一人回来没好气地说:“怎么?还没和好?”
我说:“以后别让崔白来我们家,我不想见他。”
母亲没忍住上手拍了我一下,“你气性怎么这么大?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站离母亲一步,烦躁地说:“这您就别管了。”
第二天,不出意外崔白又站在我的房门外,看来母亲并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见我出门崔白又巴巴跟了上来。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像是一晚没睡,而我却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的模样。
午时,我在醉香楼点了两个时蔬炒菜、一只酱香鸭,然后和店里的伙计美美地吃了一顿。我胃口好,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他在一旁,我没有邀请他,伙计们也不敢违逆我。
傍晚,我关店回家,饿了一天的崔白还在跟着我。
穿过街道,我驻足停下转身生气的问:“你怎么还不回家?难道是等我请你吃饭吗?”
他嗫喏着说:“我送你回家。”
我说:“不需要。”
闻言他向后退了一步,我很满意,转身继续向前走,可没走几步他又跟了上来。
我再次驻足看着他不说话,他也停下,我俩远远的对视着。
“你到底想怎样?”我忍不住发问。
他又后退一步说:“我想看着你,远远的可以吗?”他问得小心翼翼。
我气笑了第一次发现崔白还有这么无赖的一面。
“我们和离吧!”我扔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再不管跟在身后的他。
崔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呆在原地,等他回神后忙不迭地奔向我,从背后拥住我,“别和离,不和离,娘子别不要我。”
……
后来,我们是怎样和好的呢?是母亲天天在耳旁念叨夫妻哪有隔夜仇;是崔白日复一日雷打不动地围绕在我身边求和;是这个时代女子独自求生关卡太多,麻烦太多。
我妥协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命运。
在我决定和崔白回去那天,他高兴坏了,说我是他失而复得的珍宝,今后保证不会再丢了。
周围人也由衷地替我俩高兴,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做了一顿好酒好菜给我们庆祝。
夜里,我望着天空中高高挂起的月亮失神,他拿着衣裳出来为我披在身上,“娘子在看什么呢?”
我说:“今晚月色真美。”
“嗯。”他揽过我的腰同我一起静静看着月亮,月光洒在我俩身上,地上的影子互相依偎。
王氏没有再过问过我俩的事,她似乎已经皈依了佛门,整日念经拜佛。可我还是提出和崔白离开这里,去临川。
临川在江南,临川学院是历朝历代出名的学院,当世许多大家都曾在临川学院执教。崔白想要入朝为官,去临川学院深造再合适不过。
曾经,因为家境拮据,他没能去成,现在,无论如何,我都想让他去,也想避开所谓的剧情。
崔白放不下他母亲,一直在犹豫。我不着急,便也不催他。
出人意料的是王氏劝崔白尽快出发去临川,为着儿子的前途她想来也是操碎了心。
第4章
我俩到的时候,正是江南好时节。青瓦白墙、烟胧雨巷,风景美如画,和我儿时记忆里的秀丽江南一模一样。
崔白文采斐然顺利通过测试进入临川学院,并拜前任太傅陆元任为师成为他的关门弟子。
我也依着兴趣,在聚贤街开了个茶铺,生意兴隆。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常下去时,茶铺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从没设想过我们还会再见,嘉平伯宋辞书。
他穿着一身月白锦衣,执着远山图扇翩翩而来,活像一个万花丛中过的风流子弟。
“听说这一间茶铺的老板娘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今日一见也不怎么样嘛!还不如茶铺名有趣。”他坐在客位上,毫不客气地说。
茶铺里的其他客人听了他这话,纷纷侧目瞧这位大放厥词的年轻人,一看竟是一个貌美俊俏的后生,气质不凡、衣着华贵估计又是哪家的公子。
我不欲与之争辩,况且我本来就生得不是十分美丽,只是清秀而已。本着来者是客的原则我同他说道:“长得不合公子心意,是我的不是。公子要喝当下时兴的点山萃还是招牌茶雨前龙井。”
这两款茶主打的就是一个贵,奚落我,看我不让你大出血一番。
宋辞书也不墨迹,直说:“雨前龙井吧!”
我没有逗留,退下去为他制茶。
茶制好,我让李姐姐为他呈上,他却说:“老板娘怎么不来替我上茶?”
李姐皱眉,“阿念她在忙。是我来招待,您有什么意见吗?”
李姐姐性情直率,向来如此快言快语,我怕宋辞书为难她,便立刻出现,“公子要我来上茶,定是看得起我这茶铺,我在此谢过公子!”
李姐姐见状退下去为其他客人上茶,我只好额外关照宋辞书这个事精。
宋辞书,盛京贵公子圈中第一人,雅名在外,琴、棋、书、画、诗、茶无一不通,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要求更高,是个不容易被讨好的麻烦的人。
今天遇上,我只能自认倒霉。
不过,兴许他今天来真的只是为了品茶,上茶之后没有再说无礼的话,也没有刻意地找事。
也有可能是我手艺还不错,他没有找茬的点?我自恋地想到。
恭送他离开后,我希望他不要再来,却又忍不住好奇他来临川的目的。
他曾经也来过临川吗?是为了什么呢?
今日崔白回来得晚了许多,还带了一身酒气,不过人倒是清醒的。
“你今日有什么高兴事儿?怎的喝上了酒?”我打趣道。
他捏了捏眉心似是有些累了,温声回我:“今日书院诗会,大家高兴,我也陪着喝了几杯。”
“几杯?”我斜眼看他。
他忙解释:“真的只喝了几杯,其余的我都洒了。”
我笑道:“怪不得像个酒虫,浑身酒味。快些去洗洗吧!”
虽然崔白说自己喝得少,我看人也还算清醒,但我不放心,还是趁着他洗漱的时候去厨房煮了一碗醒酒茶。
饮过茶,他抱着我问:“娘子今日如何?”
我回:“挺好的,街坊四邻都挺照顾我的。生意也还不错。”
“你呢?诗会可有意思?”我问。
“有意思,今日院长带来一位公子,他文采过人,着实让人佩服。”
听他这么说,我好奇道:“哟,让你佩服的人可不多,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他只待了一会儿,许多人都去找他说话,我没来得及。不过应是京城来的。”
我失望地说:“好吧。”不再追问,随后打了个呵欠又说道:“我困了。”
他笑道:“才这会儿就困了,小懒猫。”
我摆摆手示意他松开我,我要去睡了,他却定定看着我不放手,那眼神活像是要把我吃了。
我被他看得心虚,轻声说:“下次吧!下次一定。”
他闻言轻叹一口气,将头靠在我肩上说:“娘子,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我忙说:“对不起,最近茶铺里忙,等李姐姐她熟悉了就不忙了,到时候,我一定给你补上。今晚就算了吧?”
“好啊!那我来算算,娘子已经欠我多少次了吧!”
我头皮一紧,慌得一把捂住他的嘴,“不许说。”
他笑眼盈盈地看着我,眼神说不上清白。
请告诉我,崔子墨你不是那样的人。
还好,还好,他是克制的,让我安稳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我精神饱满地去茶铺,李姐姐也早早地到了。我俩准备好就开门迎接新的一天。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是?
是宋辞书。
看到他,我真情实感发自肺腑的笑容瞬间变成了假笑。很好,又是当假笑女孩的一天。
“公子早安!”
“吴娘子安!李娘子安!”
“公子这么早来茶铺是想喝点什么?”
“来杯春雨吧。顺便再上些点心。”
我下去准备,李姐负责招待。
茶端上来递给他,我就站到一边。期间,他看了我几眼,欲言又止。
我没理会他,自顾自地忙茶铺里的事情。
“吴娘子不如来陪我喝一杯?”
宋辞书当我这里是秦楼楚馆呢?还陪他喝一杯,我呸……
“公子,是有什么烦心事吗?”快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我并没有答应他而是反问他。
他踌躇着说:“要是有一个姑娘喜欢你,但你对她并没有感觉,你会怎么办?”
我犹豫道:“我是女子,应该不会有女子喜欢我。”
他语结,然后又说:“那就男子,如果有一个男子喜欢你……”
我直接坦言道:“要是男子,那就给他一百杀威棒让他反思反思觊觎人妇是不对的。”
他:……
但不死心又说:“我是说如果你没有成婚,是在你没有成婚的时候。”
我说:“不好意思,我和我夫君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实在不能体会公子的境遇呢!”
他无奈只好摆摆手,示意我别说了。
我看他没事就继续去干自己的活儿不再理他。
“矫情。”我想我能猜出来他为什么来江南了。
不出意料,尚书嫡女徐佳颜及笄日对他告白,而他为了避开议亲特地跑来江南躲。
徐佳颜和宋辞书这两口子走的欢喜冤家路线,婚后日子和和美美,可怜我这等普通人沦为他俩爱情路上的踏脚石。
这一次我必不会重蹈覆辙。
深深看他一眼我移开视线,注意力重新放回账本上。
宋辞书将早茶喝出了夜酒的架势,他是想要“醉死”在我这里吗?
我抢过他手里的杯子,“公子不如去飘香楼喝上一坛十里香,好过来我这里忧愁。”
他看着我眼神亮亮,“吴娘子怎的还赶客?这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我轻笑:“生意自然是要做的,可我这儿是品茶的地儿,公子如此这般牛饮,不如去酒楼来得痛快。”
我是好心建议,当然也是不想他再呆在我这里碍眼。
他可不管这些,混不吝道:“既然如此,吴娘子可否赏脸同我去飘香楼喝上一杯。”
我是真的会谢!他不是知道我早已嫁为人妻吗?他怎么敢的呀?
我冷脸:“公子慎言。”
见我是真的生气了,他也收起方才浪荡的模样,起身拱手施礼赔罪。这一番动作下来才勉强找回些翩翩公子的气质。
可这种假象没有维持过三秒,他又说:“我瞧着吴娘子一直避着我,却对其他客人喜笑颜开,某可是有哪里得罪了娘子。”
我心里头一咯噔能直说我就是单纯地看他不惯吗?不能,所以我只好赔笑道:“公子说得哪里话?来者是客,我是生意人,怎么会刻意避着公子呢?”
他不依不饶,“那我与李姐一样唤你阿念吧,毕竟我们也算相熟了。”
他这是打哪论的相熟?我们统共没见过几面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