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始终是强烈的。人需要被认可,通过事业、能力获得的认可始终只是部分的认可,陌生的公众不可能真正知道你是谁;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才能真正被看到。

学者金雯研究18世纪的情感,同时也是看见当下,试图寻找思想的脉络。
她会在课上与学生聊及对作者们所表达的情感的看法:卡夫卡似乎专注于勾勒现代人内在分裂的普遍性精神症候,并不在意小情小爱,然而,他可能是最关注男性间社会纽带及其对男女情爱影响的作家之一。她认为,作家在公共生活中看到的不公正的现象、感受到的对个体的排挤和疏离,也会体现在对亲密生活和欲望的书写上。没有作家可以不写隐秘情感和私人关系。

(图/《点燃我 温暖你》剧照)
金雯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任教,如今于华东师范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她尤其关注文学与情感史、阅读史的关系。在她的著作《情感时代》里,她论及自己对理性与情感关系的观察。启蒙时代是一个强调理性的时代,但与此同时,“情感”在哲学话语和大众文化中异军突起,感伤文学、煽情文学渐次盛行。与其将启蒙与情感或理性相连,不如说启蒙时代是一个试图弥合理性与感性裂痕(但并不那么成功)的时代。
她认为,某种小说流派的盛行,一定是整体性文化工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孤立的现象。所谓文化工程,必然不是出自某种顶层设计,它是不同的话语和物质性力量汇聚到一起之后形成的人类社会的演化轨迹。以私人情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成为贯穿近现代历史的重要文学现象,正是因为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永恒需求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代氛围中变得更为重要。
以下为《新周刊》记者与金雯的对话。

“恋爱脑”并非不可控、
让人丧失自我动力
《新周刊》:如何理解“情感”与“自我”的辩证关系?如今人们聊及“恋爱脑”,似乎会偏向于将情感看作一种不可控制、会让人丧失自我的东西,但《情感时代》提到,人通过情感来自我发现与启蒙。
金雯:成书过程中发现,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情感”。界定情感就是要厘清身体经验与自我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情感首先是身体的直觉,在我看来,它也是长期以来人基于身体的经验和语言观念不断交互形成的价值判断系统,一旦形成,就成了人的选择和行动的根本动力系统。这种基于身体经验的价值判断一定是基于“自我”观念,即基于“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判断,自我是情感的基础。
我恰恰不认为“恋爱脑”是不可控、让人丧失自我动力的。从根本上说,“恋爱脑”追求他人的认可和关爱,用以满足自我。他们希望从他人身上寻求独特感的印证,获得完整的认可、关注和重视。

(图/《很想很想你》剧照)
文学里著名的“恋爱脑”包法利夫人追求强烈的情感满足,实际上她追求的是他人对自我的认可。现代人当然可以超越这种局限的、狭小的“自我”视角,但这种对认可的需求不是被规训的产物,人天然地需要他人,人的情感里必然有依赖、同情、体恤他人的元素。
年轻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恋爱脑”,并不是因为没有自我,而是自我还没有完善地建构,有很多感到不安全的地方,需要在他人的认可下,发现和印证自我的力量、魅力。年轻人有可能在追逐认可的过程中,陷入某种具体的迷恋。

2024年2月14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情人节期间,某酒店用灯光在建筑外立面组成巨大心形,一对情侣在雪地里接吻。(图/视觉中国)
年轻人还有强烈的荷尔蒙,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不可遏制的力量,与对认可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因此“恋爱脑”出现是很正常的。人的发展历程并不是要摆脱“恋爱脑”,而是使之重置、升级、换代,让自我追求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不是仅仅追求排他性的亲密情感。人可以在更大的领域里与公众形成情感连接,做利他的事情,成就更高的价值。这不妨碍他们在二人世界中成就超越性的精神和情感连接,两者并不矛盾。
当下,人们觉得不应该把自我寄托在他人身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体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并非真正理性的考量。“恋爱脑”是一种过度的情感,反对恋爱也是一种过度的情感,是被恐惧所占据的心理状态。我们还是需要对他人抱有希望和信心。
东方与西方书写情感的不同方式
《新周刊》:20世纪初流行鸳鸯蝴蝶派小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琼瑶的作品成就了庞大的故事王国;21世纪初,青春小说被年轻人追捧。它们算中文语境里的“情感小说”吗?它们盛行的原因是什么?
金雯:从琼瑶的故事到青春小说,再到今天的仙侠剧、偶像剧,很多都在追求极致的、纯净的情感,这些文学现象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说明,对两情相悦的亲密情感的追求,可以说是一条贯穿历史的红线。人都有自我满足和被认可的需求,所以这条线索不会断,它会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借助不同的媒介文化与时代脉搏对话、交流。
琼瑶小说兴起,正是港台文化兴起时,这也是我成长的年代,人们开始自由地谈论爱情、欲望、青春的冲动,琼瑶的兴起与整个风潮联系在一起。琼瑶的故事也有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相似的情感描写、虐心情节,男女主人公爱而不得,要突破很多障碍才有可能在一起。当时人们没有仔细考虑过爱情这件事情,突然看到了这些故事——爱情虽然很苦,但它最后会产生一种极致的愉悦,这对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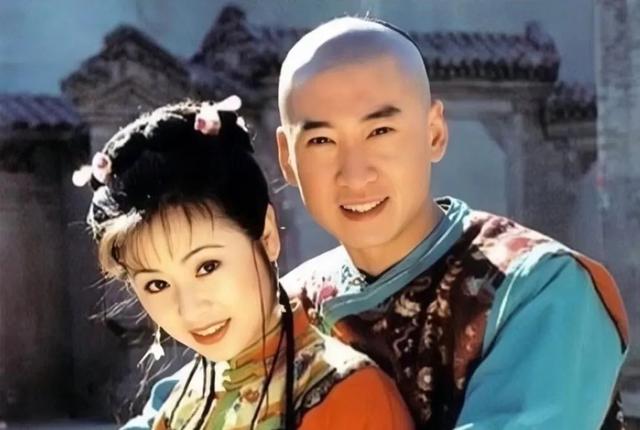
(图/《还珠格格》剧照)
从情感的压抑到情感的释放,这个过程中的快感是不可名状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向往不断向外界文化开放的社会,倾向于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琼瑶小说的火热是容易理解的。20世纪初以来,中国女性有意识地进行探索,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变革,爱情追求也成为女性成长的路径,是女性全面成长的一种隐喻。
《新周刊》:英文中有许多表达情感、情动的词语,所对应的情感都非常细微。如果对照西方、东方情感小说的文本和内容,两者在情感文化上有哪些重要的异同?
金雯:很难笼统地说不同时代的情感小说之间有什么共通性、差异性。我想,西方人书写情感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分析情感的传统。小说里有许多人物的自白,作者有意识地制造情感的谜团,意识到角色表露的情感并不是其情感世界的全部。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如詹姆斯、契诃夫,都会描写人物不可理喻的行为和选择,展现其被无意识情感推动的特性。小说家对情感的书写,往往流露出一种科学的剖析精神,将情感抽丝剥茧地展示出来。

(图/《红楼梦》剧照)
中国人没有这种分析的传统,但也有一条原生的情感小说脉络,这条脉络可以追溯到18世纪。18世纪不仅有《红楼梦》,也出现了女性作家写的弹词小说如《再生缘》,诞生自南方的戏曲文化。这些情感小说不讲究剖析,少有长篇的独白,读者只能从人物的行为、表情的描写上揣测他/她的想法。《红楼梦》会向读者展示家族内在的生态、每个人物的关系,但是叙事者不会深入人物内在的意识,不会说明林黛玉怎么想、贾宝玉又怎么想。读者通过人物的表情和行为、所作的诗词和隐晦的话语推测他们的意识,这就体现了中国和西方对情的理解的根本差异。
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就开始讨论灵魂与身体是可以分割的,也分析情感、欲望与理性的关系。而在中国,从《诗经》开始,情感就像一种无所不在的物质性力量,像气候、风一样,是一种感染人、围绕在人们身边的氛围。它能与人的自然身体结构结合,是不能单独提炼出来的。
像《诗经》里的“关关雎鸠”, 就是通过塑造美好人物、描写自然环境渲染一种氛围,以此净化读者的心灵,让他们向往美德。把文学中的情感看成一种氛围,就不需要去剖析。中国人对情的理解和实践包含着一种整体性态度。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理论,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连接、人与他人的连接,以及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内含的流动和关联。

(图/《国色芳华》剧照)
我们有时对东方、西方文化差异有一些脸谱化的认识,这种一概而论的认识不一定可取。从西方内部来说,对情感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分歧,一些英国作家强调道德教化,在小说中塑造了具有美德的女性,希望让女性引领道德风尚。在狄更斯笔下,我们看到的是胸襟宽广、情感温和的女性,她们可以弥合身边人情感的黑洞。18世纪在法国出现的情欲小说、浪荡子小说则开启了一种直书身体欲望的传统,让我们把西方与性解放相关联。可见,我们无法概括西方人或任何文化的情感模式。
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始终是强烈的
《新周刊》:18世纪,情感小说自我暴露最极致的方法是采用书信体。它有一种核心张力,作者将私人情感放到公共空间中展示。当下也有相似的文化现象,人们会在直播间谈论私人情感。为什么观看私人情感如此具有吸引力?你如何理解私人性与公共性?
金雯:在16、17世纪展现中间阶层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之前,以社会精英为主角的作品,比如以骑士和贵妇人为主角的传奇,很多是以情感纠葛为主线的。这说明人们对于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一向非常关注。在文学作品中,人们能看到内心最隐秘、最复杂的情感镜像——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跟别人交流,甚至很难与自己交流,这些情感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在读诗歌、看小说的时候,情感突然会被点亮,由此产生巨大的认同感和快感。

(图/《傲慢与偏见》剧照)
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之后,人们有了版权的观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不需要再依靠贵族的赞助。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经验都能转化为公共资源,这就突显了个人的边界问题。
大部分人看小说,当然想寻找共鸣、寻找精神的慰藉,然而不会产生过于极端的情感。但看真实的人的故事就不太一样了。主人公是读者在社会场域中的参与者、竞争者,因此真实故事中的人会让人羡慕、嫉妒,也会让人产生同情并升华,真人的故事一定会激发强烈的情感。
文字能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而情感力量可以被社会所征用,用于进行道德建设、社会动员,但它也会催生强大的攻击性。在公众面前曝光必然招致暴力,但我也并不悲观,人们必须行使公共话语的权利,不能因为可能的暴力而退缩或自我阉割。我觉得真诚仍然是公共交流的要义,或许不试图打造人设,与观众或听众平等相处,也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真诚。
《新周刊》:大家对情感小说永远是有需求的,但它们似乎很难成为经典。为什么?
金雯:通俗的、流行的情感小说,许多在艺术水准上不太高,鸳鸯蝴蝶派开启的中国言情小说大多是作为文学史现象才被人记忆。同样,18世纪晚期欧洲泛滥的感伤小说也是批量生产的,一些出版商甚至雇佣写手进行创作。

(图/《百年孤独》剧照)
不过,话说回来,许多经典作品其实是高级的言情小说,它仍然是以私人情感与人物内心的情感纠结为主要题材,只是比普通言情小说更具有创新精神和洞察力。对亲密关系的追求的确是跨历史的现象,但经典作品会将矛盾的心理现象及其与时代进程的关联表现得更完整、深邃,引发多元的阐释。纪德的《窄门》、杜拉斯的《情人》,还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写的都是爱情。
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始终是强烈的。人需要被认可,通过事业、能力获得的认可始终只是部分的认可,陌生的公众不可能真正知道你是谁;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才能真正被看到。私人和公共不能截然分开,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是公共生活的折射,在公共空间中我们感觉不被全方位地看见,才会有对私密情感的追求。
我在文学课上与同学们谈博尔赫斯和卡夫卡,就会说到他们谈的是人在现代社会中感到的被异化、被局限的境况,看上去写的是宏大的主题,但是内核仍然是个体的私密欲望,是人对被亲人、爱人认可的欲望以及超越这种欲望的挣扎。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看到的弊端,感受到的对个体的排挤和疏离,都会体现在对亲密生活和欲望的书写上。所以,没有任何一位经典作家可以不写私人情感。
情感危机是现代性的标志
《新周刊》:最近这些年,人们常常讨论“自恋的趋势”,各种媒介文化也都在满足自恋情绪。你认可这种自恋文化的形成吗?在西方,也会有这种变化吗?
金雯:我和不少学者聊过相关话题。我们认为,当人们的情感能力普遍下降的时候,情绪价值就得以突显。所谓情绪价值就是简单粗暴的情感需求。它偏向于自我保全和自我满足,不需要思考“我”与他人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因为“我”在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已经太多了,无暇、无力顾及他人。

(图/《情人》剧照)
这种所谓自恋文化杜绝带有自我忏悔性质的情感——每个人似乎都想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向往通过社交媒体得到即刻的情感满足。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有,爽剧在中国和美国的短视频平台上都非常热门。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不太倾向于把今天的文化视为大型的自恋文化。
我希望人们看到今天的文化也有“百年孤独”的一面,《百年孤独》是很有前瞻性、预言性的小说,它体现的是现代人感受到的普遍的孤独和疏离。我觉得所谓自恋文化的背面就是一种普遍孤独的状态,人隔绝了自己最深层的情感需求。正因为亲密关系可望不可即,所以这种需求被刻意压抑,或者说,人们没有得到过它的滋养,看不到可能性,所以主动与对爱的需求拉开了距离。《百年孤独》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勇气相信和投入亲密关系。

2022年12月16日,安徽合肥。一对情侣在寒冬的街头拥抱。(图/视觉中国)
这样的文化看似很冷漠、很自私、很自我,它隐藏的是一种恐惧和绝望,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些煽情来对冲的。所以人们也需要动画片、纯爱剧,以得到精神上的缓解。
任何人在现实中都很难实现身心合一的关系,如果我们坚持将亲密关系定位为完美持久的关系,就必然会处处遇挫,遭受心灵的打击。人们也许应该学着接受不那么完美、不那么长久的关系,《正常人》《好东西》正是展示这个道理。不完美的关系仍然能够让人得到巨大的个人成长,让我们能够为下一次更完美的关系做准备。

(图/《好东西》剧照)
年轻人在试图摸索和构建新的情感关系,它注定不完美,也许无法一下子满足内心最深层的渴望,但它也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关系,让人的情感得到低强度的滋养,存活下去。它也是让人能保持对神圣情感的激情和意愿的疗愈式情感训练。
我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也不仅仅是自恋的危机、信任的危机,而是爱欲的危机。人们不相信亲密关系,以真挚情感为基础的田园牧歌的场景不再被人向往,反乌托邦小说中想象的人类的灭亡看似要成为现实。
爱欲的危机并不是通过保守主义的回潮、强制的行政命令而得以解决的,越是压制,越是会带来种种冷漠、自恋的情感症结;爱欲的沦丧,只能用爱欲来重新点燃。人文思想、人文关怀其实越来越重要,并不是如人们以为的那样无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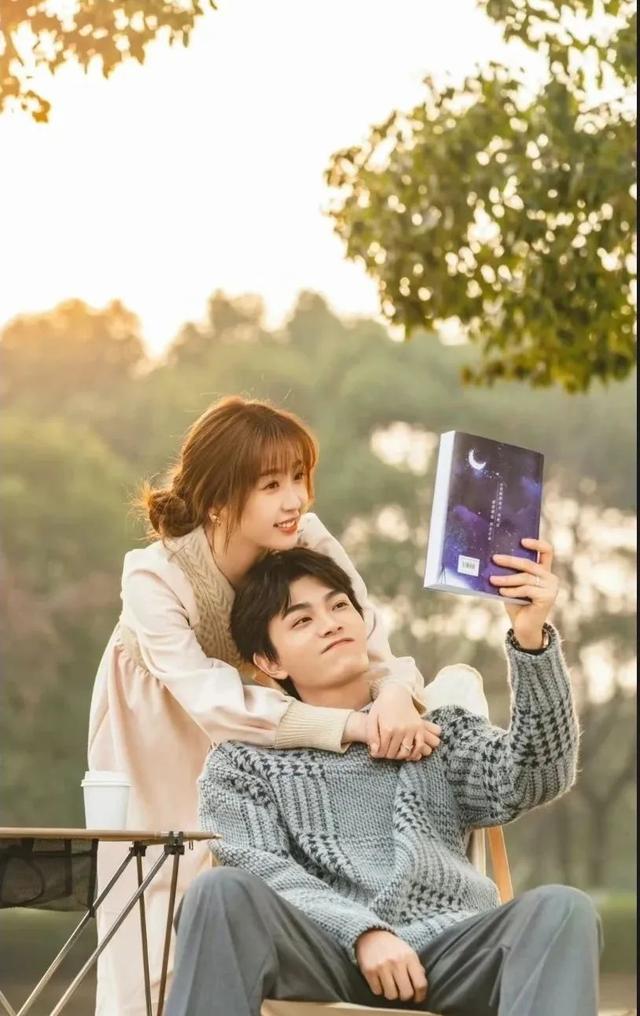
(图/《月光变奏曲》剧照)
《新周刊》:人们谈论情感的时候,也常常强调理性的重要,我们要如何理解当今这个“理性时代”?如果情感也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什么?
金雯:人们惯常以为,理性可以掌握情感,但情感是不能通过理性来解决的。理性越是狂妄,越是觉得它可以解决情感问题,越是会激化矛盾。我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发现小学对家长的教育与当下生活是脱节的。学校仍然教育家长要培养小孩的自立精神、感恩心态,让他们不那么自恋。
我觉得这是教育行业的认知误区。年轻人很自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要让他们减少自恋、有感恩意识,这是一种理性化的解决情感问题的手法。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今天的小孩需要的并不是在更多的压力下学会感恩。家长需要理解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矛盾、什么样的焦虑和压力之下,通过什么样的关注,让他们在自我非常脆弱和薄弱的时候挺过这一关,最后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如果总是试图让孩子少一点自恋,通过教化去扭转年轻人,只会激化代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图/《沙漏》剧照)
长辈的不理解,会使得年轻人变得更为精致和利己。当他们放弃了对他人的期待,觉得一切都要依靠自己的时候,便会形成一种精致的利己和强行教化之间相互加强的闭环。这最终会带来爱欲和人口的危机。
情感的危机总体来说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症候。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的兴奋、普遍的激动、普遍的向上的渴望,与他们所面临的局限和束缚会形成巨大的冲突,忧郁、哀伤、愤怒等负面情绪成为常见的情感,疏离、对抗成为常见现象。情感危机就是现代性的标志,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这两个问题都导向更深的思考,我觉得做人文研究最大的社会功用就在于,我们可以跳出常规思维,发现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预设、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它体现在顶层设计上,也体现在中层、底层的实践上。
当我们认为通过物质生活的丰富、通过理性的教育和教化,人们就能更加和谐地共存,社会会变得更加健全,这种线性的设想也许注定是要失效的。现代性的危机没有好的解药,但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就是尝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多的正向情感连接与信任,这也正是人文学科的价值与使命。
编辑 谭山山
运营 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