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上海南京东路,人潮涌动。
20年前,这里是繁华的“中华商业第一街”。
20年后,游客仍络绎不绝,但商业随时代悄然更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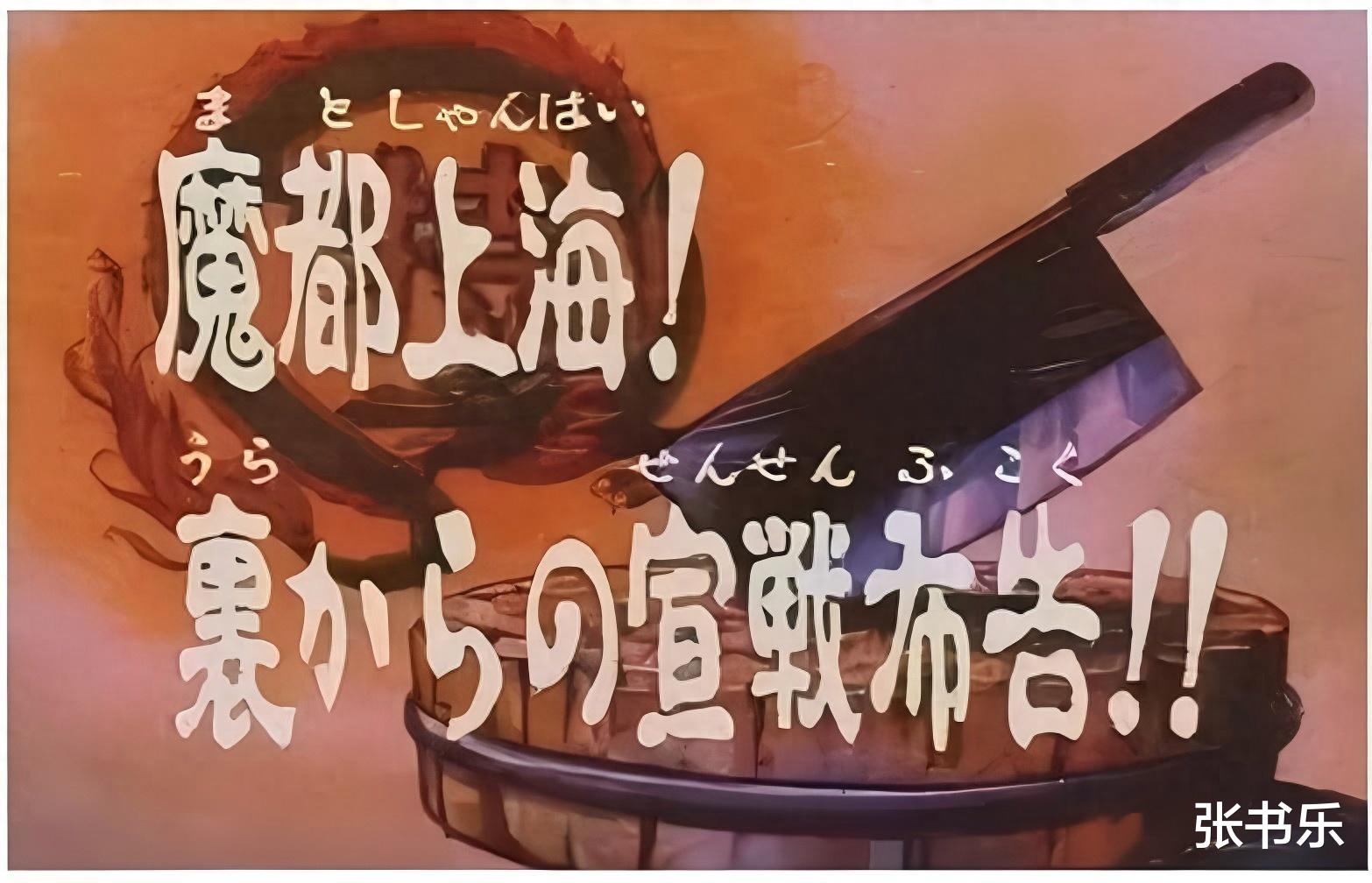
一众老字号商场里,二次元商业体“百联ZX创趣场”的大楼格外醒目。
一楼的世嘉(SEGA)快闪店前,围满了年轻人合影留念。
而商场内,从负一楼到六楼,手持“痛包”的Cosplay爱好者穿梭在各层店铺,货架上摆的是“谷子”、手办。
开业仅两年,这座1万平方米的商场总计销售额已突破7亿元,单日最高客流量超9万人次,被圈内称为“魔都秋叶原”。
秋叶原是全球闻名的二次元文化圣地,位于日本东京。
但在上海,越来越多的魔都秋叶原正在崛起,让这里成为了中国谷子经济的最佳吃谷地。
然而,“谷子经济”在上海爆发,并非无本之木。
上海是中国动漫的兴起之地。不只是这里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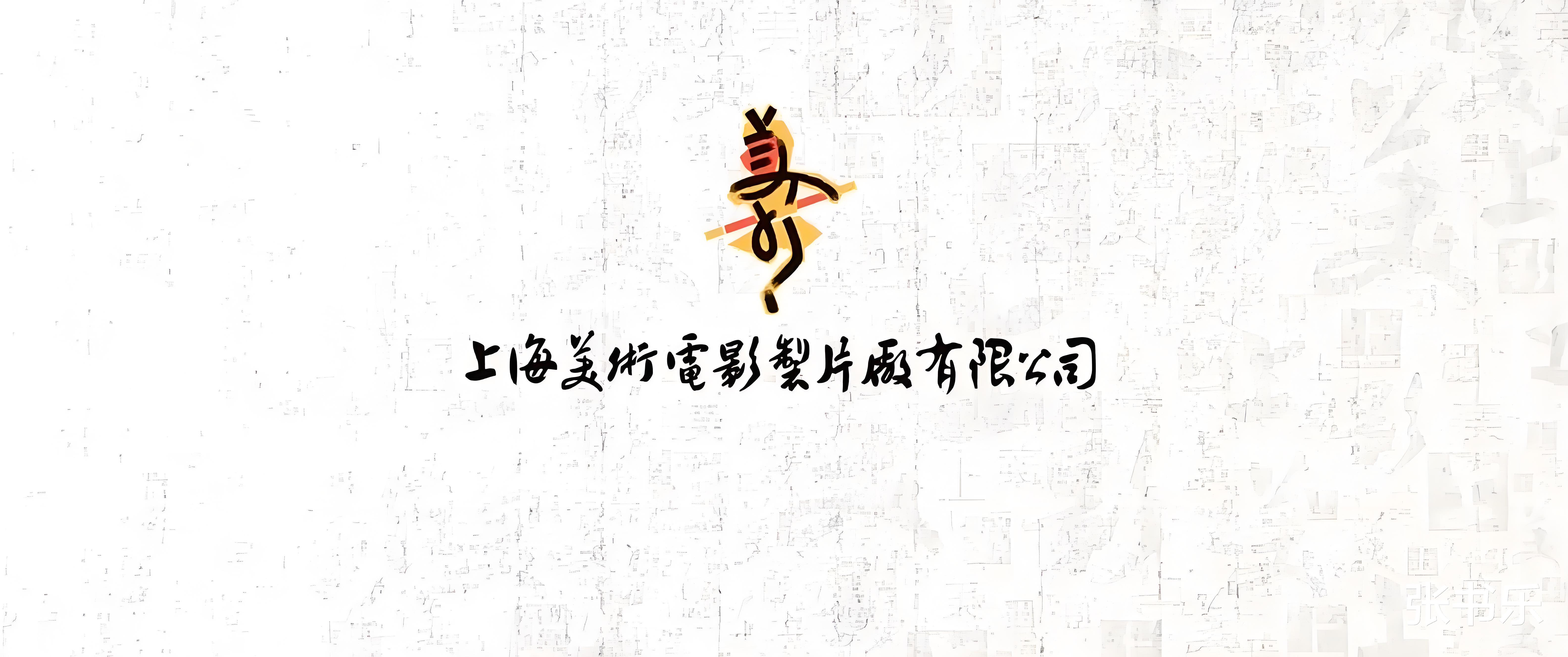
1988年,在去世前3个月,被誉为日本漫画之神的手冢治虫忍着病痛前往上海,拜访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万籁鸣,并曾画下孙悟空和阿童木的跨时空“合影”,祝愿日中永远友好。
对于手冢治虫来说,这是一次朝圣之旅。

“真正让我大开眼界,深深打动着我,激发我今天创作欲望的,是1942年在日本首映的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手冢治虫的话语里,充满了致敬。

这一印记也留在了他的动漫作品中:他的第一部动画题材源自西游记,最后一部作品则名为《我的孙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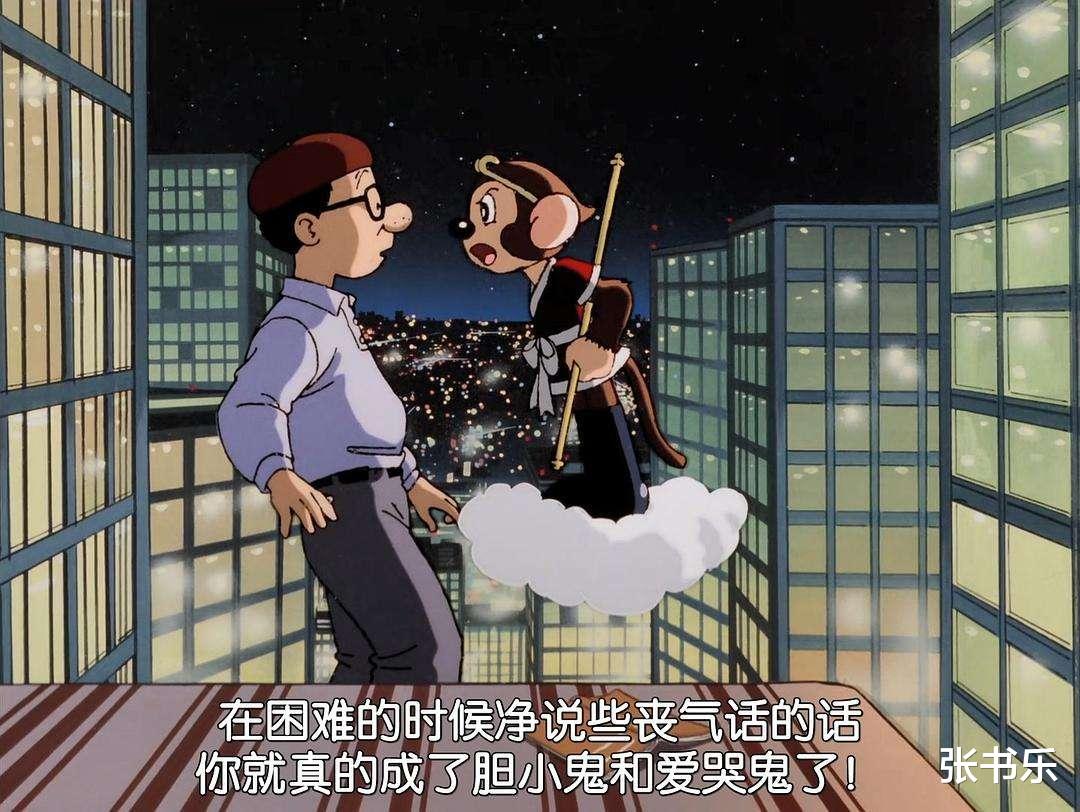
这部《铁扇公主》诞生于1941年,由万籁鸣和他的三个兄弟共同创作完成。
如果说《铁扇公主》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历尽波折,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动画人才云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背靠蒸蒸日上国力的国产动画则开启了引领世界潮流的宏大气象。
1960年代问世的《大闹天宫》是一座丰碑,这个花费万籁鸣、严定宪等人五年的时间的作品,用其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和以京剧为灵感的音乐,斩获了无数国际奖项。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等45部动画作品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先后73次获奖。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拿奖拿到手软,更在国际动漫领域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名。
或许,手冢治虫没想到,万籁鸣也没想到,他们相见的数年后,中国动画却走入了长达25年的低谷。
给中国学派一个棒喝的,恰恰是手冢治虫开启的日本动漫大潮和如影随形的美漫。
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并未就此沉寂。
1999年投资1200万的《宝莲灯》成为一次反击,效仿《花木兰》,全面学习好莱坞的制作并将其和中国传统故事相融合。

只是,尽管从配音到歌曲全是当时国内顶流艺人参与,却由于中西合璧下的异域风情过于浓烈,
最终国人不喜、洋人不看、票房惨淡。
多年的痛定思痛后,2023年《中国奇谭》横空出世。
这个以中国特色的“妖怪”故事为主线的中式奇幻动画短片集,讲述了8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
其题材包罗万象,从乡土眷恋到末世情怀,从生命关怀到人性思考,铺陈开一个极具中式想象力的世界。
仅仅1个月,播放就突破2亿。

但仅仅依靠正在重回潮头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显然不足以撑起中国的二次元经济,上海还有什么?
游戏。
谁说二次元经济一定要从动漫起步?
之所以有这样的惰性思维,在于二次元这一概念来自日本。
从战后萌芽到兴盛,日式漫画在全球独树一帜,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化产品。
二次元经济在日本的路线则是发源于漫画(出版产业),再向影视游戏产业扩散。
然而,中国二次元经济一定要按照日本模式吗?
为何不能有中国特色?

日本二次元从最强悍的漫画出发,进击动画、游戏和玩具,中国二次元完全可以从国产游戏这个“虚拟世界最强产业”,去扩张。
为何必须是上海?
很多人往往会第一时间用海派文化来作答。
但如果看看《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或许更有说服力:
2022年中国游戏产业近十年首次出现收缩时,上海网络游戏逆势增长,同比增长3.66%,国内流水超过千万的移动游戏,每4款就有一款来自上海。
2023年上海网络游戏总销售收入达1445.28亿元,同比增长12.89%;移动游戏销售收入923.62亿元,市场占有率达77.6%……
有如此后盾,上海冲击全球二次元魔都,也算真正拥有话语权。
刊载于《人民邮电报》2025年1月7日《乐游记》专栏428期
作者 张书乐,人民网、人民邮电报专栏作者,中经传媒智库专家,资深产业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