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于东汉这个相对特殊且复杂的历史时代而言,也是如此。东汉时期社会风气变动,政治局势动荡,与此同时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等多种因素相互碰撞,对于文人儒士们的价值观和创作风格都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实际上,研究东汉时期文学及思想的著述岁数量上并不算少,但相对分散且较为简略,而这本《东汉文学思想史》正是首部、也是为数不多的系统论述东汉文学思想演进历程的专著,张峰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以文学发展的自然段落为基本考量,参照东汉政治、文化演进态势对其文学创作及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书中史料翔实丰富,且不乏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正如颜崑阳教授在序言中赞其学术态度之严谨正规,“对于汉代的文学创作及思想,大体都是引据原典文本,既主观理解而又相对客观地描述及诠释,不妄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单向视域投射,当然也就没有主观肆意的批判,这确实是正规的学术态度”。
《文心雕龙·时序》有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
在汉代这样一个开创恢弘气象、影响后世深远的朝代里,世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活跃,创作方式及文学作品随之发生着变化,前朝“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学思想束缚呈现出一种解放的态势,他们敢于进谏,从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生发出多样性的审美特征,也开拓出一片文学的新天地。

《东汉文学思想史》是《西汉文学思想史》的续篇,旨在描述东汉二百年间文学思想的演进历程,为此,张峰屹教授根据文学创作、作家创作活动好文学观念实际发展的自然段落,并结合政局、社会和思想文化演变的情势,把整个东汉时期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来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解读。
书中从两汉之际的政局开始讲起,其中,王莽专权可谓是其中的一个变数,在他实际主政的那二十三年当中,政权两度改换门庭,时局动荡不安,时人的想法和选择也会随着时局起伏变化。而文学正是对于时代的书写,分析其时士人的心态和思想方面的变化,是观察当时文学创作的必经之路。
王莽不仅信重并宣扬图谶,而且非常尊重正统经学并以有汉以来的罕见力度对其进行扶持,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并遍征天下才士,士人们在其篡位前后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从之前的“士人云集”到后来逐渐呈现“不仕王莽”、“无立场者”、“为其羽翼”,抑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多元状貌的情况。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不难看出当时士人们内心之矛盾和无奈,正如书中所写,“他们是痛苦地挣扎在不得已的人生抉择之中”。
作者在这本书中,将对多位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的解读与其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结合起来,也反映出文人才士们的创作倾向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
譬如崔篆就将那种“不认同王莽篡代,心向刘汉正统,对自己无奈行为的惭愧”等复杂纠结的心情,写尽了他的名篇《慰志赋》中,“愍余生之不造兮,了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一篇赋作道出了其苦闷挣扎的心路历程,也反应了当时世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到刘秀在位期间,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前汉建国时的策略,虽然在财富和地位上给复国功臣们以优渥待遇,但在重要职权的授予上却非常严谨。与此同时,刘秀大力推行宽柔仁政的政策,并努力恢复儒学正统,重建经学博士,并重用经学儒士为官。他祭祀孔子,大量征用名儒宿学并授任要职,在种种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下,崇儒的气象逐渐展露。
当时一些主流的辞赋作品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和时事内涵,与社会政治状况紧密相连,反映出那一时期士心民意的寄托,体现出两汉时期人们的一种基本认知——“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政治观感和见解的表达,文学仍然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与此同时,如扬雄般,在文体的开拓和创新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学创作,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光武帝刘秀建武中至和帝刘肇永元初的这五十多年,是东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这时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贯穿于两汉思想史中的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也是东汉思想文化之旨趣所在。
在刘秀在位时期,依然采用经谶并重的思想取向,并引导了经谶牵合互释思潮的复兴,经刘庄、刘烜二帝,再到白虎观会议,刘秀经谶牵合的思想取向通过《白虎通》被进一步地以国家思想“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东汉王朝最崇高的统治思想。
中兴政权和思想文化取向在士人心中得到普遍的认同,他们的认可、疏离或怨望,以及以谶纬文的趋势,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风貌,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创作旨意由讽谏劝诫转向颂世论理”,而谶纬就是最重要的颂世论理一个手段,譬如班固的《典引》《终南山赋》《竹扇赋》,崔骃的《大将军西征赋》《大将军临洛观赋》等等,都是东汉前期赋作颂美主潮的体现,有着十分鲜明的歌咏教化制度的颂汉用意。
东汉文学思想史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和帝刘肇永元初至桓帝刘志和平前后的这六十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内忧外患的影响给社会带来重创,皇权和国力双双衰颓,经学衰变,思想文化也开始呈现衰落之势,文学创作的风格“由东汉前期的激情洋溢开始转向沉实稳健,由理想诉求转向现实关怀”。
其时,“以儒学为体、以数术为用的方术士,或辞官、逃官以避祸,或散财以避‘盈满之咎’,道家观念主导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逸民高士思想行为的传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东汉中期的士人们心态正悄然发生着改变,他们虽然依然有入仕倾向,但也不复那么高涨的热情和渴盼,相较之下,他们更愿意“随遇而安”,呈现出由进取到隐退的心态过渡。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就是张衡,他的作品和态度都体现着东汉中期文人的一种处世心态——“不是汲汲渴渴地追求仕途名利,但也不拒斥;一旦遭遇困辱,便随时或在行动上或思想上抽身隐退。而无论仕隐,他们的内心情志都趋向平静,波澜不惊;同时,坚守人生初衷,始终不改”。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写道,文学艺术之欣赏为士人的生活思想之一部分并蔚成风尚实起于东汉。游艺风气不仅对东汉士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
这一点在东汉中期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倾向当中得到体现,随着社会局势日趋平稳,士人们的心态也更趋于沉静平时,这时出现的一些逞才游艺的创作在事实上推动了文学艺术的进步,对汉代文学观念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人的意识”也开始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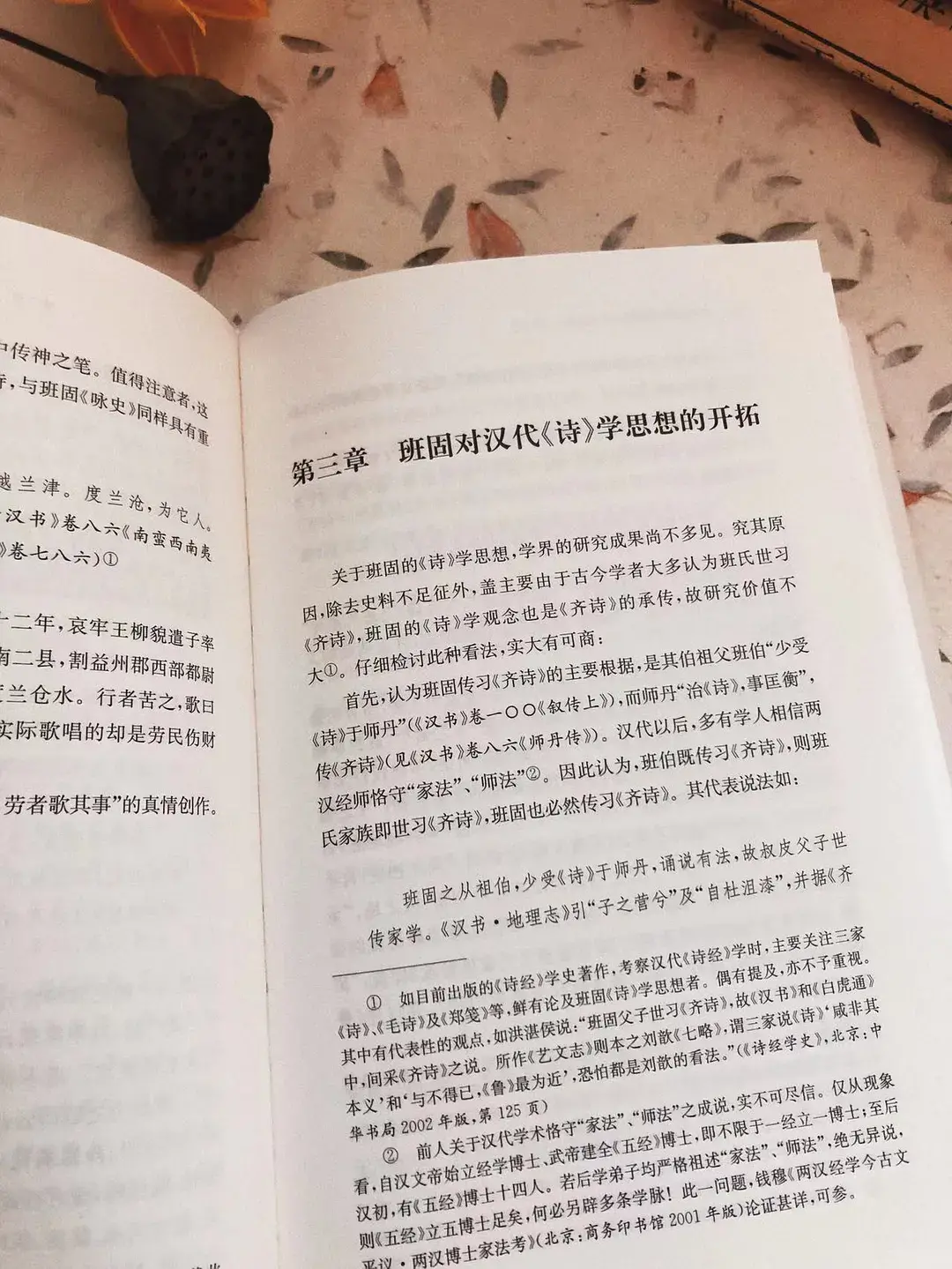
最后,桓帝刘志和平前后至献帝刘协建安末的七十年左右,是东汉文学史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持续衰败,内忧外患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雪上加霜,政治社会衰落加剧。
经学虽然仍是东汉后期思想文化的主体,但也呈现不可回天的衰落之势,“儒者之风盖衰矣”。与此同时,道家思想则迎来了回潮,甚至逐渐发展成为东汉后期的另一种普遍社会思想,此时的文学创作也发生整体转向,面对着残破山河,文人们不再歌功颂德,而是更多地“抒写衰世当中的生命体验,深度抒发个人的情志”,以王延寿、蔡邕、祢衡、建安七子以及五言古诗的作者们为创作主流的时代正式开启,“文学创作整体上逐渐从附庸于政治和经学的境况中摆脱出来,走向独立自足”,东汉后期士人群体的避世之心愈加鲜明,他们纷纷念着“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在回天乏术的颓败之局中只能惟求保全了。
纵观东汉这三个文学思想历史时期,赋是主流创作形式,虽然东汉后期颂世文学式微,但其创作内容依然是政治形势的体现。从两汉之际到东汉前期,颂世赋作是为常态,东汉中期抒情述志的赋作涌现,“个人意识”觉醒,赋作也转为更纯粹的文学本质,这一转化在东汉后期则更加明显。
张峰屹教授通过这三个历史时期中文人创作风格、思想及价值观的分析,将之与社会政治的变迁有机结合起来,呈现出一部全面、系统的东汉文学思想史,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及思想变迁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