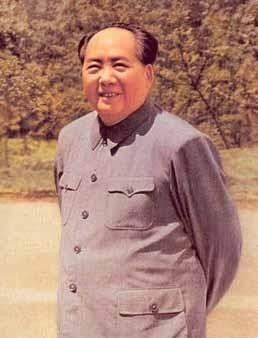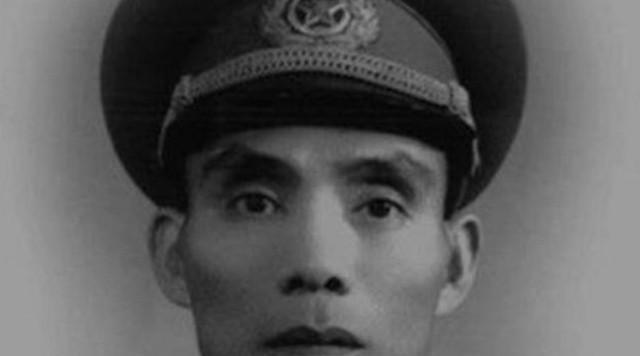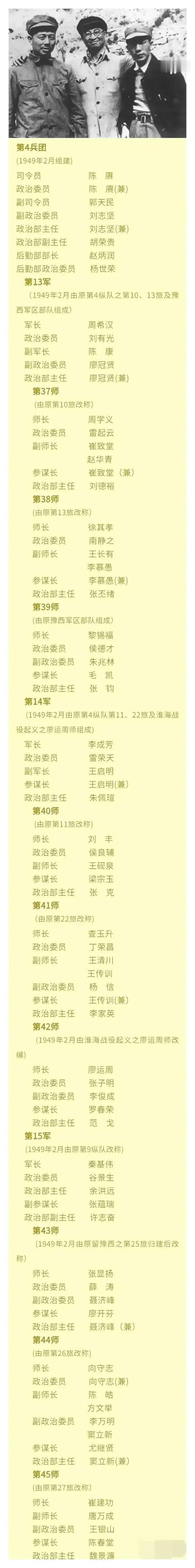1955年大授衔时,毛主席见到陈赓,笑着问他:“怎么样,跟着我干可比老蒋强吧?”
1955年大授衔时,毛主席见到陈赓,笑着问他:“怎么样,跟着我干可比老蒋强吧?”陈赓摇摇头,说:“我的大将不是您给的,是李聚奎给的。”毛主席一头雾水,不明白陈赓的意思。[横脸笑]1955年军衔评定前夕,一个看似平常的午餐时间,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陈赓和李聚奎在军委食堂碰面,这位素来爱开玩笑的湖南将军忽然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对李聚奎说:“老李啊,我这辈子在红军时期从没当过师长,这次评大将估计是没希望了。”憨厚的李聚奎当场就急了,连夜跑到组织部门为陈赓“鸣不平”,声情并茂地为战友的资历作证。结果第二天陈赓被评为大将,李聚奎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哭笑不得。其实陈赓开这个玩笑完全是闲得无聊,1903年出生的他,1925年22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还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时,陈赓曾在一次战斗中背着受伤的蒋介石突出重围,连夜奔袭160里找来援军。这份救命之恩让蒋介石对他格外器重,甚至想拉拢他做心腹。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陈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31年陈赓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面对昔日救命恩人的威逼利诱,陈赓拿起一张报纸遮住脸,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这种硬骨头的做法让蒋介石既恼火又无奈,毕竟当年的救命之恩摆在那里,最终只能把陈赓释放。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赓率领八路军129师386旅奔赴前线。1937年10月,他指挥部队夜袭山西阳明堡机场,一战炸毁日军战机24架,这个战果在八路军历史上前所未有。解放战争期间,陈赓兵团更是所向披靡,在1947年的晋南战役中,他们仅用23天就连续攻克17座县城,歼灭敌军4万多人。战场上的陈赓是个铁血硬汉,私下里却是个十足的幽默大师。就连向来严肃的彭德怀都经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有一次开作战会议,彭德怀正全神贯注地研究地图,陈赓悄悄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彭总这表情,比母鸡下蛋还专注呢!”这话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会场都憋不住笑了。新中国成立后,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952年,他又受命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哈军工。这所学校培养出了无数国防科技精英,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陈赓经常说,培养人才比打仗还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1961年陈赓因病去世,享年58岁,他的一生从黄埔军校的青年学子到开国大将,从抗日战场的指挥官到军事院校的创办者,每个阶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年被他“欺骗”的李聚奎后来也成了上将。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陈赓去世,李聚奎还经常跟人说起当年被陈赓“坑”的那件事,每次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真正的英雄不一定要板着脸装深沉,能在血雨腥风中保持乐观,在艰难岁月里不失幽默,这或许才是最难得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