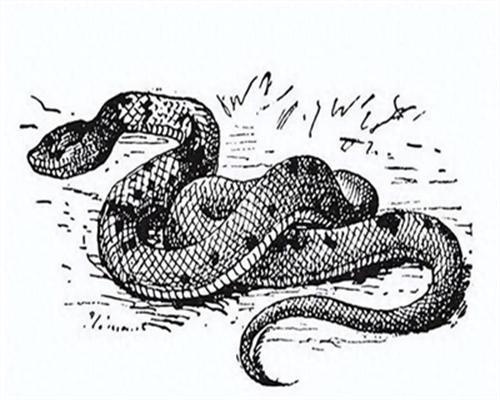"王二,后厨那扇猪肉可甭动啊!"李婶拎着菜刀从蒸笼边探出脑袋,围裙上油渍泛着光,"这是给新娘子回门宴备的。"
我蹲在土灶前扒拉柴火,火星子噼啪炸响。"知道知道,这扇五花肉金贵着呢。"话没说完,院外突然传来梆子声。这荒郊野岭的张家老宅,离最近镇子都得走三里黄泥路,哪来的叫花子?
"行行好,赏口吃的……"破锣嗓子扎着耳朵。我起身时蹭了满手锅底灰,掀开门帘就瞧见个佝偻身影杵在日头底下。这老乞丐真够瘆人,左脸烂着个窟窿,苍蝇在腐肉上打转,右手攥的破碗缺了半边沿。
"李婶,把那扇猪肉……"
"作死啊!"李婶抄起烧火棍就往外撵,"今儿是张家少爷娶亲第三天,冲撞喜气你担待得起?"
我拦住她:"就切一小块,灶王爷总不会跟叫花子计较。"说着割了指甲盖大一块五花肉扔进破碗。老乞丐突然直起腰,烂脸凑近门缝:"后生,天黑前快走,别问为啥!"
张家老宅是座三进四合院,灰墙皮簌簌往下掉渣。我蹲在院角啃馒头,后脊梁直冒冷汗。这宅子邪性,打从晌午进了门,眼皮就跳个没完。李婶说这是张员外给独苗办喜事,可满院子红绸缎都褪了色,窗花边角卷着,跟从陈年棺材里扒出来似的。
"王二!搭把手!"赵师傅在灶台前吆喝。这老师傅是镇上"一把刀",可今儿切肉丝的手直抖,刀刃险些削着手指头。我瞥见供桌上摆着两盏白灯笼,烛泪凝成血红疙瘩,正对着灶膛里的火光。
"赵师傅,喜宴用白灯笼?"
"嗐,张家老太太信佛,说红白双喜冲煞。"他抹把汗,刀刃在磨刀石上蹭出龙吟声,"昨儿新娘子过门时,轿帘刮着门框,硬是给撕了半截。"
我后槽牙发酸。新娘子过门撕轿帘,这在乡下是晦气兆头。可张家非但不恼,反倒连夜给门柱贴满黄符。晌午开席时,我看见新娘子凤冠霞帔坐在主位,红盖头下露出半截青白下巴,筷子尖沾着胭脂印往供桌方向比划。
"新郎官呢?"我装作添柴火,凑近赵师傅耳语。
他脸色唰地白了,刀锋在萝卜上划出歪扭印子:"在……在西厢房歇着。"

日头西斜时,乞丐的警告又在耳边炸响。我端着木盆去井台打水,经过西厢房听见里头传来咳嗽声,像破风箱漏气。门缝里飘出股子腐臭味,混着药渣子味直往鼻子里钻。
"劳驾,借个火。"
我激灵一下,回头看见个穿长衫的账房先生,镜片蒙着层白雾。他掏出个铜烟锅,烟袋锅里填的烟丝泛着暗红色。我划火柴时瞟见账本边角,密密麻麻记着"朱砂三钱""符纸五十"的账目。
"小哥面生。"账房吐口烟圈,烟雾拢着他半边脸,"这宅子……住得惯?"
井绳突然断了,木桶"咚"地砸进井里。我趴在井沿往下看,月光映着水面,恍惚瞧见张青白面孔一闪而过。再抬头时,账房早没影了,只剩烟灰簌簌落在青石板上。
掌灯时分,帮厨的婆子们突然炸开了锅。蒸笼里本该雪白的喜馍馍,全染成了血红色。李婶哆嗦着掰开馍馍,枣泥馅里嵌着半截指甲盖。
"造孽啊!"赵师傅抄起炒勺就要砸蒸笼,"这面是头晌午新发的,谁使的坏?"
我盯着灶台缝里漏出的朱砂粉,想起账房先生烟袋锅里的暗红烟丝。后厨门帘"哗啦"作响,穿堂风卷着纸钱灰扑在脸上,供桌的白灯笼不知何时点着了,烛影在墙上投出扭曲人影。
"新郎官吐了!"
前院传来丫鬟尖叫。我挤过人群钻进西厢房,酸腐味熏得人直翻白眼。雕花拔步床上躺着个穿红袍的年轻人,嘴唇紫得跟熟透的桑葚。被褥浸着大片黑渍,床腿刻着道符,朱砂顺着纹路往下淌,像干涸的血泪。
"都让让!"张员外拄着拐杖闯进来,金丝眼镜歪在鼻梁上,"请神婆子来,快!"
神婆裹着靛蓝头巾,铜铃摇得震天响。她突然指着床底尖叫:"孽障在那儿!"两个家丁七手八脚掀开床板,露出个黑陶罐,封口贴着黄符,罐身用朱砂画着狰狞鬼面。
"起尸了!"神婆突然掐住自己脖子,翻着白眼嚷嚷,"新娘子压不住煞,快抬到祠堂……"
话音未落,西厢房门窗"砰"地紧闭。我后背撞上供桌,白灯笼里的蜡烛"噼啪"炸开,整间屋子陷入黑暗。黑暗中响起指甲刮擦木头的声响,床板吱呀摇晃,紫袍新郎发出野兽般的呜咽。
"王二!"李婶的尖叫带着哭腔,"门……门缝里有眼睛!"

我摸出火折子往门缝凑,瞳孔猛地收缩。十几只充血的眼球贴在门板上,瞳孔收缩成针尖大小。窗纸"哗啦"裂开,月光照亮床尾,陶罐不知何时被打翻,黑血顺着砖缝往供桌流,在门槛前汇成诡异的符咒图案。
"都别动!"神婆突然厉声喝道,"等鸡鸣三声,煞气自散!"
可张家老宅方圆十里连个鸡窝都没有。我贴着墙根挪到灶台,摸出藏在围裙里的五花肉。这是晌午偷偷留下的,油纸包早被汗浸透了。乞丐的警告像根刺扎在心里,可眼下连大门都出不去——院墙外飘着十几盏白灯笼,纸糊的灯笼上分明画着新娘子的面容。
后半夜起了雾,潮气裹着腐臭味往屋里钻。新郎的喉咙里发出咯咯怪响,像被掐住脖子的老鸹。神婆瘫在墙角念咒,铜铃早不知丢哪去了。供桌上的白灯笼突然腾起幽蓝火苗,烛泪化作血珠滴在符纸上。
"王二!"赵师傅突然扯我袖子,"看供桌底下!"
我哆嗦着举起火折子,供桌下露出半截绣鞋。红缎面上沾着泥,鞋尖缀着的珍珠掉了两颗。这分明是新娘子的婚鞋,可成亲当日就该藏在床底的。更诡异的是,鞋印一路从供桌延伸到西厢房门槛,湿漉漉的像是沾着露水。
"新郎官睁眼了!"
紫袍新郎突然直挺挺坐起,眼白翻着,嘴角咧到耳根。他喉咙里发出女人的尖笑,十指如钩朝神婆抓去。张员外吓得栽倒在地,金丝眼镜甩出老远。
"用鸡血!"神婆突然尖叫,"泼他脸上!"
李婶端着铜盆冲过来,腥臭的鸡血兜头浇下。新郎浑身抽搐着栽倒,床板轰然坍塌。烟尘中,我看见床下有具枯骨,穿着残破的嫁衣,头骨上插着银簪。
"是张家少奶奶!"赵师傅牙齿打颤,"三年前上吊那个!"
神婆突然扯下头巾,露出光头上刺着的符咒:"孽障,还不现形!"她掏出把桃木剑,剑尖沾着朱砂往枯骨天灵盖刺去。枯骨突然炸开,蛆虫混着黑血溅了满墙。
"天亮前封棺!"张员外爬起身,金丝眼镜斜挂在耳边,"把新娘子……不,把少奶奶抬去祠堂!"
我趁机溜到后院,墙根狗洞半掩着杂草。乞丐的警告像催命符,可刚摸到洞沿,就听见墙外传来女人哭灵声。雾蒙蒙的月光下,我看见送亲的队伍从坟地飘来,纸钱撒了满地,最前头的花轿帘子缝里,露出半截青白手指。
"王二!"李婶举着灯笼追到后院,"新郎官咽气了!"

我僵在原地,灯笼光晕里,张员外正指挥家丁抬棺材。棺材板缝渗出黑血,滴在青石板上发出滋滋声。更可怕的是,棺材里传来指甲抓挠声,一声比一声近。
"快回屋!"李婶扯我胳膊,"神婆说要摆七星阵镇邪!"
前院供桌被挪到天井,七盏油灯摆成北斗状。神婆披头散发在灯阵里蹦跳,嘴里念叨着听不懂的咒语。我突然发现,灯阵中央摆着那个黑陶罐,罐口正对着西厢房门槛。
"子时三刻,百鬼夜行!"神婆突然扯开嗓门,"张家列祖列宗在上,今以新妇魂魄为祭……"
话音未落,西厢房传来玻璃碎裂声。我看见新娘子站在二楼雕花窗前,红盖头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突然抬起右手,指尖沾着血在窗纸上画符。月光照亮她青白下巴,那分明是枯骨的模样!
"快拦住她!"张员外挥舞拐杖砸窗,"把符纸都贴上!"
家丁们举着黄符往楼上冲,可刚碰到楼梯扶手就惨叫摔倒。我借着混乱溜到供桌旁,火折子照亮陶罐底部——刻着个生辰八字,正是三年前吊死的少奶奶!
"王二!"赵师傅突然从厨房钻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面缸里……面缸里长出头发了!"
我冲进厨房,月光从瓦缝漏进来,照得面缸里白花花一片。那些面条似的头发正往上冒,带着血腥气。更骇人的是,头发间缠着半截指甲,涂着猩红的丹蔻。
"砰!"
后院突然传来巨响。我抄起菜刀冲出厨房,正撞见棺材板被掀翻在地,紫袍新郎的尸首不翼而飞。张员外瘫在血泊里,金丝眼镜沾满泥,指着祠堂方向哆嗦:"在……在祠堂!"
祠堂门大开着,供桌上的祖宗牌位全倒了。灵位后露出暗格,里头摆着个描金妆奁。妆奁盖子上积着厚灰,铜锁却锃亮如新。张员外刚伸手去摸,暗格里突然窜出团黑气,混着腐臭味直扑面门。
"别动!"神婆举着桃木剑冲进来,"这是养尸棺!"
妆奁突然自动弹开,里头躺着个女婴干尸,肚脐眼插着银簪。张员外见状惨叫一声,竟昏死过去。神婆扯开女婴衣襟,肚皮上赫然刺着生辰八字——正是张家独苗的!
"借尸还魂!"神婆的脸在烛光下扭曲,"张员外,您当年造了什么孽?"

我突然想起乞丐的警告,浑身汗毛直竖。灶膛里的火不知何又着了,映得墙上影子乱晃。供桌上的白灯笼突然齐齐熄灭,整个祠堂陷入黑暗。黑暗中响起婴儿的啼哭,混着女人的尖笑,在梁柱间回荡。
"王二,快看那女婴!"赵师傅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举起火折子,干尸的眼皮突然动了。它咧开没牙的嘴,喉咙里发出成年女子的声音:"好弟弟,你来娶姐姐了……"
祠堂外传来公鸡打鸣,第一声刚起,女婴干尸突然炸开。蛆虫混着黑血溅了满墙,供桌上的祖宗牌位纷纷爆裂。张员外突然抽搐着坐起,金丝眼镜映着绿光,嘴角咧到耳根:"你们都得给阿翠陪葬!"
我转身要跑,却被李婶抱住腿。她满脸是血,眼珠子上翻:"新郎官在井里……在井里……"
后院的井台泛着诡异水光。我探头往下看,月光照亮水面,紫袍新郎的尸首泡在井里,十指如钩扒着井壁。更可怕的是,他脸上长着女人的五官,嘴角挂着青白獠牙。
"王二!"赵师傅举着菜刀冲过来,"神婆……神婆变成黄鼠狼了!"
祠堂里传来家具碎裂声,神婆的靛蓝头巾掉在地上,露出毛茸茸的兽头。它眼睛泛着红光,爪子在供桌上抓出五道血痕:"张家欠我的命,该还了!"
张员外突然狂笑着扑向黄鼠狼,两人滚作一团。我趁机冲向大门,可门缝里那些充血的眼球突然活过来,眼球上布满血丝,瞳孔收缩成针尖。
"天亮前快走!"
乞丐的警告在耳边炸响。我摸出藏在怀里的五花肉,狠狠砸向门缝。腐臭味扑面而来,眼球们突然爆开,溅出黑血。我冲进晨雾中,听见身后传来张员外的惨叫:"阿翠!别抓我脸!"
跑出百步开外,回头望去,张家老宅被浓雾吞没。那些白灯笼在雾中漂浮,像送葬的纸船。我踉跄着扑进草丛,怀里的五花肉早被汗浸透了。乞丐的烂脸突然在脑海浮现,他缺了牙的嘴一张一合:"后生,你印堂发黑……"
晨鸡报晓第三声时,我摸到裤兜里黏糊糊的东西。掏出一看,是半截青白指甲,还带着胭脂红。我贴着墙根儿挪到西厢房窗根儿底下,就听见里头"咔嚓"一声,像是有人把啥玩意儿掰折了。月亮地儿里影影绰绰的,窗纸破了个窟窿眼,我凑近了一瞅——
二婶正蹲在供桌跟前,手里攥着半截蜡烛。那蜡烛头子冒着青烟儿,火星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她突然把蜡烛往供桌上的相框上一戳,相框里老爷子那张黑白照片"刺啦"就着了。火苗蹿起来老高,我吓得差点儿叫出声。
"您这是干嘛啊?"我推门就进去了。二婶猛回头,脸上白一块儿红一块儿的,跟唱戏的大花脸似的。她手里还攥着个铜香炉,咣当就砸地上了。

"小兔崽子大晚上不睡觉,跑这儿装神弄鬼!"二婶嗓门儿劈了似的,"这老东西天天在相框里瞪着我,我烧了他清净!"
我瞅着供桌上那堆灰烬直发毛,老爷子照片早烧成个黑窟窿了。二婶突然凑过来,身上那股子檀香味儿混着香火味儿直呛鼻子:"你看见我屋里的玉扳指没?"
我心说您这转移话题够生硬的啊,嘴上打着哈哈:"我哪敢翻您屋啊,二婶儿您这不是寒碜我嘛。"
"甭跟我这儿耍贫嘴。"她手指头差点戳我脑门儿上,"今儿晌午就你进过我屋,那扳指儿是老爷子留下的,丢了我跟你没完!"
我转身要走,她突然拽住我胳膊:"等会儿!"我后脖颈子直冒凉风,就听见她压低声音:"你瞧见西墙根儿那堆砖没有?"
我顺着她手指头看过去,西墙底下码着几摞旧砖,看着跟胡同里拆房剩下的废料似的。"那砖头有什么问题?"
二婶突然咧嘴一笑,露出镶的金牙:"你搬开第三摞,从下往上数第七块砖,里头有东西。"说完推了我一把,我差点儿撞供桌上。
我摸黑走到西墙根儿,砖头缝儿里全是蜘蛛网。数到第七块砖时,手指头摸到个凹进去的小窟窿。我心怦怦跳,指甲盖儿抠进去一掰——
砖缝里掉出个油纸包,包得四四方方的。打开一看,是个玉扳指儿,翠绿翠绿的,里头还裹着张纸条,写着"三更天,槐树下"。
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二婶打哪儿知道的这个?外头突然响起梆子声,打更的喊"亥时三刻",我抬头瞅见月亮正挂在槐树梢上。
"二婶儿,这纸条……"我揣着玉扳指儿往回走,发现她人已经没影儿了。供桌上的蜡烛头子还在冒烟儿,相框里那团黑灰突然扑棱一下,像是有东西飞出来了。
我撒丫子就往院里跑,槐树底下黑黢黢的。刚要喊人,后脖颈子突然挨了一下,眼前金星乱冒。昏过去前恍惚看见二婶举着铜香炉,金牙在月光底下闪着光。
再睁眼时,嘴里一股子血腥味儿。手被反绑着,眼前是间破屋子,墙上挂满黄符,供桌上摆着个黑坛子,插着三炷香。二婶坐在太师椅上,正拿簪子剔牙呢。
"醒啦?"她咯咯一笑,"知道为什么选你么?你爸当年也是这么绑我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二十年前我爸失踪那事儿,胡同里都说他卷了厂里的钱跑了。二婶突然站起来,掀开墙上的黄布帘子——

里头是间密室,摆着个水晶棺材。棺材里头躺着的人,穿的是我爷爷那身中山装!我吓得直往后缩,二婶拽着我耳朵凑到棺材跟前:"你爷爷当年贪了厂里的宝贝,藏在这胡同里。你爸找着之后想独吞,结果……"
她突然掐住我脖子,金簪子抵着我喉咙:"那玉扳指儿是钥匙,开槐树底下的机关。你爷爷变成活尸守着宝贝,今儿个该你小子下去陪他了!"
外头突然响起雷声,棺材盖儿开始渗水。二婶拽着我就往槐树底下走,树根底下果然有个洞口,黑咕隆咚的。她拿玉扳指儿在洞口一转,石门轰隆隆就开了。
"下去!"她一脚踹我后腰。我顺着石阶往下滚,听见她在洞口喊:"你爷爷等着你呢,小兔崽子!"石门轰地关上,我摸着黑往前爬,手底下全是黏糊糊的东西,像是蜘蛛网。
突然,前头亮起绿光,两盏灯笼似的。我凑近了一看——是俩活尸,穿着清朝官服,脸上白森森的。他们手里捧着个铜匣子,里头装着个玉玺,刻着"受命于天"。
我后脖颈子汗都下来了,转身想跑,发现石门早封死了。活尸突然朝我扑来,我抄起地上的铜烛台就砸。这时候,头顶石缝里突然掉下个火把,有人喊:"小兔崽子接着!"
我接住火把一照,是二婶!她衣裳撕得稀烂,脸上全是血道子。"快拿玉玺!"她喊道。活尸已经扑到跟前了,我抄起玉玺就往石门上砸。
玉玺裂开的瞬间,石门轰然洞开。二婶拽着我就往外跑,后头活尸嗷嗷叫着追。跑到胡同口时,打更的突然抡起梆子就砸,活尸怕火光,滋啦滋啦往后缩。
"二十年啦!"二婶瘫坐在地上,金簪子早不知丢哪儿去了,"你爷爷当年贪了厂里的玉玺,藏在槐树底下。你爸找着之后想卖钱,结果让活尸咬死了。那玉扳指儿是钥匙,我藏了这么多年……"
我瞅瞅手里裂开的玉玺,突然明白过来:"您当年是厂里的会计?"
二婶愣了一下,突然咧嘴乐了:"小兔崽子真聪明。当年你爷爷贪了玉玺,我跟着倒霉。后来你爸找着玉玺想卖钱,结果被活尸弄死。我守着这个秘密,就等今天……"
她突然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个黑布包:"这是当年你爷爷贪的其他宝贝,你拿着走吧。胡同里要变天了,记住别回头!"
我接过布包刚要跑,就听见胡同深处传来敲锣声,阴森森的。二婶突然把我推进旁边的公共厕所,自己反手把门锁了。
"二婶儿!"我砸着门喊。里头传来她唱戏的声音,尖着嗓子:"海岛冰轮初转腾——"接着是玻璃碎的声音,还有活尸的嘶吼。
我揣着布包往胡同外跑,后头火光大作。拐过街角时,回头看见整个胡同烧红了半边天,二婶的戏腔混在火海里,飘得老远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