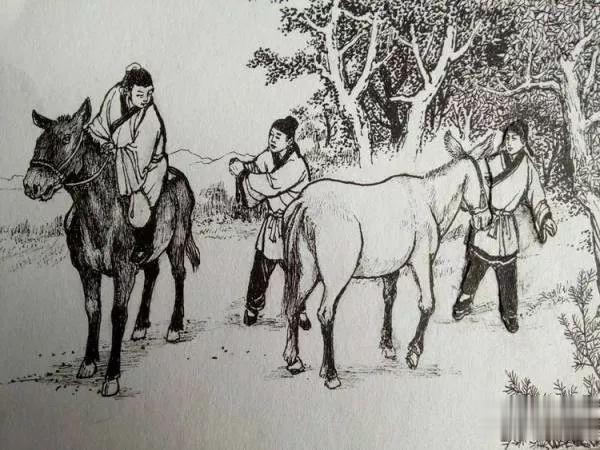雷雨夜惊魂
七月的雷雨说下就下,黑云彩压着永定河两岸的柳树梢儿。张寡妇抱着发高烧的狗子往村西头破庙冲,泥点子甩得裤脚子噼啪响。这庙里供的泥胎判官早让红卫兵砸了,就剩半截歪脖子槐树支棱着,树底下新起的坟包还冒着新土味儿。
"让让!让让!"张寡妇的布鞋刚踏进庙门,冷不丁让团花里胡哨的物什绊了个趔趄。定睛瞅去,碑石缝里盘着条两尺长的花蛇,红黑鳞片油亮亮地反光,三角脑袋支棱着信子,活脱脱戏文里白娘子现原形那架势。
"哎呦我的亲娘四舅奶奶!"外头避雨的刘二麻子怪叫,"这不老张家那个短命鬼的坟茔吗?合着棺材板子压不住,诈尸变蛇精了?"
这话音未落,花蛇猛地蹿起半尺高,刘二麻子手里的旱烟袋"当啷"掉地。众人正乱作一团,破庙外头忽然传来铜铃铛响。个穿藏青长衫的老头拄着乌木拐杖,后头跟着个眉清目秀的小后生,两人浑身淋得透湿,偏生那铜铃铛响得脆生。
"列位,借个火。"老头操着京片子,从怀里掏出个青铜罗盘,火苗儿一蹿,那罗盘里的红针竟自个儿转将起来。老头眯眼盯着坟头:"往下挖一尺二寸,见分晓。"
刘二麻子刚要啐唾沫,冷不防让后生用折扇抵住喉咙。这扇子不知什么木头做的,泛着青幽幽的光,扇骨上刻着《钟馗捉鬼图》,活灵活现。刘二麻子喉头咕嘟一声,竟真个抄起铁锹刨起来。
头几锹下去,新土混着雨水簌簌地落。挖到八寸光景,铁锹突然"当"地磕着硬物。刘二麻子抹把脸上的雨水,就着闪电往坑里瞅——半截黑坛子露着狰狞的釉面,坛口贴着褪色的黄符,朱砂画的符咒早被雨水洇成个血葫芦。
"别动!"老头喝住众人,从袖中抖出段红绳,系着八枚铜钱,"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铜钱落地,竟摆出个八卦阵。花蛇不知何时游到坛子边,拿尾巴尖儿轻轻扫那黄符,活像绣娘描花样。
小后生突然蹲下身,指尖沾了泥在坛身上抹。众人借着闪电瞧见,那泥痕下头竟浮出张人脸——眉眼像极了张寡妇早夭的闺女翠芬!

"造孽哟!"张寡妇捶胸顿足,"去年冬月这丫头得痨病,刘二麻子非说冲喜能治病,硬逼着她嫁给他家那个傻儿子。成亲那夜……"她话没说完,刘二麻子突然暴起,抡着铁锹往坛子上砸。
"让你这老棺材瓤子多嘴!"刘二麻子眼珠子通红,"当夜这小蹄子用剪子捅了傻柱,自己吊死在房梁上!老子怕吃官司,才把她埋在这荒坟……"
雷声炸响,花蛇突然昂首吐信,"嗖"地钻进坛口。老头疾步上前,红绳早缠住刘二麻子的脚踝,铜钱阵里迸出八道金光。众人再睁眼时,那黑坛子竟裂成八瓣,里头滚出个玉镯儿,镯心刻着"永镇冤魂"四个小字。
"这是前朝张天师镇妖用的法器。"老头抚须长叹,"当年翠芬咽气时含冤,三魂七魄被锁在这镯里。花蛇本是庙里修炼的灵物,嗅到怨气就过来守着。"他转头问张寡妇:"狗子可是七月十五子夜生的?"
张寡妇浑身一激灵:"您老咋知道?"
"阴阳眼,能看见脏东西。"老头指指小后生,"这是我徒弟清虚,当年你闺女的魂魄不肯投胎,附在这蛇身上修炼。今儿个雷雨交加,正是她借阳气重生的时候。"
刘二麻子早吓尿了裤子,跪在泥水里磕头如捣蒜。清虚却突然变色,折扇直指槐树:"师父,那枝桠上吊着个红肚兜!"
众人抬头望去,老槐树最高的枝桠上,果然飘着件褪色的红布兜,正是翠芬当年上吊时穿的。花蛇不知何时游到树根下,尾巴卷着个褪色的布老虎——那是翠芬小时候的玩具。
"挖!"老头突然厉喝,"把树根下的土全翻开!"

刘二麻子刚要耍滑,冷不防手腕子让红绳勒出血印子。铁锹掘地三尺,竟挖出个油纸包,里头裹着三缕青丝,用红头绳系着。张寡妇一见就哭了:"这是翠芬的胎发,满月时我亲手埋的……"
雨越下越大,破庙里飘进股子香火气。老头从怀里掏出个黄杨木匣,里头供着尊三尺高的白玉貔貅,貔貅背上驮着部线装书,书脊上四个泥金字:聊斋志异。
"列位,这貔貅是当年蒲松龄老先生镇妖用的。"老头翻开书页,里头夹着张泛黄的符纸,"翠芬的冤魂附在蛇身,今儿个借雷劫要复仇。刘二麻子,你作恶多端,可知这槐树底下埋着啥?"
刘二麻子刚要摇头,清虚的折扇"啪"地展开,扇面上钟馗突然睁眼,手指直指他眉心:"你爹当年修河堤贪墨公款,用童男童女祭河神,那七个孩子的冤魂全锁在槐树根里!"
外头雨幕中,突然传来孩子的嬉笑声。众人浑身汗毛直竖,却见那老槐树裂开了道缝,七只惨白的小手扒着树皮,唱着走调的童谣:"槐树根,锁冤魂,雷雨夜,来勾人……"
四)纸钱引魂
老柳树的枝子让夜风刮得哗啦响,树底下摆着三牲祭品,黄表纸烧得青烟缭绕。张寡妇抱着狗子缩在庙门口,清虚用朱砂在槐树身上画符,那七个惨白的小手印渐渐淡去。刘二麻子早瘫成烂泥,裤裆里洇出老大一片水渍。
"列位!"老头突然高声道,"今儿个这出《雷劈恶人》,可得演全乎了!"说话间,他掏出那尊白玉貔貅,往槐树底下这么一搁。说也怪,那貔貅的眼睛竟泛出绿光,大嘴一张,把刘二麻子"咕咚"吞进肚里。
众人正要惊呼,老头摆摆手:"莫慌,这吞的是他三魂七魄里的恶念。当年他爹用童男童女祭河神,那七个冤魂附在槐树上,如今该超度了。"说话间,清虚展开折扇,扇面上钟馗挥舞宝剑,槐树周围的空气突然泛起涟漪,七个孩子的虚影手拉着手,唱着童谣往西边去了。
雨渐渐停了,花蛇从坛子里游出来,在翠芬的坟包上盘成个太极图。张寡妇刚要磕头,冷不防那蛇突然开口:"娘,狗子命中该有劫数,您得往西走三里,找个戴铜铃铛的哑巴……"

这厢故事刚了,那厢永定河边的背尸匠王三麻子正犯愁。月黑风高夜,他刚把一具客死异乡的老尸背到渡口,冷不丁河对岸飘来个穿红袄的闺女。那闺女脸白得跟宣纸似的,嘴唇红得瘆人,怀里抱着个褪色的布老虎。
"大叔,能背我过河不?"闺女开口,声音脆生生地,"我爹在河西头等着呢。"
王三麻子心里直犯嘀咕:这年月兵荒马乱,哪有大姑娘半夜独自赶路的?再一瞅那布老虎,眼熟得很——前日张寡妇抱着狗子来求平安符,狗子手里攥着的就是这个!
"闺女,这渡口邪性……"王三麻子话没说完,冷不防脚脖子让冰凉的小手抓住了。一低头,那闺女不知啥时候飘到了跟前,红袄上沾着河边的水草,布老虎眼睛竟渗出血珠。
"求您了。"闺女突然变了脸色,眼眶子淌出黑水,"我爹是背尸匠,三年前在这渡口让水鬼勾了魂。您要是不背我过去……"她话没说完,王三麻子后背突然窜起股子阴风,怀里的铜铃铛"当当"乱响。
王三麻子到底是吃这碗饭的,咬咬牙把闺女背起来。可怪的是,这闺女轻得跟纸人似的,过河时脚底打漂,水草缠住脚脖子直往河里拽。好容易上了岸,闺女突然在他耳边吹气:"大叔,您家祖传的《背尸诀》里,可有镇水鬼的法子?"
王三麻子心里"咯噔"一下,这《背尸诀》是爷爷临终前传的,里头确有段"镇三魂"的咒语。可等他回头,闺女早没影了,地上就留个湿漉漉的脚印,形状像极了蛇蜕。
打那夜起,王三麻子就犯了邪。半夜总梦见红袄闺女在河对岸哭,布老虎眼睛滴溜溜转。更邪的是,每回做梦,他枕头底下就多出张黄纸,上头用血画着个蛇盘太极图。

"爷爷,爷爷!"王三麻子跪在祠堂里,供桌上摆着爷爷留下的铜烟袋和《背尸诀》手抄本。烟袋锅里的烟灰突然自己燃起来,青烟在半空聚成个人脸模样,正是那红袄闺女!
"三麻子,你摊上大事了。"爷爷的声音从虚无里传来,"那闺女是替死鬼,当年她爹背尸过河,让水鬼换了命。如今她阳寿未尽,得找个背尸匠替她……"
王三麻子吓得魂飞魄散,正要给爷爷磕头,冷不防门外传来铜铃铛响。张寡妇抱着狗子闯进来,狗子怀里还抱着那个布老虎!
"王大哥!"张寡妇上气不接下气,"前夜雷雨,狗子突然开口说话,说让找戴铜铃铛的哑巴……"她话没说完,狗子突然伸手抓向王三麻子:"背我过河!"
王三麻子定睛一瞅,狗子瞳孔泛绿,嘴角挂着黑水——这分明是撞客了!再一瞅那布老虎,眼睛里的血珠正往下滴,在地上汇成个蛇形。
"爷爷,爷爷!"王三麻子抖如筛糠,"当年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烟袋锅里的青烟突然凝成个画面:月黑风高夜,老背尸匠背着具女尸过河。刚到河心,女尸突然睁眼,指甲暴长,老背尸匠的铜铃铛"当当"乱响,可女尸早扑上来……
"造孽哟!"爷爷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女尸是被人活钉进棺材的,怨气化成了水鬼。你爹用《背尸诀》镇住她三魂,自己却被抽了生气……"
王三麻子浑身冷汗直冒,再一瞅狗子,那孩子突然咧嘴笑,露出满口黑牙:"背我过河,背我过河……"

"闭嘴!"张寡妇突然抄起供桌上的鸡毛掸子,作势要打。狗子却"咯咯"笑着飘到房梁上,倒挂着冲王三麻子吐舌头。
"王大哥,你得救我狗子!"张寡妇哭得梨花带雨,"前夜雷雨,有个穿长衫的老头托梦,说狗子命中该有劫数,非得找背尸匠……"
王三麻子正犯愁,冷不防怀里的《背尸诀》突然自己翻开,正翻到"镇三魂"那页。泛黄的纸页上,赫然画着个蛇盘太极图,图底下有行小字:"替死鬼缠身,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有了!"王三麻子突然眼睛发亮,"张妹子,你速去河西头找那个戴铜铃铛的哑巴,问清楚狗子他爹的生辰八字。狗子,你下来,叔给你糖吃……"
狗子却突然怪叫一声,从房梁上直挺挺摔下来。王三麻子眼疾手快,掏出随身带的糯米撒过去。糯米落地即燃,火苗窜起三尺高,狗子身上的黑气"滋滋"作响。
正当众人乱作一团,门外突然传来铜铃铛响。清虚扶着老头踱进来,老头怀里抱着那个白玉貔貅,貔貅背上驮着的《聊斋志异》泛着青光。
"列位,这出《替死鬼》演到头了。"老头冲王三麻子作揖,"当年你爹镇住的水鬼,正是张寡妇家闺女的冤魂。那闺女阳寿未尽,被水鬼抽了生气,如今附在狗子身上……"
王三麻子如梦初醒,怪道狗子生得眉眼像极了翠芬!再一瞅狗子脖颈后头,果然有块胎记,形状像极了蛇盘太极图。
"爷爷,爷爷!"王三麻子跪在祠堂前,"当年我爹用《背尸诀》镇三魂,如今该当如何?"

烟袋锅里的青烟突然聚成个蛇形,绕着狗子转了三圈。王三麻子突然福至心灵,掏出随身带的朱砂笔,蘸着狗血在狗子额头画符。那符刚画完,狗子突然睁眼,黑漆漆的瞳孔里泛出绿光。
"王三麻子,背我过河!"狗子的声音突然变成那红袄闺女的,"当年你爹欠我的,今儿个该还了!"
永定河面突然泛起白雾,雾气里飘出艘乌篷船。艄公戴着斗笠,脸藏在阴影里,船头挂着串铜铃铛,"叮叮当当"响得瘆人。
"上船吧。"艄公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刀,"阳间有阳间的规矩,阴间有阴间的法度。"
王三麻子刚要迈步,冷不防张寡妇拦住他:"不能上!当年我闺女就是让这船带走的!"
"造孽哟!"老头突然长叹,"这船是渡魂船,专门接引横死的冤魂。当年翠芬被刘二麻子逼婚,吊死在房梁上,三魂七魄被锁在槐树里。如今她借狗子重生,得回阴间销案……"
王三麻子听得浑身发凉,再一瞅狗子,那孩子突然冲他笑,露出满口白牙:"大叔,背我过河。"
"背!"王三麻子一咬牙,抄起狗子扛在肩上。可怪的是,狗子这回沉甸甸地,压得他脊梁骨都快断了。刚走到河边,狗子突然在他耳边吹气:"大叔,您家祖传的《背尸诀》,该传给我爹了……"
乌篷船渐渐飘远,河面泛起层层涟漪。王三麻子站在岸边,怀里抱着狗子留下的布老虎。老头突然掏出那尊白玉貔貅,往河里这么一掷:"列位,这貔貅该回蒲松龄老先生手里了。"

清虚却突然变色,折扇直指河对岸:"师父,那碑文……"
众人抬头望去,河对岸不知何时竖起块青石碑,碑文上刻着八个朱砂大字:"善恶有报,天道轮回"。碑脚下盘着条花蛇,红黑鳞片在月光下泛着幽光。
"翠芬的冤魂超度了。"老头抚须长叹,"刘二麻子吞了他的恶念,那七个孩子的冤魂也散了。王三麻子,你今儿个背的不是狗子,是段因果。"
王三麻子刚要开口,冷不防怀里的布老虎突然"喵"地叫了。低头一瞅,那老虎眼睛竟泛出绿光,背上用金线绣着行小字:"背尸匠的铜铃铛,镇得住冤魂,镇不住人心。"
打那夜起,永定河边多了段传说。说是有那心地不善的,半夜能听见铜铃铛响,看见穿红袄的闺女在渡口徘徊。可心地善良的,却能瞧见花蛇在碑文上晒太阳,尾巴尖儿扫着"善恶有报"四个大字。
王三麻子再没做过噩梦,只是把《背尸诀》手抄本供在祠堂里,每天三炷香。张寡妇的狗子病好了,只是脖颈后头多了块蛇形胎记,见着穿长衫的老头就笑。
老头和清虚再没出现过,只是那白玉貔貅偶尔在河里泛出青光,像是在镇守着什么。河对岸的青石碑越发光润,碑文上的朱砂字字如血,提醒着过往行人: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这故事里,花蛇是冤魂的执念,背尸匠是因果的纽带,渡魂船是阴阳的界限。看似讲鬼说怪,实则是说人心善恶。刘二麻子作恶多端,终被恶念反噬;王三麻子心怀慈悲,终得善果。翠芬的冤魂得以超度,狗子的劫难化为新生,都在印证着"善恶有报"的老理儿。

民间故事里的神神鬼鬼,不过是把人心里的贪嗔痴化成了形。那青石碑上的朱砂字,何尝不是刻在每个人心头的警戒?世事如棋,因果循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话搁今儿个也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