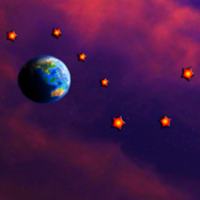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杨花

周六我和先生都晚回,母亲担心我两个儿子吃外卖,便在家炒了两个菜,坐了公交送过来。孩子们吃完饭,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外婆不仅送了菜,还送了个“古董”来。一问才知道,装菜的那个碗,碗底刻着母亲的名字,还是她未嫁时外公送给她的“礼物”,少说也快七十年了。
我小时候就对这个“刻着名字的碗”有很深的印象。母亲告诉我,她的小时候,是物质特别匮乏的时代,和村里大多数家庭一样,外公家里也特别穷,虽然家中有基本的炊具,但家里的碗却几乎没有装满过,更别说装什么好吃的、有营养的食物了。而碗底刻上名字,是每家每户都会做的事,因为邻里之间偶尔会有相互间的“碗上往来”,谁家揭不开锅了,邻居家会找个借口,叫自家孩子偷偷送碗吃的过去,而接受雪中送炭的这户人家中的孩子,一定会在如获至宝地吃完这碗食物吃完后,把碗洗得干干净净送回去,这个刻着名字的碗就不会混淆而物归原主了。在这无声的一送一还之中,这只碗装载的,是邻里乡亲相亲相爱、友善互助的浓浓乡情。
母亲是外公唯一的女儿,外公对她格外疼爱,总希望能给她留点啥,但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里,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沉厚寡言的外公于是在家里的每个碗上都刻上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让她觉得在这个家里能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财产”,哪怕只是普通得不值一提的、总是无法令她的宝贝女儿能填饱肚子的碗。它不仅是外公唯一能送给女儿的“礼物”,也饱含着外公对母亲的祝愿,他希望母亲以后的生活能家有余粮、衣食无忧。
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也带上了外公送给她的珍贵礼物。而我小时候印象中的这个碗,已经有着不同的轨迹和意义。我印象里的童年,虽然没有丰盛的一日三餐,但基本也能吃个饱饭。这些刻着名字的碗,更多的时候是用在腊月,家家户户杀完“过年猪”的时候,在处理腌制好猪肉和内脏留备过年吃腊肉用后,剩下的猪杂碎会用来煮一大锅红薯粉,撒上葱花,趁热气腾腾的时候给邻居们家家送上一碗,分享一年一次大口吃肉的喜悦。那段时间里,隔三岔五就有人家杀猪,邻里之间续承着“碗上往来”的习俗,大家也就经常能吃上一碗美味的杀猪粉,我于是盼望着每天都过年、每天都杀猪、每天都吃粉。

长大后离家求学、工作、成家,从小小的农村走向了遥远繁华的都市。小时候那个“贪吃”的愿望,也渐渐越变越大、越变越丰富。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增多,我吃过各种肉、各种海鲜、甚至许多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各个地方的餐桌上,提供的已不再是简单的解决温饱的食物,而是在厨师们的手下,呈现出它们特有的口感和当地的饮食文化。食材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做法和精致的造型,还有食物色彩和营养的搭配,那些装盛食物的碗和盘子,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美感。在这样的时代里,如何吃好一顿饭,似乎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表达。
后来父母也随我们姐弟定居广州,那些刻着母亲名字的碗也跨越山水来到了它近千里的新家。
某次去母亲家,发现她碗里只装着一个鸡蛋、一些青菜和几片水煮肉,以为她身体有何不适,结果人家是在学着网上吃“减脂餐”,直呼近些年吃得太好,体重直升,再不减肥就要“三高”了。碗里的食物,又重新变得简单朴素。但我打心眼里为这简单朴素而高兴,我认为,它是对生活品质怀抱一种更高追求的象征。
今天,母亲将对外孙们的真切关爱盛进这只年近七十、陪伴了四代人的碗里,它早已不再是一只简单的碗,而是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血脉亲情、一片土地的纯良乡情,它同时也见证了一个普通家庭四代人从贫穷到小康的巨大转变、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巨大进步、一个国家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决定把它保存下来,好好珍藏、代代传承,它将会成为我们这个小家庭最宝贵的“家产”。

☆ 作者简介:杨花,湖南汨罗人,护士,现居广州。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