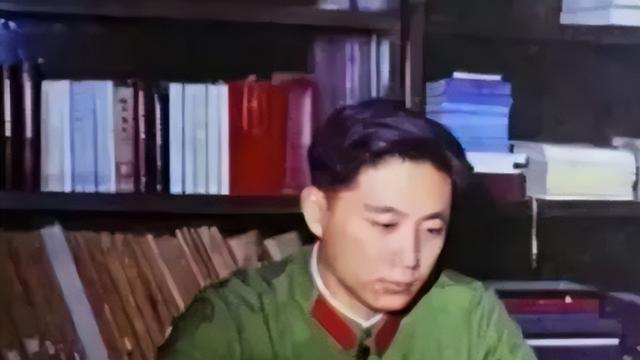东周的序幕在烽烟中拉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被迫东迁洛邑,曾经的天下共主已成虚名。镐京的残垣断壁见证了西周的终结,而洛邑的新都却未能重振周室荣光。平王依仗晋、郑等诸侯勉强立足,但诸侯的野心早已按捺不住。郑国国君护送平王之孙桓王继位,却借机索要土地,周王室疆域进一步缩水,连“赐地”都成了无奈之举。

桓王临终前的一场托孤,埋下了动乱的种子。他暗中嘱托重臣拥立次子姬克,却因长子姬佗抢先继位引发“子克之乱”。周公黑肩策划政变失败被杀,姬克逃亡燕国。这场内斗暴露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目光不再投向洛邑,而是转向彼此征伐。与此同时,齐国在管仲改革中崛起,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之名称霸,周天子的存在沦为诸侯争霸的幌子。
周王室的窘迫在顷王时期达到顶点。襄王去世后,顷王连葬礼费用都无力承担,只能低声下气向鲁国讨钱。诸侯的冷漠与周室的寒酸形成鲜明对比。而邾文公迁都的故事,更凸显了时代的风向——这位小国君主为民生甘愿折寿,赢得赞誉;反观周王,却困于内斗与财政危机,连谥号都显得苍白无力。
战国烽火彻底焚尽了周室最后的体面。周威烈王的一纸册封,将韩、赵、魏三家大夫擢升为诸侯,“三家分晋”宣告礼乐制度的崩塌。此后的周王沦为历史的旁观者:考王为自保分封“西周国”,赧王在秦军压境时试图联合诸侯反抗,却连军队粮草都靠向富商借债。最终,秦军入洛邑,九鼎易主,延续800年的周王朝在屈辱中落幕。
周赧王的结局充满讽刺。这位在位最长的末代君主,目睹秦军将象征天下的九鼎运往咸阳,其中一鼎坠入泗水,仿佛预示天命已绝。迁居阳人的东周公苟延残喘至前249年,而周朝最后的支脉朝鲜国,直到汉初才被卫满所灭。从平王东迁到赧王悲逝,东周25位帝王的故事,不仅是王权的消逝史,更是一部制度、信仰与时代彻底更迭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