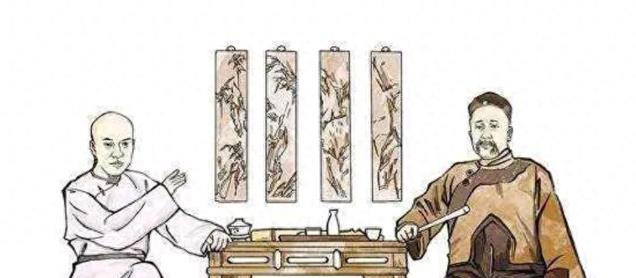
青年杨度:拥抱维新思想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杨家作为地方上的名门世家,家风严谨,崇尚学问,自幼便为杨度的人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杨度自少年起便展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他不仅研读经史子集,还对时势尤为关心。在学术风气浓厚的湘潭,他受到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精神的深远影响,同时对传统儒家理念与近代西方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与质疑。
戊戌变法期间,杨度正值青年,他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影响。当时的中国,正面临国运沉沦的最危急时刻。甲午战争的惨败迫使国人不得不反思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虽然带来了某些技术和军事现代化,但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陈旧阻碍了进一步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紧逼,瓜分中国的危机愈演愈烈。面对注定迎接剧变的国家,许多中国人彷徨而无计可施,士人群体内部分化严重:部分人沉迷传统旧学,避谈实用;部分人则醉心于西方激烈的革命思想,主张推翻一切旧制度。杨度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康梁维新思想的指引下,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富强之道。
杨度对康有为北学的主张和梁启超散布新政理念的文章格外关注,并迅速将这些主张与自己的思考结合。他深信中国社会惟有通过自上而下的体制变革,才能革除积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全面恢复活力。
《金铁主义》登场:憧憬君主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度迎来了学术与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在这一年成为了《中国新报》的主编,在这份刊物上首次发表了《金铁主义说》。这是杨度对国家富强问题的一种全新探索,他提出以“金”为经济,以“铁”为武器,通过经济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强化,来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并非孤立的学术见解,而是杨度对自己君主立宪主张的一部分。他在此前反复比较东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传统帝制的积弊虽多,但若能够结合君主立宪制的形式加以现代化改造,或许能够既保障国家稳定,又避免革命动荡的灾难。
除《金铁主义说》外,杨度在同年又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文章。在文中,他对西方宪政的优缺点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从日本模仿君主制宪政的经验中汲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这些文章与同时期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共同上奏清廷,成为清政府正在推进的“预备立宪”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

次年,清政府将原来的“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被任命为馆中的提调,走向了更具体的政府事务。该馆主要负责宪法框架的起草与修订,杨度在沈家本的主持下参与了清末的修律工作,重点研究法律如何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支柱。
金铁主义与守旧派的对决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试图通过资政院会议推动宪政改革,这是君主立宪制度框架的一次重要实验,也是杨度施展其“金铁主义”理念的舞台。作为具有鲜明维新思想的官僚,与提倡新式法律体系的知识分子,杨度在此会议中强调,中国必须从法律层面彻底清除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特权。

杨度在会议中极力倡导“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前者是指通过普及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第一步。后者则是给予人民诸如营业自由、居住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他设想通过法律的保障,让人民在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自觉承担守法和捍卫国家的责任。
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官僚认为,杨度试图“拔根”,其建议将摧毁支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伦理与文化体系。他们声称,家族制度是维护社会伦理和稳定的根基,把权利从家族结构转移到个体会破坏社会秩序。

一些更为保守的意见甚至指责杨度的“国家主义”思路完全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离经叛道”的西化尝试。面对汹涌而至的批评,杨度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指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利益难题,无论国家如何改革,都不过是旧制度的换汤不换药罢了。
尽管杨度据理力争,但资政院这场争锋的最终结果,仍体现了清末改革的现实窘境——守旧势力根深蒂固,改革派孤掌难鸣。杨度的提议在资政院未能真正地得到推动,其所代表的思想也未能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参与复辟的灰暗一页
辛亥革命的爆发颠覆了清王朝统治,此后的中国风云变幻,一片动荡。在清廷灭亡和民国建立之际,杨度的思想也开始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期。在杨度看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过于剧烈,会彻底摧毁传统帝制下中央集权的基本秩序。这种彻底打破传统的方式,很可能让国家陷入动荡与分裂的深渊。因此,他走上了反对共和、支持复辟的道路。
1913年,袁世凯掌控北洋政府,正式宣布解散国会,逐渐对外显露出恢复帝制的意图。杨度成为袁世凯复辟的主要智囊之一。1915年,袁世凯步步推进帝制复辟计划时,杨度以“筹安会”的方式,为袁世凯铺路。这一组织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前清官僚,为袁世凯称帝进行舆论宣传和理论支持。杨度撰写文章为帝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宣传称中国的国家传统和社会需要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但是,这一理论并未引起社会的共鸣,反而激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革命势力的愤慨。

杨度并没有预料到袁世凯称帝会掀起如此大的反对浪潮。各地反袁斗争此起彼伏,复辟帝制的尝试不但没有恢复杨度理想中的国家稳定,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混乱。袁世凯最终在舆论压迫和地方军阀的威逼下放弃帝制,复辟以失败告终。他不久后便因病去世,杨度也因复辟失败遭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抨击。复辟活动让杨度的政治理想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而他的声望也跌到了谷底。
五四运动后的转折
五四运动发生时,杨度已处于人生的低谷阶段。他曾经坚信的君主立宪道路在清朝灭亡及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完全破产,共和制也未能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政治上背负的复辟污名让他几乎被主流舆论所遗弃;同时,社会剧烈的动荡让他对未来的国家出路重新展开思考。

在此期间,杨度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新的社会运动,通过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撰写的文章,他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改造等理论内容。与此同时,他还有机会与李大钊展开多次深入谈话。李大钊从工农角度解析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并明确指出杨度以往的君主立宪思想遮蔽了对于底层群众力量的理解。
1929年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者面临着极大的生命威胁。在全国报刊封杀、知识分子广泛被监控的艰难环境下,杨度悄然做出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

他秘密向中国共产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并迅速获得批准,成为一名党员。从名动一时的维新思想倡导者,到袁世凯身边的复辟推动者,再到投身工农革命的地下党员,无人能够预料杨度的这一转身。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的入党身份被严格保密,甚至在许多历史资料中,他晚年的革命经历被一度忽略。
在地下活动期间,杨度为党做了许多重要而隐秘的工作。他利用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关系,为革命争取一定的国内外支持,也为党提供了许多理论性建议。在这段时期,他积极阅读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

杨度关于时代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和投身革命的行为,“几乎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杨度的身影”。他的洞察力、适应力以及在各派力量间的游走,使人们常常怀疑他的行动背后是否有超越时代的观念积淀。有人甚至戏言,杨度简直像“穿越者”一样,总能看准时代潮流的方向,调整自身位置,以便化危为机。
参考资料:[1]陈先初,刘峰.杨度宪政主张的正途与歧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1(3):10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