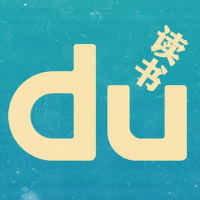别说读书苦,那是你看世界的路——
而后,严尚清几乎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躺在一铺洁净的火炕上,一个叫悦来嫂的中年妇女又是怎样一口一口用水桃根子刻的小匙儿喂他米汤……窗户镜上的霜花儿,一会儿变成个兽儿,一会儿变成一串葡萄,一会儿又变成一只展翅儿高飞的山鸡形状;严尚清想用看霜花的办法,让眼睛多睁一会儿。这工夫,他才领略了所谓人不思不想,是多么难熬的滋味。
外屋里有人在说话。起头嘁嘁喳喳压低声,跟着声儿也越发高起来。只听见鲍廷发含着愠怒的语声:“于永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拨拉你的小算盘?先借你这桶酒,后首我还你。”可能是那个叫于永年的人回说:“这可是纯粹下河口的二锅头哇!”第三个人是人称悦来嫂的,她说:“他于叔,这不是等着急用嘛!”
大概是于永年叹了一口气,悦来嫂嗤了一声,门开了,鲍廷发捧着一铜盆烧酒,轻手轻脚地掀起严尚清盖的被,用羊肚子手巾,蘸着酒,在严尚清两条腿上搓揉起来。严尚清只觉得木胀胀,那腿像不是长在他身上……过了三天,严尚清求鲍廷发把老松树窟窿里的挎包取出来,两个人捧腹大笑了一场。不用说,调拨木材的任务那就不是准时,而是提前完成了。
严尚清从部队转业到棒棰川,曾特意找过一回鲍廷发,原说要痛快喝几盅,大约是剿土匪的事儿把这顿酒给冲了。一个人在县政府,另一个人在林业局的伐木场里,各忙自己的活儿,左推右差,这顿酒却始终是心上的一个愿望。
头年冬出战勤,两个人凑到一块儿了,枪林弹雨里一块儿抬担架,冰天雪地里一块儿饿肚子,两个人都把痛快喝几盅的愿望藏在心里。又一年过去了,找鲍廷发喝几盅的愿望,依然还是个愿望。一个多么简单而又简单的愿望,实现起来却是这么不易。

倏忽间,在这青松岗顶,在这月黑头的晚上,在慎防意外的紧张的瞬息里,这个愿望又从严尚清记忆里闪了出来,甚而他脑门子上又像当年似的出了冷汗,这不是怕斜刺里过来的人是山里的匪徒,而是担心他所相识的鲍廷发的命运——鲍廷发今年在林业局春天卡套(长白山林区俚语,指春融后爬犁(即雪橇)不能行走,运不得木材,把牲口卸了套,以标示季节性的林业生产的结束。)不伐木头的时候回了山东老家,按说最近也该返回棒棰川了;他会不会赶在那趟被炸的小火车上?要是赶在那趟小火车上,会不会摊上暴事儿?
一闪神儿的工夫,斜刺里的来人更近了。
通信员刘金豆窜到了前面,把严尚清挡在身后。
那人一见势头不对,高叫了一声,闪向一边,随怒吼道:“莫非你们要暗算爷爷不成?”
“你敢骂人?!”刘金豆哗啦一声顶上了子弹。
“哟嗬,还亮了呛硬的家伙来了?”那人并不惧怕,“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要钱,我的腰包可不是春上刚卡套那会儿了,嘿嘿,全花在下河口的二锅头上了;要命,我向来不在乎,光棍子一条,早死早利落。”
一听说话的口气不像是歹人,严尚清忙喝住刘金豆,接着上前搭话,来人原来是歇伏后也无家可归的木把子;老家的人死绝逃亡,自己迄今也没混上家口,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随遇而安,挣多少花多少,他们吃喝之外,也有时耍耍钱,靠靠娘们儿,没个过长日子的打算。这种人,在棒棰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上百。

眼前这位便是一个,他叫战老大,在青松岗东边的一个叫寒葱沟的木场子里吃劳金。只因一日三顿饭断不了下河口的二锅头,闹了个酒迷山东的诨号儿。这酒迷山东战老大,是严尚清所熟悉的那个鲍延发的把兄弟;一个地面儿上住着,严尚清也倒是认得他,不过从未过话儿打招呼。
然而,战老大却是不认识严尚清的;他这个人,不知什么叫交往过从,除了下河口的二锅头,至今也还只认得他那一把联儿(即有交情关系的一群人)的哥们儿,外加一个在县城里为木把子们经管宿店的寡妇悦来嫂。
“我说,你们二位是干什么勾当的?”这时是战老大发话了,他手里有个东西在昏黑的夜色里泛着青光,那是山里木把子们出门都不离身的大斧子。
刘金豆觉着这汉子的话有损体面,不无傲横地亮着牌子:“你说我们是干什么勾当的?这是咱县的严县长。”
“啊,啊,我是严尚清。”严尚清在缓和着紧张气氛。
“哟嗬——严县长,县太爷啊!”战老大讥讽地笑笑,“你这么大的官儿是干什么吃的?”
“你这是什么话?”刘金豆不高兴了。
“小刘!”严尚清喝住了刘金豆,随问战老大,“听话味儿,你是对我有意见?”
“不错。”战老大坦率应道。
“那提提吧!”严尚清很震惊:棒棰川这一带的士农工商的普通群众里,还没一个人跟他这么说话的。
“提提?”战老大打了个哏,伸手从腰间摸出个什么物件儿送到嘴边,只听咕嘟一口,一股酒气冲进严尚清的鼻孔,“行,那就提提。我说,你这县长是一县父母官,怎就不替这一带百姓想想?这块儿林子里头藏的那伙子拿枪的官匪老闹事儿,你就治不服?下河口那儿炸了小火车是真是假?”
“是真的。”严尚清说。
“你说这事儿多损政府的脸面!告诉你,我就是为访听这个下山来。”战老大抬高了嗓门儿,“我那大哥打信儿来说,他就是这几天从山东老家回棒棰川。”
“你大哥?”严尚清心里一折个儿,顿时恍然了,“是不是鲍廷发?”
“有名声的人物吧?”战老大很得意,像是有了什么仰仗,“要是他有了个好歹,赶在那趟小火车上,你这当官儿的还有脸儿见黎民百姓?”
“这,这话怎么能这么说?”严尚清有些委屈。
“那怎么说?你自个儿寻思去吧!”战老大一顿脚,矮矮身影从老松树下鬼头石边闪过去,带起一股凉飕飕的风。
严尚清打了个寒噤。

“这人!想不到碰上这么一块料。”刘金豆嘟哝着。
严尚清说不清心里头是个什么滋味儿;战老大的话尖苛得像把刀子,剮碎了一个县长的自信。他到了这个僻远的小县以来,同炮筒子脾气的副县长郭起合作得十分顺手,搞土改,搞支前,搞换工插犋互助组,都得到了省政府的表扬。枪声还没断,已经能够吃饱饭,这是吹气儿的事儿吗?然而,战老大显然是不满足县政府已经做到的这些,他的要求是不是过分了?严尚清沉默着……
本小说背景为建国初期的东北,作者朱春雨。
本号是一个传播优秀文学传承传统文化的平台。阅读是一件重要的小事,关注本号,一起来读书养性、终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