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宋浩编译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在瑞典学院领奖。现场她作了题为《光与线》(LightandThread)的获奖演讲。

在演讲中,她从童年写下的诗句开始,讲述了每一部作品背后的创作心路,而始终困扰她的问题是,“为什么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然而,世界为何又如此美丽?”如今她意识到,只因为她文字背后对人类怀有的爱,促使她一次次重返历史现场,让情感沿着文字之线,传递给一个个读者。
以下为韩江的演讲内容,根据诺奖官网发布的英语版、《文学报》编辑郑周明编译版本整理。

去年一月,我准备搬家时,整理储藏室,偶然发现了一个旧鞋盒。打开盒子,发现了几本童年日记。其中夹着一本小册子,封面用铅笔写着“诗集”。这本小册子很薄:五张粗糙的A5纸对折,订书钉装订。“诗集”二字下面画着两条阶梯状的折线,一条从左向上延伸六级,另一条从右向下延申七级。这是封面插图吗?或者只是一个涂鸦?小册子封底,写着1979年这个年份以及我的名字。
册子里共8首诗,与封面、封底一样,我用铅笔整洁地书写。每一页底部,按时间顺序,写着8个不同的日期。我八岁时写的那些诗句非常天真,没有经过润色,但其中四月的一首,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
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爱在哪里?
它在我砰砰直跳的胸膛里。
爱是什么?
它是连接我们心灵的金线。”
那一瞬间,我被拉回40年前,我制作小册子的那个下午。短短的、套着延长器的铅笔,散落的橡皮屑,以及从父亲房间里偷偷拿来的大号订书机。我得知我们全家要搬到首尔后,我有一种冲动,把我写在纸条上、笔记本空白处,或日记上零散的诗收集起来,集成一册。我记得当时有种无法解释的感觉,那就是我的《诗集》终于完成,并不想给任何人看。

我把日记和小册子放回鞋盒前,用手机拍下了这首诗。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当年写的这些诗句,冥冥中与现在的我之间是连在一起。在我的胸膛里,在我跳动的心脏里,在我们的心之间,那条金线在连接着——一条发光的线。
在那14年后,我的第一部诗集和第一个短篇小说的相继发表,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又过了5年,我花费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出版了。从过去到现在,我对写诗、写短篇小说都很感兴趣,但写长篇对我有特殊的吸引力。我写一本书,通常要耗费一年到七年的时间,写作占据了相当部分的个人生活。写作吸引我的地方也在于此,我可以专注于我认为重要、紧迫的问题,如此我才愿意用个人生活去交换。
每次我写小说,我都会面临着这些问题,生活在它们之中。当我到达这些问题的尽头时——这并不意味着我找到了答案——便是写作的结束。到那时,我已经不再是最初的自己,而是从这种改变的状态开始新的创作。接着是下一个问题,像链条上的一环,或像多米诺骨牌,彼此叠加、连接、延续,推动我去写新的东西。

《素食者》,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
2003年至2005年,我写第三部小说《素食者》时,我一直面临着一些痛苦的问题:一个人能完全无辜吗?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暴力?一个拒绝成为“人类”的人会怎么样?
《素食者》中,主人公英慧选择不吃肉,拒绝暴力,最终她拒绝除了水之外的所有食物和饮料,因为她相信自己变成了一棵植物,讽刺的是,她为了“拯救自己”而快速走向死亡。
英慧和她的姐姐仁惠,其实是故事中共同的主角,在绝望的噩梦和创伤中无声地呐喊和尖叫,但最终她们还是在一起。故事的最后,我把场景设定在救护车上,因为我希望英慧在这个故事里活下去。救护车在浓翠的绿茵中,沿着山路疾驰而下,而姐姐凝视窗外,也许在等待回应,也许在抗议。整部小说都处于一种质疑的状态:凝视,抗议、等待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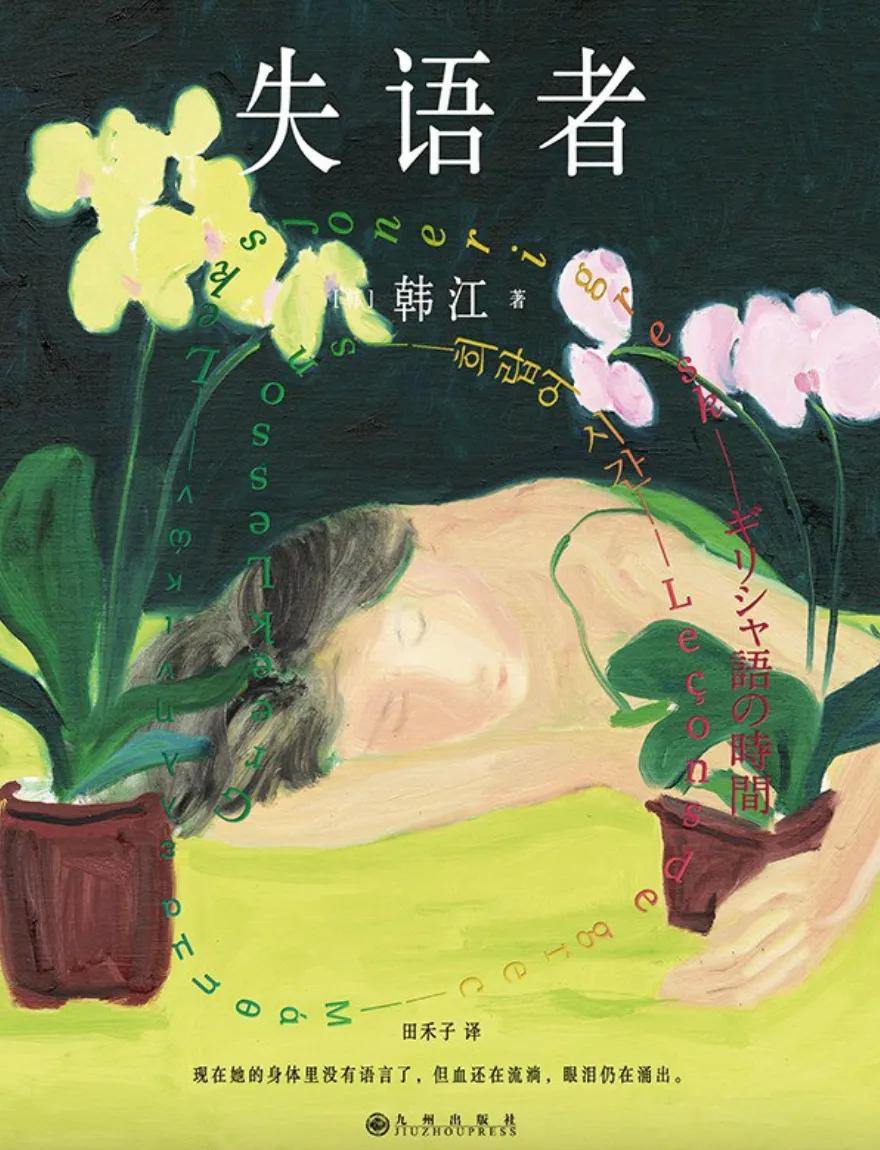
《失语者》,磨铁/九州出版社,2023年
我的第五部小说《失语者》中,我更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必须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瞬间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一个失语女人和一个失明男人,在寂静和黑暗中行走,在孤独的道路上相遇。我试图捕捉故事中那些触感鲜明的瞬间。小说在自己的缓慢节奏中推进,穿越静默和黑暗,直到女性伸出手,在男性的掌心写下几个字。那个瞬间仿佛无限延伸,变成永恒。在这片刻中,这两个角色展现了他们最柔软的部分。我在这里试图询问:是否正是通过凝视人类最柔软的部分,感受那不可否认的温暖,我们才能在这个短暂、暴力的世界中继续活下去?
之后,我开始思考下一部小说。这是在2012年春天,《失语者》出版后不久。我告诉自己,我要写一部向光明和温暖又迈进一步的小说,这是一部充满透明感和生机的作品。我立马找到了一个标题,初稿已经写了20页,但我不得不停下来。我意识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写下去。
直到那一刻,我还没考虑过写光州。1980年1月,我们全家搬离光州时,我才9岁。几年后,12岁的我偶然看到书架上的一本《光州照片集》,周围没有大人。小时候,我还没有理解那些图像的政治意义,那成为了我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类为何对同类施加如此暴行?在我的心中结成一个我无法解开的结。
于是,2012年春天,当我试图写一部光辉而充满生命力小说时,我再次面临着这个未解的问题。我早已失去了对人类根深蒂固的信任。那么,我又该如何拥抱这个世界?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前行,就必须面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我明白,写作是我唯一能突破并超越这一切的方式。
那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那部小说,想象1980年5月的光州会成为这本书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这本小说不会仅仅将光州作为一个背景,而是要正视它。
在小说做准备性研究时,有两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我二十多岁时,我已经在每本日记的扉页页上写下这些话:
“现在能否帮助过去?
活着的人能否拯救逝者?”
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答的。在对人类最黑暗面的持续探寻中,我长久以来破碎的对人性的信念彻底崩塌。我几乎放弃了这部小说。然而,我读到了一个年轻夜校教师的日记,日记中写道:“为什么我必须有如此刺痛我的良知?我多么想活下去。”
读到这些话时,我仿佛瞬间被闪电击中,明白了这部小说的方向,也意识到我的两个问题必须反转:
“过去能否帮助现在?
逝者能否拯救活着的人?”

《少年来了》韩文版封面
后来,在写成《少年来了》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在某些时刻确实感受到,过去在帮助现在,死者在拯救活着的人。
那本照片集留给我的问题长久萦绕:人类为何如此暴力?然而,为何人类又能与如此压倒性的暴力相对抗?作为一种被称为“人类”的物种,这意味着什么?为了在人类暴行与人类尊严这两座深渊之间的空白中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我需要死者的帮助。就像小说《少年来了》中,孩子东浩拉着母亲的手,试图将她引向阳光一样。
当然,我无法改变已发生的事,无法补偿死者、幸存者或他们的家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我的身体中流动的感知、情感和生命力借给他们。怀着这样的愿望,我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点亮了一支蜡烛。在开篇,我描写了市体育馆中,十五岁的东浩为尸体铺上白布并点燃蜡烛的场景。他凝视着每支蜡烛淡蓝色的火焰。
这部小说的韩文标题是《소년이온다》。“온다”是动词“오다”(来)的现在时。当少年以第二人称“你”被称呼时,他在微弱的光线中醒来,朝着现在走来,他的步伐是一个灵魂的步伐。他逐渐靠近,化为当下。当我们用“光州”指代一个人类残暴和人类尊严并存至极的时间与地点时,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独特的专有名词,而是变成一个普通名词。正如我在写这本书时所领悟的,它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时间和空间来到我们面前,并永远以现在时存在。即使是现在。
当这本书最终完成并于2014年春天出版时,读者向我倾诉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这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我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与读者对我表达的痛苦之间,有什么联系?这种痛苦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人性抱有信念,而当这种信念被动摇时,我们感到自身的某种根基也被摧毁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人类,而当这种爱被打碎时,我们便陷入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之中?爱是否会带来痛苦,而某种痛苦是否正是爱的证明?

同年的六月,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穿过一片辽阔的平原,稀稀落落地下着雪。无数的黑色树桩点缀在平原上,而每一根树桩后面都藏着一个坟堆。忽然,我踩进了水里,回头一看,发现远处我以为是地平线的地方,海水正在涌入这片平原。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会有坟墓?我感到疑惑。那些靠近海边的低矮坟堆里的骨头,难道不会被海水冲走吗?而那些靠上的坟堆,我是不是至少应该赶紧把骨头迁走呢?可我能怎么办呢?我甚至没有一把铲子。我醒来后,盯着依旧漆黑的窗外,隐约感觉到这个梦在向我传递某些重要的信息。写下这个梦后,我记得自己曾想,这也许是我下一部小说的开端。
然而,我并没有清晰的方向。于是我尝试构思一些可能从那个梦中延伸出来的故事,但一一放弃。直到2017年12月,我在济州岛租了一间房,接下来的两年间,我在济州与首尔之间来回往返。在济州的森林里、海边以及村路上漫步,感受着每一刻济州强烈的天气——风、光、雪和雨——我渐渐捕捉到这部小说的轮廓。与《少年来了》相似,我阅读了关于屠杀幸存者的证词,仔细研究资料,然后尽可能克制地、毫不回避那些几乎难以言说的残酷细节,写下了后来成为《不做告别》的作品。这本书最终在我梦到那些黑色树桩和汹涌海水后的七年间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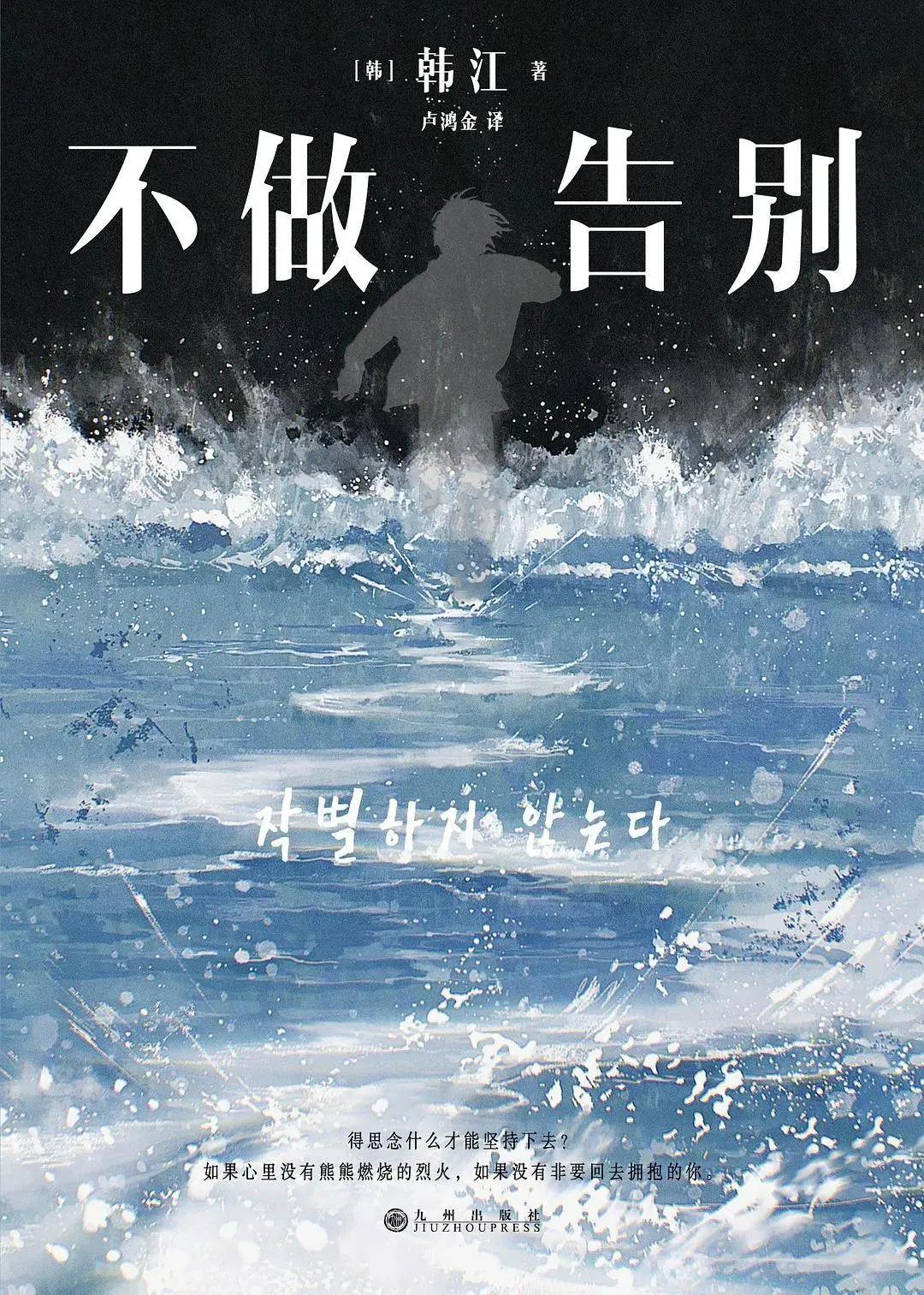
《不做告别》磨铁/九州出版社2024版
在为这本书工作的笔记本里,我写下了以下内容:
“生命追求生存。生命是温暖的。
死亡意味着变得冰冷。雪落在脸上却不会融化。
杀戮意味着让生命变得冰冷。
人类在历史中,人类在宇宙中。
风与海流。连通整个世界的水与空气的循环流动。
我们是相连的。我祈祷我们是相连的。”
小说由三部分组成。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一次横向的旅程,跟随叙述者庆荷从首尔穿过大雪来到朋友仁善的济州的家,去解救她被委托照看的宠物鸟,那么第二部分则是一段纵向的旅程,带领庆荷与仁善回到人类最黑暗的夜晚之一——1948年济州平民被屠杀的冬天——并深入海底。而在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二人共同在海底点燃了一支蜡烛。
尽管小说由两位朋友推动前行,就像她们轮流举着那支蜡烛,但小说真正的主角,以及与庆荷和仁善都有联系的人,是仁善的母亲正心。她在济州的屠杀中幸存下来,为了找到自己至亲的一块骨头,能够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她不断抗争。她拒绝停止哀悼,承受着痛苦,对抗遗忘,不肯说再见。在关注她的生活时——她的生活长期被同等密度和热度的痛苦与爱所炙烤——我想我在问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极限在哪里?为了在生命的尽头依然保持作为人的本质,我们究竟需要爱到什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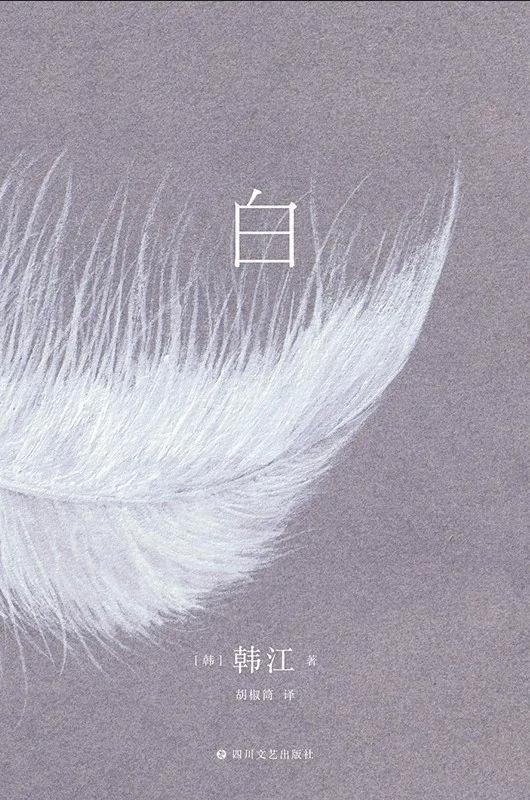
《白》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版
距韩文版《不做告别》出版已经三年了,而我的下一部小说仍未完成。而我原以为会紧随其后的那本书,也已经等待我很久了。这本书在形式上与《白》有联系,我写《白》时的初衷,是希望能短暂地将我的生命借给那位在出生仅仅两个小时后就离开人世的姐姐,也希望能探寻我们身上那些无论经历什么都无法摧毁的部分。像往常一样,我无法预测任何作品会何时完成,但我会继续写下去,哪怕速度很慢。我会跨过那些我已写过的书,继续前行,直到转过一个弯,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一直走到我生命所能抵达的最远处。
当我远离它们时,我的书也将独立于我继续它们自己的生命,按照它们的命运去远行。正如那两位姐妹,她们将永远待在那辆救护车里,在挡风玻璃外绿色的火光中一起向前。正如那个女人,她即将重新开口说话,但此刻却在黑暗与静谧中,用手指在男人的掌心写下文字。正如我的姐姐,她仅仅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两个小时,和我那年轻的母亲,她一直恳求她的婴儿:“别死,求你别死”,直到最后一刻。那些灵魂会走多远——那些在我闭上的眼皮后汇聚成深橙色光芒的灵魂,那些将我包裹在无法言喻的温暖光线中的灵魂?那些蜡烛会走多远——在每个屠杀现场,在每一个被无法想象的暴力摧毁的时间和地点点燃的蜡烛,那些由发誓永不说再见的人们高举的蜡烛?它们会沿着一根金色的线,从一根灯芯传递到另一根灯芯,从一颗心传递到另一颗心吗?
我从旧鞋盒里翻出的那本小册子里,过去的自己在1979年4月问了这样的问题:“爱在哪里?什么是爱?”
而直到2021年秋天,《不做告别》出版时,我始终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我的核心:“为什么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世界为何又如此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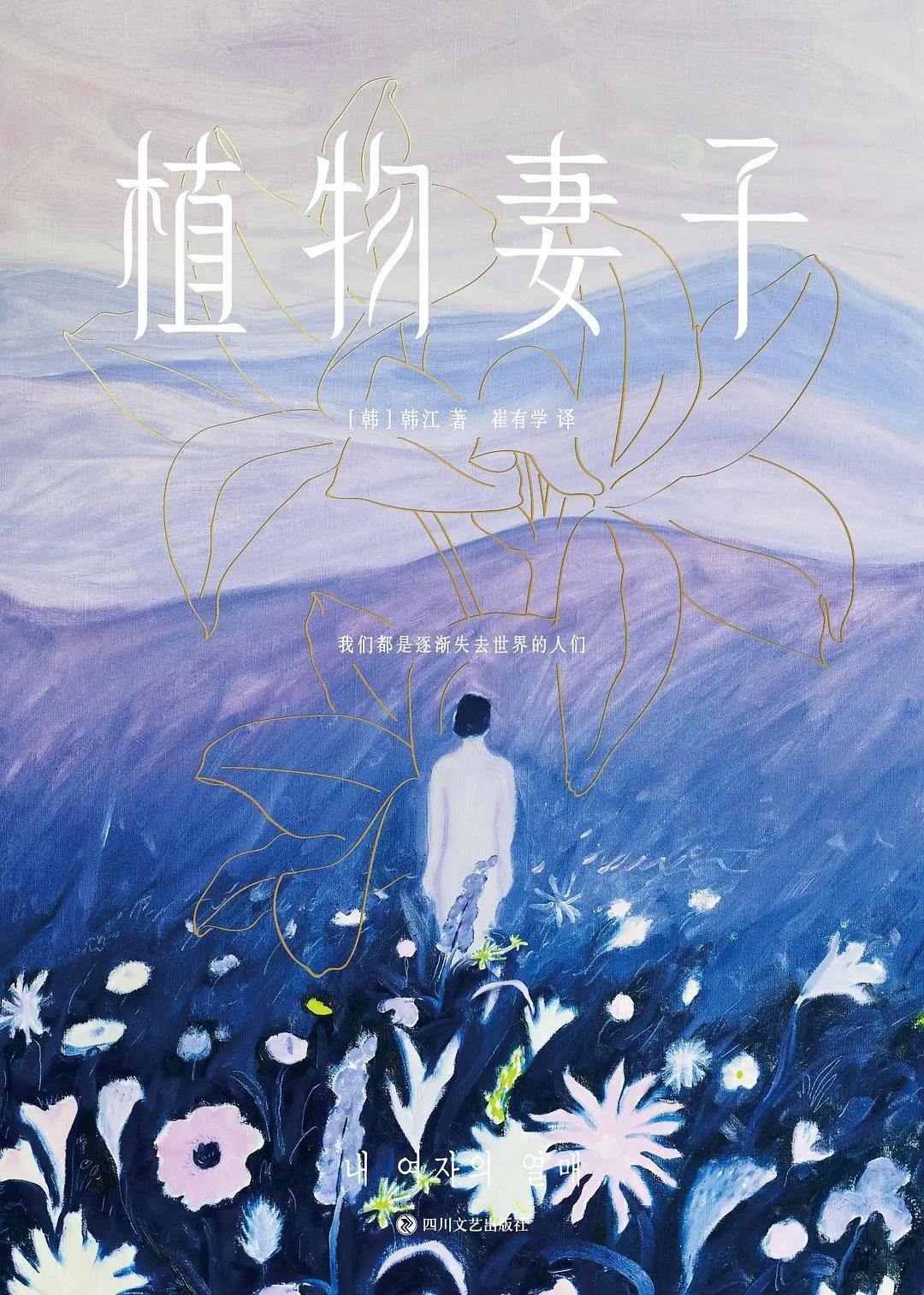
《植物妻子》,磨铁/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版
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两句话之间的张力和内心挣扎是我写作的驱动力。从我的第一部小说到最近的一部,伴随我思考的问题不断变化和延展,但这两句始终不变。然而,两三年前,我开始产生疑问。难道我真的只是从2014年春天《少年来了》韩文版出版后,才开始问自己关于爱的事情——关于将我们连接起来的痛苦?从我最早的小说到最近的作品,我最深层的追问难道不是一直指向爱吗?爱会不会其实是我生命中最古老、最根本的基调?
1979年4月,那个孩子写道:“爱在一个叫‘我内心’的私密地方。(它在我扑通扑通跳动的胸膛里。)”至于什么是爱,她的回答是:“它是连接我们心灵之间的金色线。”
当我写作时,我使用我的身体。我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用舌头去尝,用心去感受温柔、温暖、寒冷和痛苦。我注意到我的心跳加速,注意到我的身体需要食物和水,注意到我在行走和奔跑,注意到风、雨、雪落在我皮肤上的触感,注意到牵手的感觉。我试图将我作为一个血液在体内流淌的凡人所感受到的那些鲜活感官注入到我的句子中,就好像我在释放电流一样。当我感觉到这种电流传递到读者时,我感到震撼并深受感动。在这些瞬间,我再次体验到将我们连接起来的语言之线,以及我的问题如何通过这种有生命的电流与读者发生联系。我想向所有通过这条线与我产生联系的人,以及所有未来可能会这样做的人,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情。
(图片来自诺奖官网、磨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