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曾说:实事求是的讲,大多数人对中国文学、对莫言小说的了解程度只能算是一知半解,停留的层面或止于电影《红高粱》。易中天也直言:单论描写农村生活,路遥的思想层次、艺术水平比莫言差了好多,即使柳青的《创业史》彪炳史册,但比莫言《生死疲劳》还是略逊一筹。浅薄的读者,不能理解莫言的伟大,那种深藏于宿命论的抗争。 莫言写小说有个特点,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什么高高在上的文化人。他总说自己在生活里就是个普通人,胆小怕事,遇到麻烦能躲就躲。可一拿起笔来,这人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就像他自己说的,写小说的时候"贼胆包天",能把平时不敢说的话都倒出来。 你看他写《丰乳肥臀》,那些荒唐事,什么让绵羊和兔子配种啊,想培育凤凰啊,写得活灵活现。这些事放在今天看简直不可思议,可那时候就是有人当真。莫言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写这些沉重的话题从来不说教。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把人和事原汁原味地端出来,让你自己去品。这种写法特别考验功力,就像他说的,作家得站在人类的高度看问题,但又不能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都特别鲜活,有血有肉,你会觉得这就是你村里的张三李四,甚至是你的某个亲戚。 有意思的是,莫言写这些严肃题材的时候,语言却特别生动,甚至有点粗俗。他不在乎什么文雅不文雅,怎么痛快怎么来。这种写法刚开始可能让人觉得不适应,但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生活的本真。就像农村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莫言的小说也是这个调调,直来直去,反而更有力量。 说到底,莫言写来写去都是在写人。他写历史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想弄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在不同时代会做出那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明明是好心却常常办坏事?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莫言用他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的小说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困惑和挣扎。 莫言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经历了三个鲜明的阶段,这种创作轨迹折射出他对人性认知的不断深化。从最初"把好人当坏人写"的颠覆性视角,到"把坏人当好人写"的辩证思考,最终抵达"把自己当罪人写"的自我拷问境界。这种创作理念的演变,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对历史与人性的理解在不断突破表层,向着更幽深的内心世界掘进。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种将自身置于审判席上的写作姿态显得尤为珍贵。当大多数作家习惯于扮演旁观者或批判者的角色时,莫言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将批判的锋芒转向自身。这种自我解剖的勇气,使得他的作品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更成为一面照见人性深渊的镜子。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引下,文学不再是简单的歌颂或暴露,而成为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叩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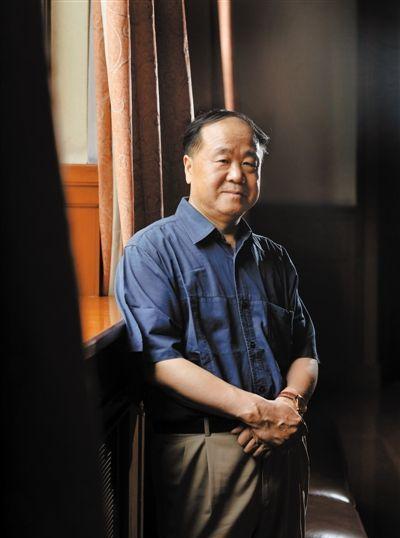


大牛
投敌所好写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