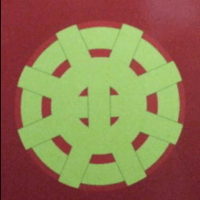作者:张道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航运学校毕业以后分配来淮安到运河上成了一名跑船的人,与师傅结下了一段师徒缘。
师傅是一位老水手长,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拿工资时在工资表上签不好自己的名字,只能让他摁手印。可他撑船弄船的技术实在是一流。他是个有经历的人,航行途中我经常缠着他讲古。他出生在山东微山湖上,所以讲一口侉话,祖祖辈辈在微山湖逮鱼为生。在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而亡,他侥幸存活下来,是父亲用鱼汤把他喂养大,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在他15岁那年,父亲终究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离他而去。临终前拉着他的手,叮嘱他:“不求大富大贵,要学好,不要学坏,平平安安地做一个好人!”他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卖船葬父。
为了活下去,他经人介绍去给运河上的船家做伙计,前三年从学徒开始,所谓学徒,就是给船家打杂,给船主做饭洗衣服带孩子,甚至给女主人洗刷马桶,还受尽白眼,经常被打骂,吃不饱肚子。到他成年时加入到撑船拉纤的船工队伍,最终落脚到淮安,因为淮安的船运发达,生意多,赚到钱。撑船拉纤是苦行当,世上三样苦呀,撑船打铁磨豆腐,日晒雨淋,餐风饮露,用脚板丈量人生。肩背时常被纤绳勒得火辣辣的痛,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一开始脚上总是磨出水泡,晚上用针把水泡放了,钻心地疼,第二天抹上药膏用布缠上继续上路。时间长了,那些长水泡的地方就结成硬硬的厚厚的老茧。
除了体力之苦,还要忍受夫头(船主与船工之间的经纪人)的盘剥。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船工们常常按照地域结成帮派体系,帮派之间会因为利益之争常常发生械斗,打得头破血流。回忆过去,师傅常常一声叹息,目光盯着遥远的天际,久久回不到现实中来。

师傅还会哼几句船工号子,那么有力,那么悠扬,非常有韵味,仿佛让我看到一队船工躬身在运河边,裸露着黑红的后背,一步一个脚印,一根纤绳牵着一艘航船在晚风中悠悠前行。每当夜色深沉,船工们就会上岸找乐趣,喝酒赌钱,甚至寻花问柳,有的人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撒在沿河的花街柳巷,及时行乐;有的人终身不娶,最后染疾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初入行时,师哥们会带着他上岸见世面,喝喝酒,有的人会鼓动他玩“花活”,可是他滴水不进,把口袋捂得紧紧的,永远记得父亲临终前给他说的话,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存够钱,娶一个媳妇成个家。
师傅虽然个子不高,可是长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锻炼了他的体魄,练就了一身好体力和一手娴熟的弄船技艺。50年代公私合营时,他被招入国营航运单位,成了一名正式工,从此开始了他的美好人生。后来师傅经人介绍找到了一个疼他爱他的师娘,师娘长得高高大大,比师傅还高半个头,是船公司下属蓬帆服装厂的工人。
每当我们船队要靠岸时,总是看到师娘扶着自行车在码头上翘首等望,师傅总会笑嘻嘻地拿着各种早就加工好的熟食,有烧鱼烧鸡鸭,沉甸甸的,坐上师娘的自行车欢笑而去,让我们年轻人羡慕不已。
因为从旧社会苦难生活过来的人,新社会当家作主人,这在师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真正的爱船如家。一天到晚闲不下来,船甲板总是光亮如镜。靠球破了,他会补一补。缆绳断了他会接起来。用旧用破的拖把他舍不得扔,待领了新的拖把条,他就把新的旧的掺杂使用,用起来还很顺手。他没事就喜欢修修补补,修旧如新,修补得天衣无缝,真是好手艺。晴好天气,他会把锚链拖出来铺在甲板上晒,防止生锈。前舱里各种物料摆放整齐,师傅就像当家过日子的人那样守着他那些宝贝。人家船队总是物料不够用,而我们的船队上总是富余。

师傅好烟好茶,烟不离手,茶不离口。他的茶缸是那种老式搪瓷的,印有当年领袖的头像,背景是光芒四射的红太阳,下面一行字是公司某年职代会纪念。为了防止在茶缸盖子掉河里,他用橡皮筋把茶缸盖子系在茶缸手把上。长年累月的,茶垢都把茶缸染得发黄,脏兮兮的,黑不溜秋的。师傅虽好茶,却舍不得买好茶,都是在茶叶店淘的茶叶沫子,泡得酽酽的,稀苦稀苦的,与职业有关,晚上航行值班时,这样的茶汤特别提神。
晚上船队靠泊,他会拉一盏灯静静地钓鱼,人家钓不到,但是师傅能钓到,也没看他下铒料。每当夜晚船队停泊时,我就会鼓动师傅钓鱼,最喜欢那些个静悄悄的夜色里,星光闪闪,微风习习,渔火点点,虫鸣啾啾,水声汩汩,看浮标在水面上浮沉。我总是希望浮标能迅速下潜,一条接一条的才过瘾,可是师傅说不能心急,钓鱼最能磨练人的心气,你看那浮标半天也不动,可是当你绝望放弃的时候浮标却突然下沉,好像真是蕴含着人生哲理呢!只见师傅稳坐缆桩上,一杯茶一支烟,悠闲自在。
当浮标“嗖”的一下突然从水面急速下潜时,我的心跳也会“嘭嘭”加快,大概这就是钓鱼人的乐趣吧。钓上来的鱼很杂,有鲫鱼、昂刺鱼、白条等各种河鲜。钓上来的鱼师傅会就现场加工烧得我们吃,师傅做得一手好饭菜,尤其擅长煮鱼,真正的河水煮河鱼。各种小杂鱼处理干净了,油烧热锅冒烟,鱼下锅慢煎,在鱼快熟的时候,师傅会沿锅上沿贴一圈饼子,贴饼子的面糊和起来十分讲究,稠了摊不开,厚薄不匀不好吃;稀了挂不住,全掉汤里了,全凭火候和经验。

快出锅时,师傅会不断用勺子把鱼汤浇在面饼上,特别地入味,让人馋涎欲滴,不断地咽口水,那香味飘出去好远,弥漫在河面上,隔着几条船都能闻到。他不但会烧鱼,还会吃鱼,看他吃鱼是一门艺术,只见一条小鱼横着夹在口中,就像吹口琴一样,上下牙床磕碰着,再翻着身,上下牙床继续磕碰,不一会,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从他嘴里吐出完整的鱼骨架子,一根刺都不会少,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神奇了,把我们看呆了。在我看来,他就是为河而生、为船而生的,他的生命与运河深深地融合在一起。
师傅还特别会做手擀面,把面和得硬硬的,面团摊在案板上,因为师傅个子矮,我看他脚后跟踮起,好像整个身子压在擀面棍上,用长长的擀面棍反复卷着推着,一次次展开,一次次卷起,面团在他的反复碾展下,慢慢地扩开,成为一张硕大的面皮,一层一层叠起来,用刀细细地切,抖开,下锅,用青菜穿个汤,淋上鸡蛋花子,那劲道、口感、嚼头、面香,师兄弟们你争我抢,不一会儿,一大锅连面带汤吃个底朝天,比现在饭店的小刀面好吃多了。
别看师傅平时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安静得让人忘记他的存在,可关键时候就看出他的惊人之处。我们船队是运河上大型吊拖船队,一轮四拖,后面四条驳船各600吨,一个船队满载就是2400吨,在当时运河上是属于大型船队了。在过船闸的时候,整个船队长度超出闸室长度,拖轮要改缆绑到船队边上,出闸时再编队出去。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船队过淮安闸,我因为是刚上船,照顾我在船头值班,活简单些。师兄在船尾,活相对复杂些,在往闸墙上挂缆时,正常安全的做法是跨步上前,好进好退,这在课本上是学不来的,全凭工作实践悟出来,而师兄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并步上前挂缆,没想到拖船甩尾了,其后果是他下半身回来了,上半身却回不来了,“扑通”一声掉河里了。

当时正在驳船头的师傅三步并两步地往轮船驾驶室冲去,与正在向船尾跑的我差点撞个满怀。我就纳闷了,师傅不救人,却往驾驶室跑干嘛?当我赶到船尾时,只见水里的师兄只有一绺头发飘浮在水面上,不断地在水里挣扎。因为穿着救生衣,不至于出人命,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上来。而师傅考虑的是,他必须第一时间通知驾驶室的人千万不要动车,无论是进车还是倒车,那螺旋桨产生的强大的冲击力或吸附力才是致命的。
听师傅这样一说,我们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师兄经过几年严格的磨练,终于成了一名运河上非常有能力有经验的船长,这也算是成长的代价吧。
师傅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他特别喜欢和佩服有文化的人。上船以后,我一直注重读书学习,倒不是有什么功利目的,而是一种习惯。航行中一般夜里十二点交接班,有时候我读书学习的晚了,睡过头了,常常起不来,师傅也不叫我,也不怪我,还安慰我说:“你们年轻人觉好睡,我们岁数大了,睡的少。”
1984年的秋天,公司举行国庆征文比赛,我的一篇散文《航标灯》获得一等奖,公司领导认为我孺子可教,就调我到机关做文字工作,我与师傅一年半的师徒缘分就结束了。
后来师傅在船队靠岸时,来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真的非常开心,捧上一杯热茶,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他有点受宠若惊,屁股在椅子上就坐不住了,局促不安。离开了水,离开了船,他就失了魂。

公司开职代会或年度表彰大会,会派机关干部下船队蹲点,宣传贯彻会议精神,我有幸被分配到师傅的船队。师傅见了我,像见到亲人,又是帮我拿行李,又是帮我铺床,拿出他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一遍一遍地把床铺擀平,脸上笑成一朵花,那一日三餐把我照顾的是乐不思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暂时放下那些烦心俗事,来到世外桃园一样的船上,任水流有节奏地拍打在船舷上,船舱有节奏地晃动,像极了小时候的摇篮。临分别时师傅那个依依不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其实我能帮助师傅回报师傅的真的不多,甚至没有。但是,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感情,尤其是在师傅这代老工人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算起来,师傅也应该耄耋之年了,愿他老人家安享晚年,健康快乐吧!
编辑:苗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