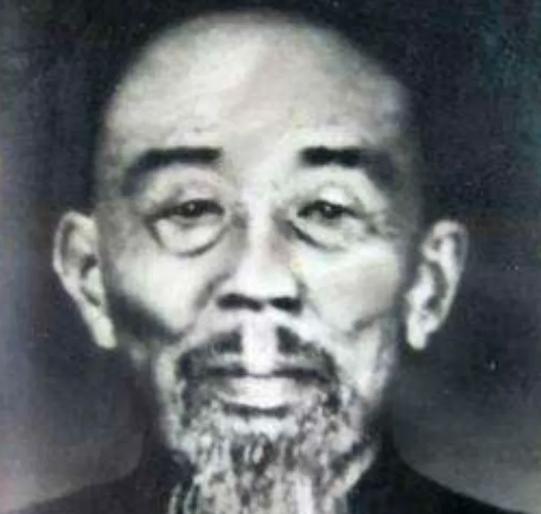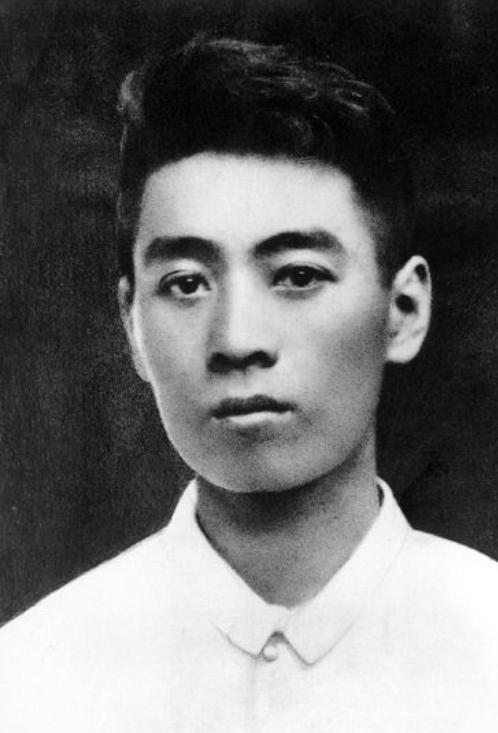建国后表哥给周恩来写信,被秘书当作普通信件,从此两人失去联系 “1950年初春的上海邮局窗口——‘同志,请寄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收。’”老人声音微颤,双手奉上一只泛黄的信封。营业员点头收下,他在柜台前站了许久,才慢慢转身。信封里装着的不仅是问候,更是四十多年血脉亲情的惦念。 几周后,那位老人——陈式周,却收到一封盖着“国务院办公厅”公章的回函。几行工整铅字冷冰冰:“建议来函者,就近与地方人民政府联系。”语气公式化,没有称呼,没有署名。老人愣在长廊里,半晌发不出声。他记得表弟周恩来早年的亲笔信,墨迹犹新、语气热烈。此刻,落差像江水灌进胸口,凉得发痛。老人不再提笔,家人却看见他把那封回函与旧信叠放,珍而重之地锁进抽屉。 故事得回到1907年。那年夏天,九岁的周恩来随嗣母陈氏来到江苏宝应水巷口。嗣母抱病求医,寄居娘家。宅子里开设的蒙馆生气勃勃,书房深处堆满线装书。此时的陈式周,二十五岁,毕业于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饱读经史,又走南闯北。小表弟的到来,让这位青年书生眼前一亮。几次交谈,他惊讶于孩子对《左传》《水浒》的信手拈来,更惊讶于少年竟能评价“洪杨之乱”的成败。于是,他向陈氏建议:别让大鸾再学千字文,直接到我书房来。 日子像江南细雨,三个月悄然溜走。白天,表兄弟捧书对坐;夜里,油灯下讨论太平天国、西学东渐。陈式周喜欢引经据典,小周恩来常常追问:“若天下真可大同,路在何方?”一次游京杭大运河堤,他指着往来漕船说:“表哥,河水不息,可民生却艰。”这样的对话里,早已埋下关注苍生的种子。 短暂相处后,两人各奔前程。周恩来随伯父北上,辗转进入天津南开;陈式周留沪,在《申报》任编辑。1919年的五四浪潮席卷津沪,兄弟重启书信往来,频率之高几乎月月一封。周恩来把观察写成稿件,托表哥改润后在《申报》刊出;陈式周则把上海书局的新书、时事评论寄往天津。信里,那股子彼此砥砺的劲头,让人读来仍觉脉搏跳动。 1920年底,周恩来越洋赴法前最后一夜,两人在上海永泰里彻夜长谈。陈式周掏出积蓄凑路费,拍着弟弟肩膀叮嘱:“读书也好,革命也罢,别忘了看清百姓饭碗。”翌日清晨,他护送弟弟登上“波尔多斯”号邮轮。海风猎猎,船舷边相视一笑,各自心事都在波浪里起伏。 法国餐费便宜、革命史料丰富,表哥给的一句话,让周恩来留了下来。三个月后,他写信道:“俄式改造或许是中国唯一出路。”信纸四页,逻辑缜密,情感激昂。陈式周读完连称“深得我心”,当即回信鼓励:“但行稳致远,勿躁勿怯。”兄弟在纸面上辩驳冲突、交换立场,彼此逼出更清晰的思想。不得不说,这段通信,正好见证了周恩来由学生向职业革命者的蜕变。 然而历史车轮滚滚。1927年,南昌起义后,上海报纸对周恩来火力全开。陈式周摔报怒骂“无耻”,转身示范给外甥:“读新闻要分真假,恩来不是那样的人。”为了保护表弟,他把周恩来寄来的欧洲照片与信件悉数收好,外人难窥半分。 30年代初,周恩来秘密回沪,几次更名换装。陈式周利用编辑身份,藏匿文件、安排联络,冒着坐牢风险做掩护。可1931年底,周恩来赴江西中央苏区,两人音讯隔绝。抗战全面爆发,陈式周带妻儿返回宝应。那处陈氏祖屋因战乱被卖,他四方筹钱赎回,粉刷梁柱,只为某一天能同弟再坐廊下谈书卷。 日子耗在烽火与期盼里。1949年10月的清晨,天安门礼炮声传到江南小镇。陈式周翻报纸,看见“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字样,眼眶一下湿润:“多少年了,他做到了!”这一声感慨被孩子们记住,也促成了那封迟来的家书。 可命运偏爱玩笑。中南海办公厅每天接收山一般的信件,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批阅分级,陌生来信自然列入“群众来函”类别。周恩来几乎拿不到那些无明显标识的私信。就这样,一份家书被当作普通信件处理,从“亲属问候”变成“建议到地方政府报到”。一纸差错,兄弟情被卡在邮袋里,遗憾刻进年轮。 1954年,北京医院里,72岁的陈式周因病离世。病榻前,他仍嘱咐子女:“把表弟的信件保存好,以后或能用得上。”他没机会知道,周恩来其实一直在找他。1964年,总理委托江苏公安厅查访“陈式周”时,卷宗显示——已逝。直到1970年代末,周陈两家后辈才重新聚首,提到往事,仍唏嘘无言。 书信往返、红尘聚散,一次不起眼的误分档,就让两位血脉之亲错过了见面。有人说这是时局弄人,也有人说是制度流程的盲区。我更愿意相信,深埋在老抽屉里的那些手稿、邮票与折痕,早已替他们完成了最后一次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