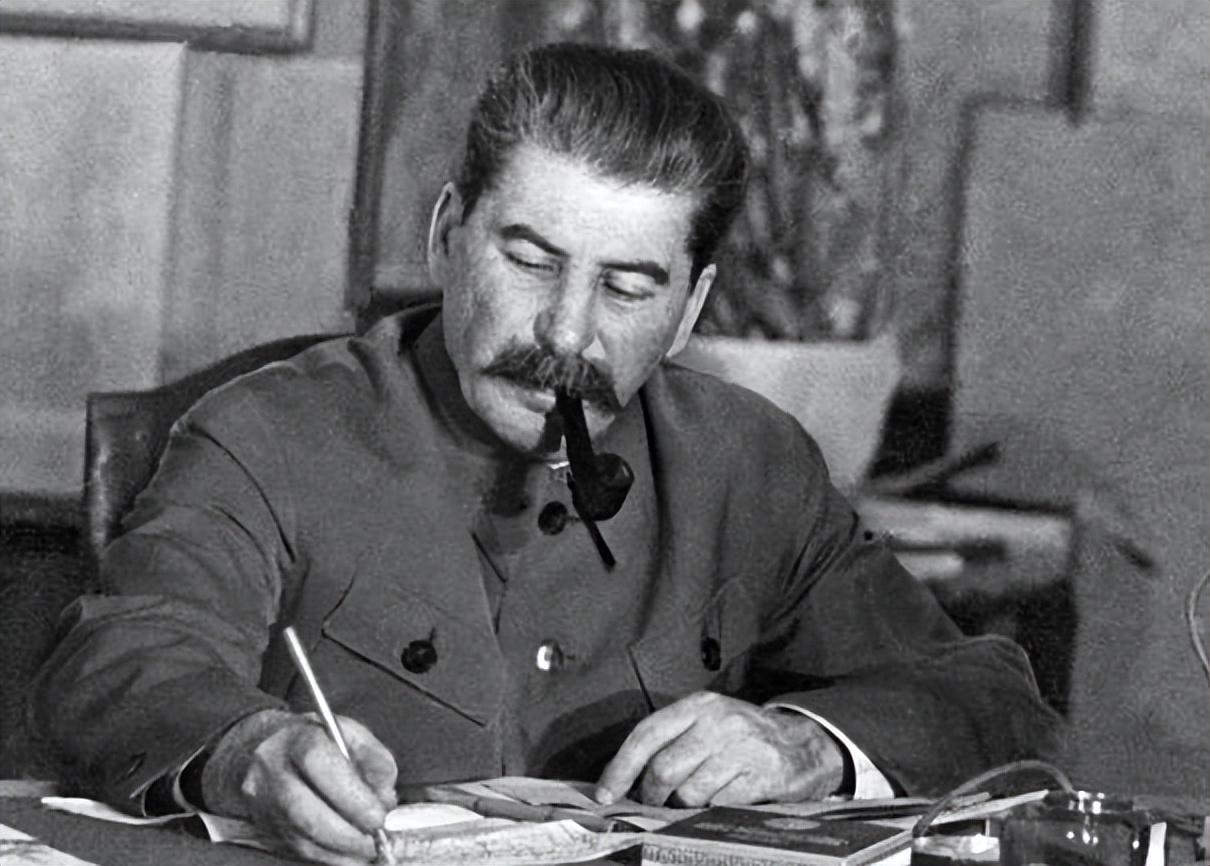普京看出情况不妙,西方让苏联解体一幕重演,绍伊古紧急出面表态,却显莫斯科力不从心?利用他国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削弱对手,是西方国家沿用数百年的招数,远有英法借民族问题搅动奥斯曼内乱,近有苏联解体,都是西方这一战略的现实体现。 西方国家利用对手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来削弱其整体实力的做法,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传统。这种方法并非新鲜发明,而是从19世纪起就反复验证的有效路径。以奥斯曼帝国为例,英国和法国情报机构早在1870年代就开始系统干预,通过资助阿拉伯部落和亚美尼亚团体,放大奥斯曼统治下的教派对立。它们散布虚假情报,声称苏丹偏袒逊尼派穆斯林,剥夺少数派权益,导致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起义频发。 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这种外部煽动加速了帝国的领土流失,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国相继独立。奥斯曼的衰落并非单纯军事失败,而是内部凝聚力被精准瓦解的结果。到一战结束,英法主导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进一步肢解中东,证明了这种策略的长期效力。俄罗斯作为奥斯曼的宿敌,本该从中吸取教训,却在当代重蹈覆辙。 这种路径依赖在20世纪冷战后期对苏联的围堵中得到放大。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80年代起加大投入,支持波罗的海和中亚的分离势力,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印刷反俄宣传品。这些材料突出俄罗斯人与本地穆斯林的资源分配不均,引发1989年里加和维尔纽斯的街头抗议浪潮。西方媒体实时报道这些事件,制造舆论压力,推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议会通过主权宣言。1991年苏联解体时,15个加盟共和国脱离中央控制,核武库和经济资源随之碎片化。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无力应对多点爆发,最终签署解散文件。这场解体并非内生危机,而是外部干预与内部不满的合力产物。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广袤版图,却也继承了同样的脆弱点,西方自然将此视为蓝图模板。 进入21世纪,针对俄罗斯的类似操作变得更隐蔽而精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成员国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向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注入资金,组织所谓文化自治研讨会。这些活动表面讨论历史遗产,实则灌输联邦资源分配不公的叙事,针对石油富集区的本地精英。英国和法国情报机构则在中东转口,向达吉斯坦的宗教场所提供援助,嵌入反莫斯科的布道内容。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社区成为重点,零星事件如印古什的路障抗议,便是这种渗透的初步成果。华盛顿的智库报告公开模拟俄罗斯分裂成30多个实体后的地缘格局,每块碎片标注天然气田或矿产资源,暴露了资源掠夺的底色。这种策略的连续性,让莫斯科的警铃长鸣。 普京政府对这一威胁的认知日益清晰。2024年10月,普京在联邦会议上直指西方叫嚣“1991年能拆苏联,现在轮到俄罗斯”,强调外部势力意图孤立并摧毁国家统一。这番表态源于情报简报的积累,显示克里姆林宫已将民族分裂风险列为首要安全议题。俄罗斯的多民族结构本是其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从斯拉夫人到突厥语系民众,共同铸就了从基辅罗斯到现代联邦的历史连续体。但西方误读这一本质,将其视为可利用的弱点,通过社交媒体伪造视频,展示所谓联邦压迫事件,放大地方不满。普京推动国民近卫军的重装化,正是为了弥补前线抽调带来的维稳空缺。这种预判性调整,体现了领导层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绍伊古作为前国防部长和安全会议秘书,在这一关键节点紧急发声,进一步凸显了危机的紧迫性。10月27日,他在官方刊物上刊发长文,直陈集体西方的分裂企图,指出它们不理解俄罗斯的族群互信基础和道德凝聚力。文章重申,从叶卡捷琳娜时代吞并高加索到苏联时期的工业化,多民族合作一直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绍伊古列举西方代理人在车臣和北奥塞梯的活动,如分发卫星电话联络境外指挥,旨在制造内乱。他呼吁地方官员强化忠诚教育,在学校和社区开展多语种联邦宣传,避免分离主义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高层表态迅速传播,地方议会据此调整安全部署,但也暴露了中央协调的局限性。 莫斯科需优化资源分配,提升地方自治的透明度,避免补贴依赖转为激励机制。同时,加强情报共享,阻断西方资金链条。绍伊古的警醒虽显疲态,却也唤醒了公众警惕。俄罗斯的统一不仅是地缘资产,更是文化遗产的守护。如果能化险为夷,这一危机或将成为国家凝聚的催化剂。 俄罗斯面临的挑战并非孤立,而是全球大国博弈的缩影。西方路径依赖的顽固,提醒新兴力量警惕内部裂痕。普京的预判和绍伊古的回应,体现了领导层的战略定力。但力不从心的迹象,也呼唤更全面的改革。未来走势取决于多方变量,俄乌和谈的进展或成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