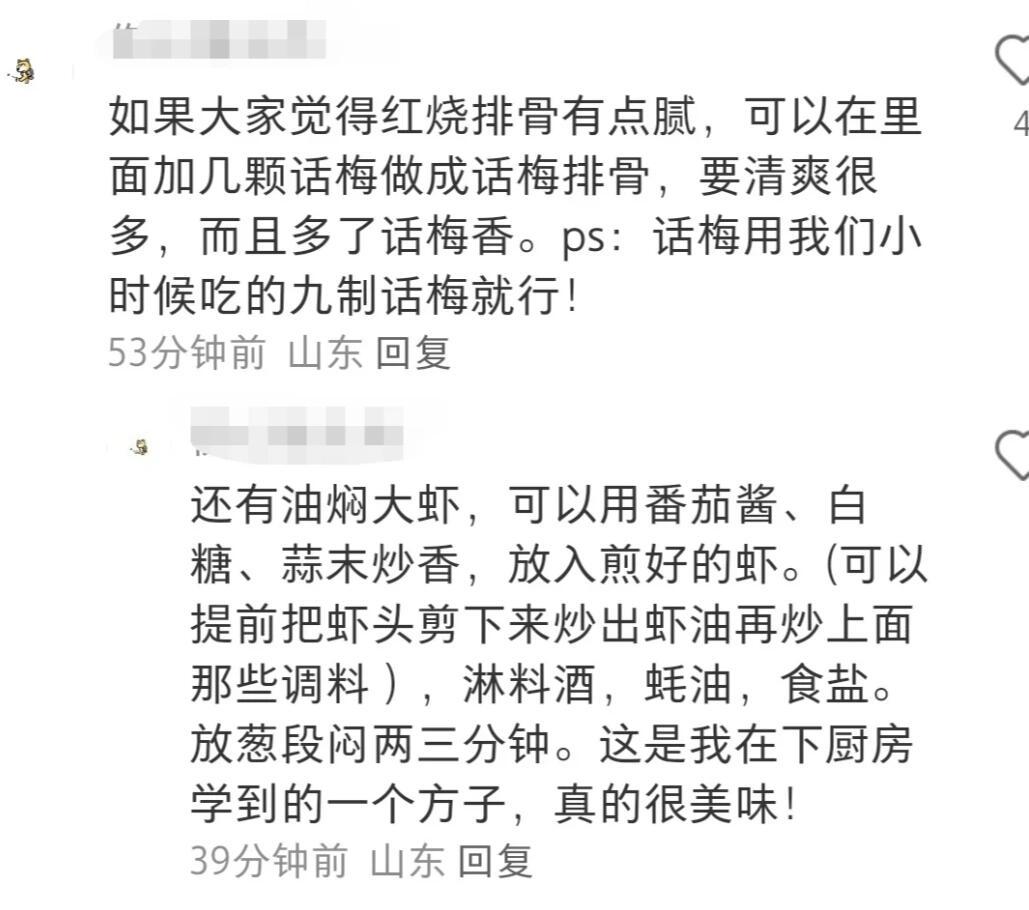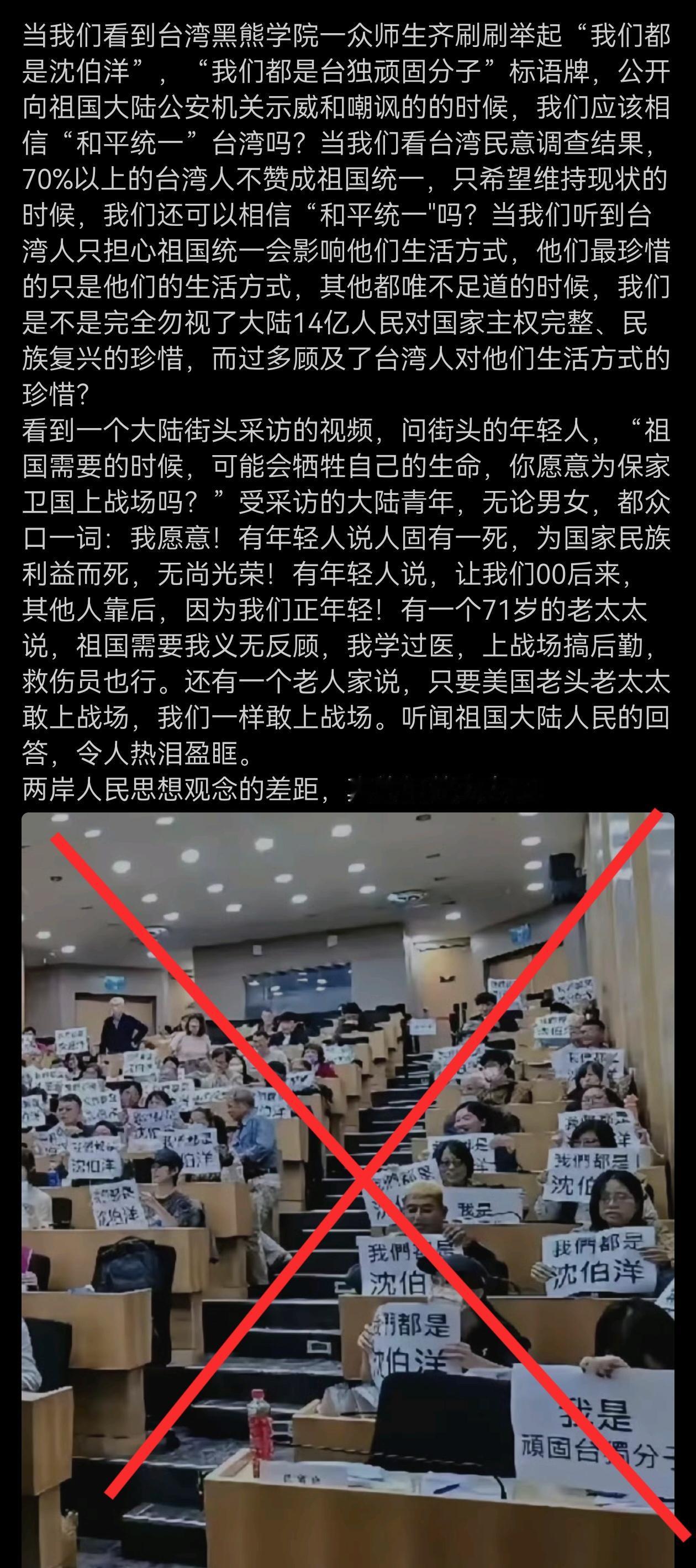性学家李银河醍醐灌顶的话: “男欢女爱的确让人很兴奋,很刺激,很快乐,但是所有的男女都要记住一个古训叫做乐极生悲,越是快乐的东西越容易摧毁你,越是刺激的东西越容易毁灭你,越是兴奋的东西,越容易伤害你。” 我是在一个当代艺术展上遇见林雪的。她站在一幅全黑的画作前,侧脸像用刀刻出来的。她说:“你看,这黑里有十一种层次。”我闻到她身上雪松与琥珀的味道,像冬天里一把温柔的火。 我们很快同居。她的公寓像个迷你剧场,卧室挂着猩红丝绒,浴室镜子上贴满金色贴纸,连喝水的杯子都造型癫狂。 她教我品尝单一麦芽威士忌的泥煤味,带我在凌晨三点的天台跳舞,在我写稿时突然抽走我的眼镜吻我。 “陈默,你活得太像标点符号了。”她咬着我的耳朵说,“我要把你变成惊叹号!” 我确实成了惊叹号。出版社的催稿电话响到第七遍,我直接关了机。连载小说断更两周,读者骂声一片。 老友约饭,我说忙,其实正和林薇在浴室地板上喝香槟。那是我四十二年人生里最快乐的半年,像坐永不停止的过山车。 直到某个雨夜。 我无意中点开她忘关的笔记本电脑,十几个聊天窗口在闪烁。置顶的那个备注是“Ares”,对话露骨得让我胃里翻腾。最新一条是五分钟前:“老地方?想你了。” 浴室水声停了。我合上电脑,手指冰凉。 她擦着头发出来,很自然地跨坐到我腿上:“宝贝,我们明天去冰岛吧?” “和谁?”我问。 她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笑得更加娇媚:“当然是和你呀。” 那晚我第一次失眠。天亮时,我发现书桌上摊开的稿纸已经蒙了层薄灰。 裂痕像病毒般扩散。我查看她手机,她夺过去摔在地上:“你凭什么查我?”我追问Ares是谁,她冷笑:“艺术赞助人,你要不要连我的画笔也检查?” 快乐成了淬毒的蜜糖。我们争吵,和好,在激烈的爱后抱在一起流泪,然后开启新一轮猜疑。我的编辑找上门,说如果再交不出稿子,就要启动解约程序。 转机发生得猝不及防。 林雪消失了。连同她那些疯狂的衣服、古怪的收藏和一半家具。客厅突然空了大半,像被洗劫过。她在餐桌上留了张字条:“快乐到期了。” 我疯狂打电话,全是空号。去她常去的画廊,新来的策展人说林小姐上周就结清了所有款项。她像一场精准策划的台风,席卷一切后从容退场。 最讽刺的是,三天后我收到她的邮件,来自一个冰岛的匿名服务器。附件是她和Ares的合影,背景是极光。她写道:“陈默,你是我最完美的作品,我把一个绅士变成了野兽。现在作品完成,该落幕了。” 我砸了公寓里所有能砸的东西。然后坐在废墟中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窝深陷,头发油腻,衬衫扣子绷掉一颗。这个野兽般的陌生人对着我狞笑。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戒毒期。我戒威士忌,戒凌晨三点的音乐,戒一切让她存在过的痕迹。生理上的戒断反应像一场重感冒,但心理上的重建如同刮骨疗毒。 我开始重新写作。第一个短篇发表时,主编惊喜地来电:“陈默,你笔下有了以前没有的东西。” 我知道那是什么,是痛楚过滤后的清醒。 昨天整理书柜,从《辞海》里飘出一张便签,是林雪的字迹:“你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句号。”现在看,这话像句谶语。她终究没能把我变成惊叹号,只是在我这个句号上,烫了个灼人的洞。 今早刮胡子时,我仔细端详镜中的脸。那道因她而起的皱纹停在眉间,像个小型的纪念碑。 我忽然明白了李银河的话。极致的快乐是蓝色火焰,温暖耀眼,但靠得太近,就会烧掉眉毛。 它用毁灭教会你:真正的完整,不在于能攀登多高的兴奋之巅,而在于风暴过后,你还能不能认出自己的轮廓。 现在我能了。 《淮南子》:“乐极则悲,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 此乃“乐极生悲”的古训源头,它指出快乐与悲伤、兴盛与衰败的转换,是天地间恒常的规律。极致的快乐,本身就孕育着转向其反面的种子。 莎士比亚:“狂暴的快乐将有狂暴的结局,正如火与火药的亲吻,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 这位文学巨匠用极其诗意的比喻,描绘了极致兴奋与毁灭之间紧密而危险的因果关系,如同“火与火药的亲吻”。 佛陀:“诸欲求时苦,得时多怖畏,失时怀热恼,一切无乐时。” 此偈语深刻揭示了欲望的真相:追求时痛苦,得到后害怕失去,失去后懊恼不堪,在欲望的驱使下,其实并无真正的快乐可言。这正说明了为何兴奋之物“容易伤害你”。 奥斯卡·王尔德:“我可以抵抗任何事物,除了诱惑。” 这句话,道出了人性在面对极致快乐与刺激时的普遍脆弱。我们往往清醒地认识到其危险性,却又难以自持地被其吸引,最终走向毁灭。 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是儒家处理情感的最高准则。快乐而不过度放纵,悲哀而不过分伤身。这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享受快乐而不被其摧毁。 极致的快乐是“高杠杆”的情感投资,收益与风险并存;“刺激”与“毁灭”是一体两面,失控的火焰终将吞噬一切;清醒地享受,而非盲目地沉溺。做快乐的主人,而非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