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邻居,一个跟我一样大的73年的牛,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早上遛弯时还看见他蹲在楼下修自行车,蓝布褂子上沾着机油,见了我笑着打招呼:“老张,你那孙子的学步车螺丝松了,回头我给拧拧。”没想到傍晚就接到他爱人的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他……他走了,突发心梗。” 我赶到他家时,客厅已经摆上了简易的灵堂,他爱人正蹲在角落叠纸钱,手指被纸边划了道小口子,血珠渗出来也没察觉。我想帮忙,目光却被他书桌吸引——那是张旧书桌,抽屉半开着,露出半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铅笔写着“小宇收”。 “那是他昨天半夜写的,”他爱人哽咽着说,“说要寄给山里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封。”我抽出信纸,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认真:“天冷了,记得添衣裳,图书馆的书够不够看?不够我再给你寄……”我捏着信纸发愣,他什么时候跟山里孩子有联系? 正琢磨着,门铃响了。门口站着个穿冲锋衣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个布包,看见灵堂“扑通”跪下:“李老师,我来晚了!”他爱人赶紧扶他,年轻人抹把脸说:“我是小宇,李老师资助了我十年,从小学到大学,他总说自己是普通工人,可我去年才知道,他每个月偷偷把一半退休金寄给我们村小学……” 布包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汇款单,最早的一张是十五年前,收款人写着“XX村小学图书角”。年轻人又从包里掏出本相册,翻开是孩子们的画:有的画着戴蓝布褂子的爷爷在修黑板,有的画着“李爷爷的自行车”,车筐里装满了书。 我想起他总说“退休金够花”,想起他那件蓝布褂子洗得发白,想起他蹲在楼下修车时,车座上总放着本《小学生作文选》。他爱人突然“哇”地哭出来:“他总说去公园遛弯,原来都是坐公交去郊区废品站,捡旧书回来擦干净寄走,膝盖就是那时候蹲坏的……” 出殡那天,小宇带来了十几个村民代表,都是当年受过资助的孩子,现在有的成了老师,有的成了医生。他们抬着块木牌,上面刻着“李老师图书馆”,说要在村里建个图书馆,让孩子们记住这份情。 回来的路上,我路过废品站,老板看见我就说:“老李前儿还来呢,说要找几本适合孩子看的童话书,膝盖疼得站不住,蹲在地上挑了俩钟头。”我鼻子一酸,转身去了书店,买了五十本儿童读物,寄往那个我第一次听说的山村小学。 现在我每天遛弯,都会绕到废品站,看见旧书就捡回来,擦干净、包上书皮,攒够一箱子就寄走。社区的王老师知道了,发动学生捐书;小卖部李婶把儿子的旧课本都翻了出来,说“也算替老李做点事”。前几天收到小宇的短信,说图书馆快建好了,孩子们在墙上画了个戴蓝布褂子的爷爷,旁边写着“李爷爷,我们想你”。 我摩挲着手机屏幕,突然明白,有些人走了,却把光留在了别人的生命里。就像他总说的“帮人一把,心里踏实”,这份踏实,现在成了我们心里的暖。这样的人生,算不算另一种圆满?
网友分享,所以就这段位没有上位也是正常的!
【1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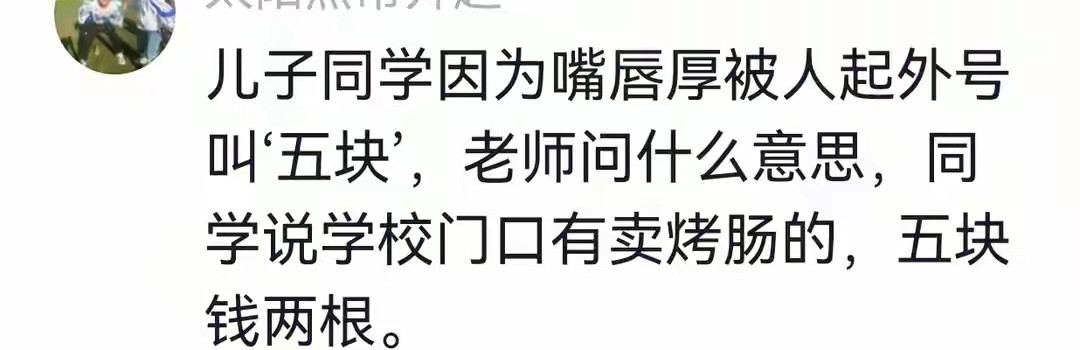

![蒙牛如果真敢用了这样的广告语,伊利绝对会与其不死不休![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233283810755639882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