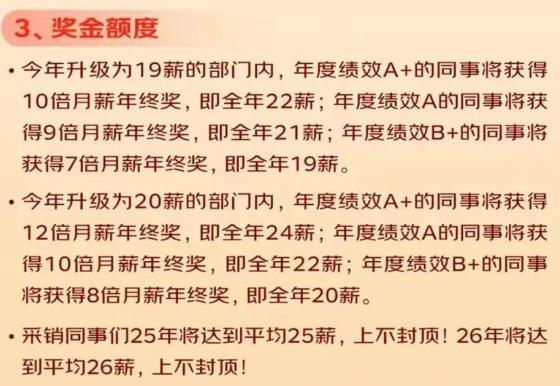夕阳下的文件袋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风带着点初冬的凉意,吹得我裹紧了大衣。我坐进车里,降下车窗,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手里攥着一个旧帆布包,一步一步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 “以后别联系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他没回头,只是顿了顿脚步,轻轻点了点头。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落寞得不像话。 我发动车子,正要驶离,目光无意间扫过副驾驶座。那里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是他刚才落在这儿的。 我皱了皱眉,伸手拿过来,指尖触到纸袋的瞬间,竟觉得有些沉。 打开封口,里面没有离婚协议的副本,也没有多余的叮嘱,只有一沓整整齐齐的单据和票据,用一根红绳捆着。 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收据,日期是八年前,我父亲突发脑梗住院,上面写着“住院押金五万元”,收款人签字那一栏,是他的名字。 我手指微微发颤,继续往下翻。 有药店的购药小票,密密麻麻的,大多是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的进口药;有医院的缴费单,从挂号费到复查费,一笔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有超市的购物清单,上面列着奶粉、燕麦、无糖饼干,都是我父亲爱吃的;甚至还有几张出租车发票,时间大多是凌晨,备注栏里歪歪扭扭写着“送叔叔去急诊”。 八年来,我忙着在职场上厮杀,从月薪八千熬到五万,忙着买名牌包、买豪车,忙着抱怨他的平庸、他的不上进,忙着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像一条跨不过去的鸿沟。 我总说他配不上我,说他的八千块工资,连我一个包都买不起。 可我忘了,我父亲住院的那半年,是他每天下班就往医院跑,替我守夜,替我给父亲擦身喂饭;忘了他省吃俭用,把攒下的年终奖全给我父亲买了康复器械;忘了他从不抱怨我加班晚归,只在餐桌上留一盏灯、一碗热汤;忘了他每次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部分钱转给我,只留一点够自己吃饭坐车。 这些单据,有的边角已经磨损,有的上面还沾着淡淡的水渍,显然是被他小心翼翼地收藏了很久很久。 我突然想起,刚才在民政局签字的时候,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他说:“家里的东西,你要是不想要,我回头让人搬走。” 那时候我只觉得烦,觉得他磨磨蹭蹭,连离婚都这么拖沓。 可现在,看着这一沓薄薄的、却又重逾千斤的单据,我的眼眶突然就湿了。 车窗外,夕阳渐渐沉下去,把半边天都染成了橘红色。地铁站的入口处,他的背影已经看不见了。 我趴在方向盘上,眼泪无声地落下来,砸在文件袋上,晕开了收据上的字迹。 原来,这八年里,我眼里的“差距”,从来都不是钱。 是我忙着往前跑,忘了回头看看,那个一直站在我身后,用他微薄的八千块工资,默默撑起我父亲的晚年,也撑起我所有体面的男人。 车外的路灯亮了起来,暖黄的光透过车窗照进来,落在那些单据上。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带他去见我父亲时,局促地搓着手说:“叔叔放心,我虽然赚得不多,但我会对她好,会对您好。” 那时候,我笑着说他傻。 现在才懂,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做到了。 而我,却亲手把他弄丢了。 晚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丝凉意。我握着那个文件袋,指尖冰凉,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着,疼得喘不过气。 远处的地铁站,人来人往。 再也不会有一个人,会在夕阳下,那样落寞地走向那里了。
一个保姆在雇主家干了22年,她60岁时,雇主的儿子说:你年纪大了,我们打算辞退你
【19评论】【1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