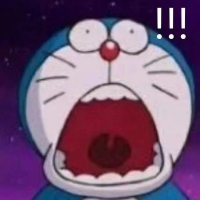十五岁那年,我被人贩子带上黑车卖到山里。
买我的男人联合他妈,强迫我替那个家传宗接代。
我抓住每次机会想逃,都被打到遍体鳞伤。
隐忍无止境的拳打脚踢将近七年,我终于大仇得报,解救全村。

初中毕业那年我刚十五岁,没考上高中,顺理成章跟村里人到广东一家制衣厂打工。
厂里的员工宿舍很是偏僻,路边经常有黑车出没。
一天中午路上没什么人,我正好走路回去。
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闯入眼帘,在我身边鬼祟地周旋。
车内下来一个模样油腻的光头,露着邪笑把我逼到车门边缘。
我异常恐惧,还没喊出声他便拖住我往车里带,在我耳边发出狞笑:[这里连个监控都没有,喊破嗓子也没用。]
我紧扯住车门,他却顺势蒙住了我的口鼻。
等醒来,我已经躺在一个黑黢黢的地方,摸着像是张禾草铺就的木板床。
屋内跟进不来光似的,阴森可怖。
身体某处传来钻心的疼,我隐隐有不好的预感,挣扎着起身。
屋外响起一阵动静。
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约莫三十来岁的男人手里点着盏煤油灯,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以后这就是你家了。]
我如遭雷劈,匍匐着下地朝门边跑去。
迎面闪现的一抹人影,吓得我差点魂飞魄散。
只见一个摘除了左眼球的老太婆,一脸凶相地拦住了我。
[人醒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她的嗓音嘶哑,跟巫婆般阴沉。
我推搡她一把,跑出门外才发现周边都是浓密的山林。
男人快步追了出来,从后背扯住我的头发,[不知道成没成,今晚再试试。]
老太婆喘着气,没瞎的那只眼朝我身上打量,[身段还行,脸庞子也嫩,可得把握好了]。
听着他们的污言秽语,我嗓子都快喊哑,哀求他们放我走。
男人却扯住我往屋里带,[买你回来想跑,你必须给我添几个儿子。]
[今晚妈给你把风,好好教育她。]老太婆嗓音中透着股兴奋。
那晚,在声嘶力竭的求救声中,我再次被强暴。
后来我才知道,那畜生叫刘家生,花了三千块从人贩子那买的我。
我不知道被卖到了什么鬼地方,只知道所在的村子出门难见天。
四面环山,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踏进这里,这辈子我十有八九是出不去了。
2
刘家一贫如洗,住得还是拿油毛毡当屋顶的泥瓦房。
泥墙遇到风雨洗刷,随时可能倒塌。
我变着法儿想逃,可次次都被抓回来,少不了被打得遍体鳞伤。
在承受完刘家母子持续的凌辱后,三个月后我怀孕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的肚子渐渐显怀。
[吃下去,可别饿着我大孙子。]刘母逼近丢了盆饭给我,满口黄牙的嘴漏着一阵臭气。
我极度嫌恶地撇开脸。
刘母脸色立刻一拉,[受了那么多教训还不服?进了这家我就是婆婆,什么都得听我的。]
我气不过瞪她一眼,沉默着想往屋外走。
[我看她还是想跑,绑起来。]
刘家生赶紧撒丫子追了过来,拽着我朝漆黑的卧室拖。
刘母则照例到屋外锁紧大门。
我的身体一阵阵发冷汗,撞在屋里那堆破烂家具上。
刘家生捡了根麻绳绑住我的双手,手不停朝我两条胳膊上的嫩肉掐。
我痛到钻心,满眼都是痛恨,[你们一天不放了我,我迟早会跑。]
刘母守在屋外,虽然瞎了一只眼,耳朵却能穿墙。
[外边的婆娘脾气大,不给她点颜色瞧瞧,得长八条腿。]
刘家生掐我的力气,不自觉变大。
我怒火中烧,哆嗦着:[腿长我身上,我想跑,你们根本拦不住。]
刘家生被激怒,干脆把我扔回床上,[再敢跑,老子扒下你一层皮。]
[这胎是女娃就继续生,直到给我生出孙子为止。]刘母守在窗外,恨不得视奸屋内。
刘家生伸出恶心的手摸我的脸,[听清楚了,咱妈在教你做人。]
我不说话,呸他一口。
迎接我的,是一顿新的殴打。
听着我的阵阵惨叫,刘母笑声猖狂,[挑着点皮肉,可别伤着肚子。]

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除了肚子逃过一劫,我全身都没留下几处好肉。
屋里乌漆抹黑,连仅有的一盏煤油灯都熄了。
刘家生发泄完,到旁边去点灯。
想到以后很长时间都要面对这对禽兽母子,我情绪崩溃到大哭,骂他们杀千刀的畜生。
见我哭闹,刘家生却始终面不改色,劝我老实生几个儿子才有好日子过。
我想着不吃东西,跟肚里的孩子一起饿死。
可我一开始绝食,他们就蛮横地往我嘴里塞东西,跟喂鸭子似的。
食道被堵吐不出也咽不下的滋味,生不如死。
后来,我又跟刘家生母子闹了好几次。
可他们轮番折磨我,捆绑手脚,关小黑屋几乎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有时候连大小便,我都没办法按时解决。
在受够各种身心虐待后,我终于心如死灰,表面变得乖巧安静。
刘家生得管着家里的农活。
刘母则多了一项职责,那就是看住我。
她说家里不养闲人,总逼我帮她做家务。
基本上天刚蒙蒙亮,她就会在屋外制造声响,闹着我起床劈柴烧饭。
我想弯腰捡柴火,后背却传来一阵剧痛。
[动作利索点,跟没力气的鸡仔似的,怎么伺候我?]
我回头瞪她,便见她拿着根鞭子,正对我耀武扬威。
面目可憎到极点。
我被教训怕了,不敢跟她顶撞,只得故意伪装顺从,苟且安稳了一段时间。
一天,刘母突然肚子疼着急上厕所。
家里厕所还是外边那种旱厕,她跑得急,忘了把我关回屋里。
巧的是,刘家生也不在家。
见时机难得,我紧急翻箱倒柜,揣着几十块钱往外跑。
才跑出去几百米,附近就有两个村民涌了出来。
他们就像两条疯狗,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住我,一点点把我往回逼。
我强自镇定,慌乱操起田埂上那根木棍要跟他们拼命。
他们根本却不为所动,把我当成被捏住脚的蚂蚱。
[这肚子得有七个月了?要摔着流产什么的,村里头可没有医院。]
刘母连裤头都没系好急匆匆赶回来,见是我被拖回去,狠狠揪住我的耳朵。
[跟我玩阴的?我看你是苦头没吃够。]

我被他们像抬牲口一样,抬回屋内锁了起来。
刘家生很快从田里回来。
我头发散乱着蜷缩在墙角,目光空洞,一直嚷嚷着想逃,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刘母一把扯住我的乱发,独眼露着凶光,[把你关到鸡棚,跟那群鸡睡。不信还能不老实。]
刘家生脸色扭曲,半个字都没有说。
我被扔进屋外肮脏的鸡笼,身边是他家养的十几只鸡。
地上的积水混着一坨又一坨鸡粪,奇臭无比。
刘母在门外骂骂咧咧。
看着那道生锈的铁门,我无助到流泪。
那晚,我蜷缩在阴冷的地上辗转难眠。
时不时有鸡来啄我的身体,成为我一生的噩梦。
难道我真的不能逃出魔窟,死都要死在这?
我越发的不甘心。
隔天,我在刘母忽远忽近的骂声当中醒来。
[起来劈柴,别以为在这就能睡懒觉。]
我身上奇臭无比,浑身骨头像散架一般。
在翻身的时候,藏在衣服内兜的几十块钱掉在地上。
刘母当即过来抢夺,[贱骨头,还想偷了家里的钱跑?]
她再度拉扯我,对我谩骂殴打。
话里话外暗示这附近都是眼线,我怎么样都逃不了。
心底的愤怒跟痛恨持续升腾,让我对身边的一切恨到咬牙切齿。
也许总有一天,我也会变得跟这群野蛮不开化的村民一样,活脱脱成为魔鬼?
大不了一个死。
想通后,我重新拾起要逃出去的念头。
不过得先生下孩子,再做打算。
之后我变得越发沉默寡言,似乎渐渐被磨得没了脾气。
那年冬天格外冷,我躺在屋里生孩子。
可惜过程并不顺利,我难产痛苦到几乎昏厥。
关系到传宗接代,刘家母子自然着急。
商量下,刘母到村里请回一个四五十岁的接生婆。
在完全没有卫生条件保障的情况下,我生下一个女儿。
刘母脸色阴沉,破口大骂。
[头胎就生了个赔钱货,长大后就得跟野男人跑了。]
[就像你妹,完全不中用。]
我听说过一嘴,刘家生还有个妹妹,外出打工时跟男人跑了再也没回来。
刘家生有些不耐烦,[才生完,杀只鸡给她补补。]
刘母狠狠剜我一眼,[想吃鸡?有口饭吃就不错了。那些鸡,我得留着给你补身子。]
5
我丢了半条命,虚弱地躺在床上坐月子。
见刘家生抱女儿过来喂奶,我却不想跟她亲近。
这孩子承载了我所有的不幸,让我很难对她有半点感情。
更多的是恨。
等稍微能下地,刘母又马上使唤我做事。
我忍气吞声,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卖力干好家务。
时间一久,我稍微得到他们的信任,也渐渐摸清楚这对母子的活动范围。
除了去山里几块地干活,他们偶尔会步行几公里,到村里唯一的小卖部买东西。
有小卖部的地方铁定跟外界有往来,我暗中留了个心眼。
刘家生似乎猜到我的心思,就算带我出门,也从不让我跟村里人有任何接触。
又等了很久,我才等到一个新的机会。
那天我难得睡到自然醒,屋外没有任何动静。
按着平时,刘母铁定在门外又敲又打逼我起床了。
察觉到异常,我撇开女儿招娣来到屋外。
只见刘母卧室的门微张,里头时不时传出痛苦的喘息。
我故意敲门,[怎么了?]
刘母在她那肮脏发臭的床上打滚,以怨毒的眼神看着我。
[还死在那做什么?我肚子疼,快带我找医生。]
在这个家待了快三年,老太婆难得说了句让我身心舒爽的话。
我眼前一亮,很快故作为难。
[村里哪来的医生?你忘了我生孩子,还是你找的接生婆?]
刘母挣扎着想爬起,[你就是没安好心,快过来扶我。]
我忍住憋笑,在床边眼睁睁瞧着她却是不动,[那以后能不能别打我?]
刘母求生心切,额头冒着冷汗捂住肚子,[过来,不然阿生今天就能打死你。]
我咬碎牙往肚里吞。
按照刘母指示,用家里的一辆推车,推着她到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家。
医生帮刘母把脉,开了两副草药。
我听说刘母有肠子便血的毛病,应该有十来年了。
而且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好能到县城去看看。
刘母虽然虚弱,却还是防备地瞪我一眼。
[那也得等家生回来。别看这婆娘表面老老实实,撒蹄子就能跑了。]
我眼底闪过难以抑制的兴奋。
推了刘母回家,她在刘家生面前拱火,说我看她疼了老半天无动于衷,分明想害死她。
刘家生手里的烟头还冒着浓烟,朝我的胳膊直接扎了过来。
[这么多年还没学会伺候我妈?以后还敢不敢?]
我疼到发出惨叫,一个劲求饶,[不敢,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