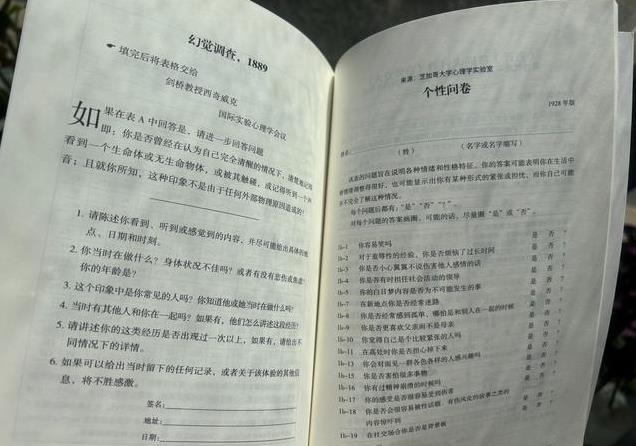通过《我正常吗》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正常”是一个复杂且多变的概念,通过作者萨拉的研究和亲身经历,让我明白自己无法“正常”,也不再试图去追求“正常”。

一,
我国古代 医术中有望闻问切,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五官就能知道你身体有没有什么病,甚至通过一个人的五官,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个善人还是恶 人。
在英国也有过类似的报告,1883年,高尔顿通过合成图的方式,展示了典型病患与罪犯的面貌。
高尔顿指出:罪犯邪恶面孔逐渐消失,面向之下人类共同的特征得到了体现。他认为,他合成的这些看起来很柔和的人像,虽然不是罪犯,却是容易犯罪的人。
所以,在那个时代,“你长着一张不好相处的脸”“你看起来就是个病秧子”是非常主观的判断。
如今,见到大千世界的我们,会更懂得“日久见人心”的道理。

二,
很多人会因为“我是否正常”这问题让自己陷入比较和内卷之中。
有人会因为自己体重超过BMI18.5-25kg/m2,就会认为自己体重不正常、不健康,就算医生强调没有病理症状就是健康。
有人会因为自己开始近视要带眼镜而焦虑,而当医生说10%的人视力正常,90%的人视力都不正常时,视力不好的反而“正常”了。
还有太多人因为穿着而焦虑,以前大家注重衣服款式,现在人们又开始注重穿衣比例,似乎自己还不会穿衣打扮就是“不正常”的,就是过时,落伍。
这种定义往往是不稳定且主观的,因为社会期望和标准在不断变化。

三,
“正常”这个词源自1801年,意大利神父和天文学家朱塞普·皮亚齐,他们在寻找火星和木星的时候,发现了一颗新星——谷神星。但是有一天他们发现这颗星距离太阳过近无法观测而消失了。
后来,24岁德国数学家高斯通过一个数学公式得出了一个平均值,并且绘制了一张图,认为谷神星将出现在这条曲线显示的正中心处。没想到还真的应验了。
于是,平均值的概念就出现了,这也作为天文学家避免曾经出现误差的一种方法,测量平均值,就需要大量的测量,也因此,在平均值附近的数据才算是“正常”。
所以,“正常”一开始是数学属于,用于角度、方程和公式,人并不需要被计算,不需要“正常”。
可如今,“正常”有了很多的寓意,正常的反面,可能是极端或特殊,可能是不寻常和奇怪,也可能是病态、患病。


四,
在《我正常吗》这本书中,作者萨拉·钱尼也曾问过自己“我正常吗?”的问题,
萨尼从小就是个高个子女孩,所以当别的女生穿36码鞋子的时候,她已经穿43码鞋子了。当别的女生都喜欢穿裙子时,她宁愿穿上男孩子的衣服做着酷拽的动作。生理原因,让她无法成为“平均值”里的一员。
当她上大学去了伦敦,她发现自己依然无法融入其他女孩圈子,因为自己不太爱说话,也不太爱聊八卦,更不太会关注穿着。
后来,她开始深入阅读医学和科学史、殖民主义和性别、酷儿理论和残章的社会模式等相关书籍,萨拉对于正常的概念逐渐变得不那么自我和狭隘了。

五,
正常真的存在吗?人类的任何行动、习俗、惯例、信仰或概念都可以被纳入同一个尺度衡量。
然而,社会期望一直在变化,比如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梗。
更准确的说,“正常”是当下社会为了制造出理想化的形象所提出来的改造人类的方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用自己的观念来打破“正常”的界限,创造“新正常”。
有时候,只有发现其他人与我们期望的不同时,我们才会注意到社会的正常标准是什么。当这些标准与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突时,我们才会更注意到这些标准本身。
那些与我们预期一致的事情,容易被我们所忽略,而这种看似无形的正常,就形成了社会历史的一抹记忆。
萨拉指出:正常是社会上的共享的特征,即“平均值”,完全“正常”的人比我们预期的要少,所以“正常”成为了一种预期的成就,是虚构的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去追求“正常”,但也要接纳并超越“正常”的束缚,追求个性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