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绛宇/文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复合手术外科主任
我记忆中的Juha教授
读文献又看到尤哈教授的名字,触发了我写一点东西追忆尤哈的想法,一些话沉在心里,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尤哈的全名是Juha Hernesniemi,当地人习惯叫他Juha,咱们中国人叫他Juha教授,按说应该是Hernesniemi教授,可是“赫讷思涅米教授”太拗口,我们都喊他professor Juha,他是神经外科界的前辈,背后我们也会称他“老尤哈”。他也习惯了这种称呼,并不纠正。
我个人最早谈论Juha,好像是2010年,或是2012年的一个下午,神经外科郭锁成教授经一侧翼点入路,花费两三个小时,解剖开了双侧的侧裂,居然没找到动脉瘤。他电话我去手术室,看了CTA图像,这是个颈眼动脉瘤,CTA误报告为“后交通动脉瘤”,医生被带偏了,切除前床突就能找到动脉瘤。郭教授完成手术后,我又对他说,前不久到巴黎参加Jacques Moret教授领导LINNC会议(Live 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 & Neurosurgery Course),听到芬兰的Juha教授的一个关于脑动脉瘤外科手术的讲座,大为倾倒,Juha的某些高超技巧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我是一只年轻的井底之蛙----Juha曾经一侧开颅夹闭双侧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简直神乎其技。老郭你误打误撞解剖了双侧的侧裂,水平直追Juha。老郭受到鼓舞,一个月后真的就做出了一侧翼点入路夹闭双侧大脑中动脉瘤的精彩手术。
也是那次巴黎的会议上,听Moret教授称呼Juha 为“鸠阿”,心里生出疑问。Juha是个名人,神经外科专业的国际名人,在上海读书时,听顾斌贤教授给我讲过“尤哈”的故事,是我记错了?还是顾教授念错了?后来我科段光明主任又给出一个版本,他当初在301医院读博士阶段,曾接待过Juha教授来访并与之合影,段说,他的名字念做“鸠哈”。仨读音,谁正确?我想,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名字,打小儿他父母喊他名字的发音才正确。这个除非能当面问他本人。

四时冬复春,造化一机会。世事就这么奇妙,2017年12月,Juha从芬兰退休,接受省医院的聘请,来签署工作合同。我赶紧问他,在你的家乡,你的名字怎么发音?尤哈?鸠阿?还是鸠哈?Juha说:尤哈。总算得到权威答案,再不会错的。
2018年6月,尤哈教授正式开启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职业生涯。世界著名神经外科大师来到身边,神经外科各位医生本着“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的古训,都把疑难病例拿来,请尤哈教授帮忙手术。尤哈是喜爱做手术的人,来着不拒,对于手术量,更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恰好我也有一个为难的患者,左侧功能区的一个大型脑动静脉畸形(AVM),并且有豆纹动脉深部供血。我请尤哈会诊,能不能手术切除?他反问我能不能先把豆纹动脉供应那部分畸形给栓塞掉?这是外科手术的难点。我把他要求的那部分栓塞后,尤哈把剩余的畸形血管做了漂亮的切除,术后患者没有任何神经缺失,恢复良好。尤哈教授本人不会神经介入技术,但他完全了解,对介入来说,豆纹动脉也很难处理,所以他夸奖我Great man! 我就不失时机地把他的赞美写在纸上,照相为证。

我的专业是脑血管复合手术外科,通常会把复杂脑AVM放在杂交手术室,栓塞主要供血动脉后,立即开刀切除畸形血管团。在一个手术台上,由我一组医生完成介入和外科技术,很累。与尤哈合作这例手术之后,我大受启发,为什么不分期处理复杂脑AVM呢?先介入栓塞,一两天后开颅切除,效果同样好,医生也不那么疲惫,病人甚至更安全。我把这个模式叫做“联合手术”,以区别于复合手术。这几年用联合手术模式完成了几十例脑AVM手术,不但病人效果好,我也觉得身心轻松许多。
尤哈教授,如你所知,他特别擅长脑动脉瘤手术,更是一个快刀手,曾经25分钟完成一台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夹闭术,“skin-to-skin”,尤哈说。可是时代毕竟变了,大部分脑动脉瘤多可以通过微创的介入技术治愈,我院每年收治脑动脉瘤上千例,九成以上患者选择了介入治疗。尤哈宝刀未老,留给他开颅的动脉瘤却不多,时间长了,各位医生积攒的疑难病例也“消耗”完了,尤哈不能尽兴,有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落寞,就找医院提意见,你们给我薪水,也要让我劳动呀。
2019年秋,医院安排我带一组医生到“Juha国际神经外科中心”病区工作,加上段光明、白卫星两个医生组,充实Juha团队,增加尤哈的手术量。于我,是得到了和国际著名大师朝夕相处,近距离学习他的技术和治学方法良机。
尤哈号召大家学英语,因为国际交流太重要。别说国际交流,离开英语,科内交流就无法进行。每天早上科室进行病例讨论,讨论每一例手术方案,当然得用英语和尤哈交换意见。尤哈鼓励大家说,学外语一点儿都不难,他本人就懂五、六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什么的。并且他要给各位中国医生树立榜样,力争半年内掌握汉语----我们都小小吃了一惊----他真的就请了一个家庭教师,坚持学习。我科白卫星、段光明主任,还有几个年轻医生,英语都很流利,其他医生也都在尤哈的感召下努力提高了英语水平。两年后,尤哈沮丧地认输,说他记住了七八百个中文词汇,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听得懂他的中国话,汉语太难了。我们努力不笑出声,安慰他说,他的“你好”和“谢谢”发音很清晰,能听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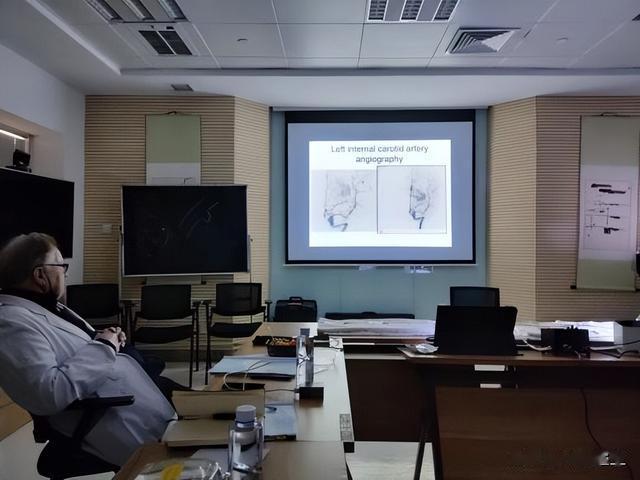
无论工作和生活,尤哈都在努力适应中国环境。可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产生不同的行为逻辑。有一个16岁的男孩,癫痫发病,左侧运动区一个很大的AVM,慕名来找尤哈诊治。尤哈教授对脑AVM有深入研究,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中风协会在2017年发布的《脑动静脉畸形的管理》中专门引用尤哈的研究成果:Ondra等人和Hernesniemi等人对160例和238例未破裂AVM患者进行了平均23.7年和13.4年的随访,发现出血的年风险通常为2%至4%。对于一个16岁的患者来说,未来人生还有几十年,也就是说,几乎可以确定患者将来会发生AVM破裂,脑出血。患者家属求治心切,尤哈亲自和患者家属沟通,彼此交换了看法。谁知患者家属一再犹豫,既不出院,也不手术。尤哈感到不理解,Why? 我只能劝尤哈,尊重患者家属的决策。他哪儿知道独生子对中国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功能区病变,如果手术造成患者残疾,还能拥有阳光、自信的心态吗?我们拥有一个残疾人友好的社会吗?足足考虑了两个星期,患者家属才定下手术的决心。尤哈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揣摩出别的意味。术后尤哈对我说,I found you Chinese people don’t trust each other,中国人互不信任。我说sure,that’s the point. 可是你要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民风是官风的映射。我的英语烂,翻译不出这句话给他听。况且,也不好给“国际友人”讲这个内容吧。


技艺高超,声望卓著,见多识广,所以尤哈是个自信又倔强的老头儿,还坚守着属于他的时代的荣光。比如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尤哈总是斩钉截铁地反对介入栓塞而建议开刀夹闭,他说,it is guilty to treat one MCA aneurysm without clipping,不开刀简直是犯罪。虽然他说过很多次这句话,我们并不严格执行,因为科技发展了,一部分大脑中动脉动脉瘤非常适合介入治疗,甚至比开颅夹闭更容易、效果更好。他老人家最快的动脉瘤手术是25分钟,而我介入栓塞大脑中动脉动脉瘤,最快成绩不到10分钟。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隔三差五的,人们就“主动居家不外出”了,“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的外国人也不例外。尤哈感到极大的不适应。2021年11月,一个大风冷雨的晚上,尤哈乘飞机回了芬兰。又过了1年多,他去世了。时间久了,我们就记不清他老人家反对介入的原话是怎么说了。段光明主任说好像是it’s crime to treat…,我疑惑,是crime还是guilty? 段主任略想了想,说应该是guilty,稍微温和些,听起来不那么罪大恶极。

事实上,尤哈成了脑血管病医生的后盾。我们敢于收治各种困难病例,反正有尤哈给兜底。介入手术我们自己做,相对简单的开颅手术我们自己做,困难的,给尤哈。尤哈得到的病例往往是高难的,自然就吃过几次亏----有几次干干净净的手术,术后病人偏瘫了----尤哈困惑良久,得出结论说,你们中国人的脑血管very terrible,因为中国人吃了太多Mao’s pork。确实,颅内血管广泛动脉硬化似乎是中国人的专利,开颅后,经常看见满脑的动脉血管都是黄颜色,而欧美白人很少这种情况,他们的动脉硬化斑块更集中在颅外段,颅内血管红润光滑。一些脑动脉硬化严重的动脉瘤患者,连动脉瘤颈都是黄色斑块,大概是夹闭动脉瘤时,斑块脱落,造成远端血管栓塞,偏瘫。尤哈来中国,吃过几次毛氏红烧肉(Mao’s pork),很喜欢。他推己及人,认为所有中国人每天在吃红烧肉,联系到高脂血症是动脉硬化的主要病因之一,就得出前述结论。我反对说,中国人不富裕,哪有欧洲人吃肉多?我倒认为,植物油才是中国人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煎、炒、烹、炸,是中国烹饪的精髓,尤其是底层人民经常光顾的中低档餐馆,一盘菜半盘油。还有空气、水、食品污染,等等,不一而足。唉,这是能说的话题吗?
不但喜欢红烧肉,尤哈也喜欢喝酒,还吸烟。他对于香烟品牌很有执念,基本上只吸中华烟,如果递给他别的香烟,哪怕价格更昂贵,也会遭到不留情面的拒绝----他毕竟是个耿直的外国人,不虚伪。而喝酒,却十分没有品位,凡是白酒,他统统叫做“茅台”,他爱二锅头与爱茅台的程度相当。2023年3月16日,尤哈返回郑州,虽是仲春时节,那天却下了一场大雪,迎接尤哈时,我说他到底是圣诞老人的老乡,有大雪陪伴。这句马屁拍得他微红不疼,兴高采烈。晚宴特意准备了中华烟,尤哈却戒烟了,他说,芬兰是最适合戒烟的国家,即使在自己家吸烟,也会被邻居投诉。他还说,他准备90岁的时候再开戒。酒没戒,今晚是河南本地白酒,仰韶酒。尤哈照例问,茅台?我也照例回答,yes, a kind of 茅台。于是就愉快的碰杯,畅饮。

2023年的3月和6月,尤哈在中国参加了几次学术活动。以河南省各大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为主体,成立了“Juha脑血管外科俱乐部”,并举办了两次学术会议,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神经外科陈小兵主任专门请开封的名家创作几张书画赠予尤哈教授,后来我去芬兰赫尔辛基,看见这幅画放在尤哈家的书房里;6月,结束“少林脑血管病大会”之后,我陪同尤哈访问了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张新中院长,周文科教授,王玉峰教授共同主持了尤哈教授的学术报告。这大概是尤哈生命中最后的学术活动,也是他心情轻松愉快的一次社会交往,宴席上的黄河鲤鱼“游到”他面前,尤哈已经是个河南通,熟练地指着鱼头说,得喝酒?大伙儿哄然笑说:鱼头一对,大富大贵,仨酒!




半个月后,就在那个6月底,一个星期二的晚上,结束一天的手术刚回到家,忽然接到Fitri----尤哈的女友----从印度尼西亚来电,Fitri呜咽着,说尤哈摔倒了。我问伤到哪里?胳膊?还是腿?骨折了?Fitri说是head injury。我有些吃惊,他是脑外科专家,居然伤到自己的头颅。又问尤哈现在情况咋样了?Fitri说had passed away。这夜于我是噩耗惊传废夕餐,往事萦回不成眠。据说,那天的微信朋友圈已有关于尤哈的坏消息,所以,直到半夜,不停接到全国各地神经外科同行们关心尤哈的问询电话,以至于我怀疑,在中国,“尤哈死于脑外伤”这个消息,都是从我这儿传出去的。


2023年7月底,尤哈的葬礼在赫尔辛基的一个专门的教堂举行,李天晓教授、段光明教授等我们一行数人前去芬兰与尤哈作最后的告别。尤哈的一个学生,在德国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Ferzat Hijazy 对我说,尤哈死于肺栓塞,不是脑外伤。尤哈不小心跌倒,造成上臂骨折,他老人家固执,不住院,认为自己是医生,在家休养,自我治疗即可。谁料到几天后突然肺栓塞,死亡。下肢骨折并发肺栓塞比较常见,尤哈却是上肢!Ferzat Hijazy给我们看了他手机上保存的尤哈的上肢X光片,又补充说,尸体解剖证实了肺栓塞。
尤哈终年76岁,没有活到90岁他想开戒吸烟的年龄。
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也夫!
薛绛宇,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复合手术外科主任,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专业是脑和脊髓血管病,曾在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和美国费城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Hospital 脑血管外科进修。
发明脑动脉瘤的“超大弹簧圈栓塞术”,第一执笔人撰写“颈动脉脉性闭塞的开通手术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