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雨别
编辑|雨别
《——【·前言·】——》
苏轼是北宋的奇才,写诗作词画画治政样样拿手,百姓爱他同行敬他,朝廷偏不待见,几次三番把他发配到地方。
乌台诗案、谪居黄州、远放海南,官职忽高忽低,命运反复无常。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江湖地位顶天的文坛大咖,翻开苏轼的试卷眼睛一亮。
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行文大气,欧阳修拍板,头名。
苏轼一鸣惊人,迅速成了京城里的“网红”,文坛前辈如欧阳修、梅尧臣,都对他青睐有加,大家都说这年轻人有戏,朝廷会重用他,但十年后命运翻转,他的仕途并不顺遂。

几年后他通过了更高难度的制科考试,被授为“凤翔签判”,开始地方政务生涯,凤翔是偏远地区,和京城没法比。
苏轼没闲着,政绩卓著写诗练字,苏家遇变故,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回家丁忧。
这一待就是三年,仕途断档,重回政坛时京城已经变了天。

宋仁宗去世,新皇宋神宗登基,新官上任三把火,神宗决定改革,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目标是强国富民,可这些法令一推行,各地怨声载道。
苏轼看到问题,他不反对改革,但觉得王安石太急了,这么大的工程得一步步来,他直言:“治国如治病不可猛药去疴,反伤根本。”但新皇和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去。

苏轼的态度得罪了新党,变法派认为他唱反调不支持大局,他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杭州是个好地方,风景优美,可对苏轼来说这就是“边缘化”。
在杭州,他的治理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湖修缮他组织民工筑堤,水利管理他修建水闸,保障农业灌溉。
百姓感激他爱戴他,可这些政绩没能让朝廷重视他,他继续被调动,先是密州再是徐州。

密州时期,苏轼完成了传世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词里写得豪迈,可他心里压抑,朝廷不给机会,他的施展空间越来越小,徐州时,他抗洪救灾有功绩,但仕途仍无起色。
1077年,他调任湖州,刚到任就上书朝廷,说新法的问题,动了变法派的神经,紧接着他的麻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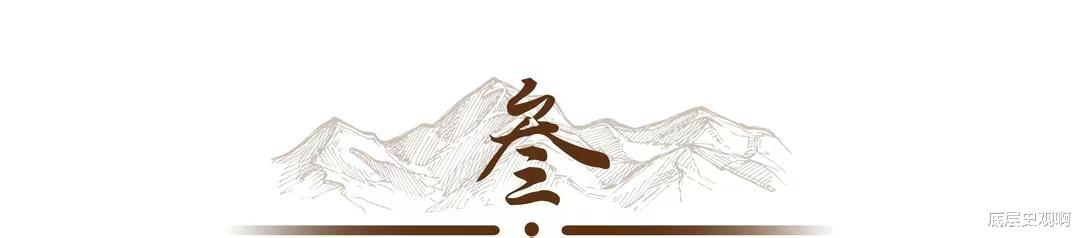
1079年苏轼的新任职地是湖州,他刚到便上书朝廷,写了一篇《湖州谢表》,表面是感谢皇帝的提拔,实际上暗藏对新法的讽刺和批评。
文章被王安石新党的党羽看成挑衅,再加上之前的积怨,苏轼被盯上了。

新党开始搜集他的“罪证”,苏轼的诗文平日里本就爱用讽刺语调批评朝廷结果成了把柄,有人将他的诗断章取义指控他对皇帝不敬、讽刺朝廷,最终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他逮捕。
这场案件史称“乌台诗案”,苏轼被押解回京,关进御史台的大牢,当时他命悬一线,狱中甚至写下遗书做好赴死的准备,狱卒对他念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案子最后并未定性为叛国大罪,在好友的周旋下苏轼保住了性命,但被贬到黄州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这是他仕途的重大转折,从京城才俊变成地方弃臣。

许多旧党官员奔走营救,试图为苏轼说情,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朝廷没有将乌台诗案定性为“叛国”或“大逆不道”。
苏轼虽然躲过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毫无实权的职位,相当于被发配边疆。
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关进御史台狱中,狱中生活极为艰苦,他自知性命难保甚至写下遗书:“伏死之后,葬于江上,无以家事累人。”他把生死看得很淡,却对家人的安危极为牵挂。

黄州的生活与苏轼以往的仕途完全不同,他没有俸禄,靠自己耕种度日,生活清苦,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无常与本质,试图从苦难中寻找一丝乐趣。
在黄州的四年他物质匮乏却心态豁达,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赤壁赋》《前后赤壁赋》就诞生于这段时间,他的思想也从入世的积极转为出世的洒脱,开始接受命运的波折。

但无论多豁达他终究没法彻底摆脱现实的羁绊,“文章惊天下,仕途不如意”是苏轼一生的写照。1079年后的苏轼,再难回到政治核心,变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旧党领袖司马光重新掌权,推行“元祐更化”,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苏轼也迎来了仕途的短暂高光,他被召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等职,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依旧谨慎,他既不完全支持旧党,也没有彻底否定新党,两派都看不惯他但又无法忽视他的才华。

他负责修缮西湖时主持修筑了“苏堤”,解决了西湖淤塞问题,这件事让杭州百姓至今感恩。
政治形势很快又变了,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次掌权,这一次新党的领袖是章惇比王安石更为强势,也对苏轼更加敌视。
1094年苏轼被贬到惠州,惠州已经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地方,但章惇仍不放过,继续给他施压。
1097年,苏轼被流放到更远的儋州,海南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发,被称为“瘴疠之地”,流放到这里的人,基本没有回来的可能。

在儋州苏轼依然没有放弃,他在海南开设学堂,教化当地百姓,将中原文化带到荒蛮之地,他的乐观精神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虽然艰苦,但他把生活过成了一场修行。苏轼在这一阶段也尽量避免党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百姓生活,而非继续卷入派系斗争。
但在一个以党派利益为中心的政坛上,中立显然是一种奢望。

1099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新党失势,苏轼终于被赦免回到大陆,可惜此时的他已年过六旬,身体羸弱无法再为官,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
他不是一个坚定的派系人物,无法彻底融入任何一方,新党认为他顽固,旧党觉得他不够坚定,他两边不得罪却也两边不讨好。
他直言敢谏,不善于迎合,政敌想打压他轻而易举,像乌台诗案这种事换别人可能避开了,但苏轼的才华和锋芒却成了祸根。

北宋中期的党争不允许“中立者”存在,苏轼的政治智慧虽然不低,但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也难以招架。
苏轼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通过诗文、书画、政绩影响了后世千百年,这或许才是苏轼的“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