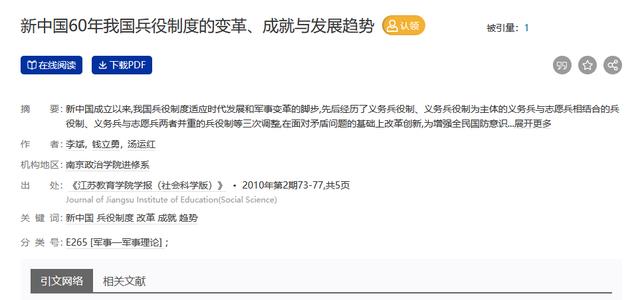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特别是关于在特定情况下征召36至45周岁男性的权力,根植于国家根本大法和长期演进的兵役制度。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行使这一权力,这部法律自1955年诞生以来,经过多次修订,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时与战时相结合、义务与志愿相结合”的动员机制。
这套制度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规矩,打哪儿来的?
现代中国兵役制度的基石,可以追溯到1954年宪法确立的义务兵役制。
在此基础上,由聂荣臻元帅主持起草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于1955年颁布实施。
聂荣臻在制定该法时,就高瞻远瞩地强调“预备役制度要着眼长远”。
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为满足特殊战场环境的需求,军方就曾试验性地征调了约5000名年龄在35岁以上、具备特定技术专长的兵员,以补充高原部队的技术力量。

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防需求的变化,兵役法经历了多次修订。
1998年的修订是一个重要节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积极推动建立了更为科学的三级兵员评估体系。
这套体系旨在更精确地评估预备役人员的专业能力、身体状况和动员潜力,为快速、精准动员奠定基础。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正是依托这套评估系统和相应的动员机制,军队得以在短短3天内,完成了对来自不同地区的15万预备役人员的调度集结,迅速投入抢险救灾,为挽救生命、恢复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

历经11次修订,兵役法逐步形成了“平时与战时相结合、义务与志愿相结合”的成熟动员体系。
2023年最新修订的兵役法,在第四十九条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国家发布动员令或者遭遇重大安全威胁、需要进入紧急状态时,可以决定扩大兵员征集范围,征召36周岁至45周岁男性公民服现役的权力。

谁说了算?咋分工的?
战时扩大征召范围的权力,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行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款的规定,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这意味着在动员过程中,国务院负责统筹全国的行政资源、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撑。

国务院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已有体现。
例如,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暴发,面对医疗物资极度短缺的严峻局面,国务院启动应急机制,在短短72小时内就协调完成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医疗物资跨区域调配,保障了抗疫前线的急需。
这种高效的组织协调和资源调动能力,正是战时进行大规模、复杂动员所需的核心要素,为特殊情况下的兵员征召提供了坚实的行政保障。

与此同时,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国家军事领导机关,则负责具体的军事动员指挥。
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如全军战备数据系统,中央军委能够实时、精确地掌握全国范围内的兵员数量、分布、专业结构等动态信息。

以东部战区某集团军为例,其建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精确调取辖区内高达360万预备役人员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专业技能、过往服役经历等。
这使得在需要征召特定专业人才时,能够快速筛选、精准匹配,确保征召的兵员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作战需求。

这种国务院负责行政统筹、中央军委负责军事指挥的分工协作机制,在2016年启动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例如,在退役军人安置方面,中央财政承担了高达70%的费用,这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负担,也解除了潜在动员对象的后顾之忧,为在必要时快速、顺利地进行兵员动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为啥专挑这批“老兵”?
将36至45周岁的男性公民纳入特殊情况下的征召范围,并非随意之举,而是基于对这一年龄段人群独特战略价值的准确判断。
他们虽然在体能上可能不如年轻士兵,但在知识、技能、经验和社会阅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国家战争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这一群体是国家高技能人才的“富矿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全国约63%的中高级技工集中在36至45岁这个年龄段。
其中,掌握各类军民两用技术的专业人才数量庞大,估计约有1200万人,涵盖数控机床操作、精密仪器维修、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特种焊接、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

这些技能在平时是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战时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或强大的保障能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参与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改造工程的高级焊工李明华。
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发明了“多层多道焊”新工艺,显著提升了航母甲板的焊接效率达40%。
这项技术后来被证明具有很高的军事应用价值,可推广应用于野战工事的快速构筑和修复,大幅缩短作业时间。

其次,这一年龄段积累了大量具备基层管理和指挥经验的退役军人。
据估算,全国约有85万名曾在军队担任过尉官职务的退役军人属于这一年龄区间。他们熟悉军队的运作模式,具备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
在战时,经过短期恢复性训练,他们可以迅速补充到部队中,担任基层指挥员或管理人员,有效缓解战时可能出现的骨干力量短缺问题。

2022年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的一次对抗演练中,一位被征召回役的38岁预备役军官王建国,凭借其过往的服役经验和在地方企业从事物流管理的知识,创造性地将民用物流管理系统引入到部队的物资配送流程中,成功将战场补给的响应时间缩短了28%。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尽管征召36至45岁男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必然会遇到一些现实的挑战和需要妥善处理的复杂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特殊的家庭结构带来的影响。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大量“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成为社会常态。
征召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中年男性,无疑会对家庭的经济来源、老人赡养、子女照顾等方面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2015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救援行动中,曾需要紧急征召一批化工领域的专家参与处置。
当时,某位符合条件的化工专家因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唯一劳动力,其父母年迈多病,妻子也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

地方人民武装部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进行了审慎评估,最终依据相关规定,并报请上级批准,对其作出了暂缓征召的特殊处理。
这个案例引发了对动员政策人性化和社会影响的深入思考,并直接推动了相关法规细则的修订。
在2020年修订兵役法实施细则时,特别增加了关于家庭风险评估的条款。

为了更好地解决征召可能带来的后顾之忧,退役军人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也建立了一系列配套保障制度。
例如,推行“双清单”制度,即一方面建立符合征召条件的预备役人员清单,另一方面建立需要重点帮扶的被征召人员家庭清单。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前识别困难家庭,并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
根据公开数据,仅2024年,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就为被征召人员家庭提供了约1.2万人次的就业帮扶,协调解决了约8700例涉及子女教育转接等实际困难。

跟国外比,咱有啥不一样?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特定情况下扩大兵员征召年龄上限的做法并非中国独有。
一些面临现实安全威胁或奉行普遍兵役制的国家也有类似规定或实践。
例如,韩国在经历了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为加强技术兵员储备,就将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征召年龄上限提高到了45岁。

中国动员体系的特殊性在于其强大的行政力量与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的紧密协同。
这种军政一体、平战结合的动员机制,使得中国在动员的速度、规模和精准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以资料中提及的2024年某次台海联合警巡行动为例,南部战区依托大数据分析系统,能够在短短6小时内,从广东、福建等地的民航维修企业中,精准筛选并锁定约2300名具备特定飞机维修资质和经验的预备役人员,为后续的动员和部署提供了快速响应能力。

这种高效动员能力的形成,得益于中国长期以来对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的持续投入。
早在2003年,中国就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并在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技术人才密集的省份率先试点“平战转换”机制。

这些试点旨在探索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效地将民用资源,特别是高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快速纳入国防动员体系。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这些成功的机制和做法如今已逐步推广至全国333个地级市,形成了覆盖全国、军地协同、高效运转的现代化国防动员网络。
参考资料:[1]李斌,钱立勇,汤运红.新中国60年我国兵役制度的变革、成就与发展趋势[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2):73-77